生活圆桌(155)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劳乐 布丁 洪晃 何人)
生前身后
劳乐 图 谢峰
一开始本来是件很普通的事:我们的一个大学同学最近失去了音讯,于是大家吵吵嚷嚷地在校友录的BBS上贴“寻人启事”。终于有一天这个家伙躲在这么一个帖子后面露面了:
在复兴门地铁站检票的阿姨,是我。
在新东安卖仔裤的姑娘,是我。
在中关村卖盗版光盘的小个儿,是我。
在聊天室恬不知耻的人,是我。
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的胖子,是我。
在电视机前流哈喇子的白痴,是我。
在生活里吊儿浪当的人,是我。
是我,是我,还是我。
我们的同学中还有一个是在毕业后留校读了两年英美文学研究生,现在在美国某大学深造,攻读这一领域的博士。他当然也在这个BBS里凑热闹。看过上面这个帖子后,他回了一个近千字的英文帖子。内容翻译成中文大致是这样的:
“这是上个世纪的一位中国诗人手稿中的一段文字。文献学研究证实这是一部长诗的一部分,而那部长诗本身不幸已经散佚了,我们甚至不知道这部长诗的标题。从残存的部分,我们可以假定这是一部自传体诗歌,它意在以普通现代中国人的口吻,表现作者对某次心理危机的极其复杂的反省/重组过程以及后来得自于艺术的(部分成功的)救赎。诗人本人情况和他的作品一样暖昧。目前我们对他的生活知之甚少(注:男性第三人称此处只用于泛指,因为我们至今无法确定这位诗人的性别)……”
在别的情况下这也就当个笑话了。但我们那位留洋同学的学历着实让我担心:也许有一天他会在没有别的题材可做的时候,把我们那个同学真当作一个中国佚名诗人介绍给他那些学究教授。十几年后,当我们再以崇敬的心情捧读某本权威“anthology”时,会在里面发现一串“it′s me,it′s me”。
大学文学课上我们学过拜伦的诗。但那时我没有在那个原文选本里看出我以前了解的拜伦。我原来的印象中,他总在诗里吹嘘他1810年横渡达尼尔海峡的那段经历。据最新考证,拜伦算得上“横渡海峡”这项运动的世界第一人。在我看来,假如后来拜伦不是识趣地在《哈罗尔德游记》与《唐·璜》里塞进了更多的其他文字,今天的人大概只会记得他是一个不错的业余运动员,不会想起什么“反正我坟头的青草/将长久地对着夜风叹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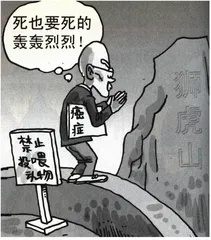
中学时一个同学曾经雄心勃勃地说: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不管是否“百世”、“万年”,其实人死后留一件事出名也就不错了。但我有时还是不免有些苛求。我曾经听一位老教授指着他身后的一排书感慨:“我一辈子就写了这么几本小书。”当时我暗地里很同意他的说法,因为我想起了阿西莫夫的书房:他出的书摆满了一书架,没有一本重样的。
作家玩具
布丁
有人向我描述一个玩具,是徐志摩的偶像,下面有个按扭,你一按,那玩具就会背出一段徐志摩的诗出来——我是天空中的一片云,偶尔飘到你的波心。更多时候,他背的是更著名的那几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玩具售价30多元,可惜会背的诗少了些,要不比买一本诗集划算。
等我见到那玩具的样子不禁有些失望,大诗人和泥人张的玩偶没什么区别。这就是形象对想象力的抹杀,有个朋友看《人间四月天》,看到徐志摩、林徽音陪泰戈尔那段——也就是人们形容为“岁寒三友”的——对我说:“中间那个卖羊肉串的新疆大爷就是泰戈尔吗?”
外国人评价海明威,说他是“作家中的第一个偶像”,其实,我们要是把作家做成个泥人张似的玩具,鲁迅就是个好选择,他那向天刺去的头发和浓密的胡须比徐志摩更有表现力。他的名句也不少,你一按按扭,他就说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或者说,也许可能大概是渔火。当然应该把更有战斗力的句子输入到玩具中——《纪念刘和珍君》或“我以我血荐轩辕”、“怒向刀丛觅小诗”就好。金庸慈眉善目的也可以做成玩具,他要读出小说,那比好多有声读物好—一有声读物在我们这里不发达。
这思路自然可以挪到外国作家身上,做个海明威,他就给你朗诵《老人与海》,要是太长了就来“密执安北”;做个马尔克斯,他就会朗诵《百年孤独》那著名的开头。上了年纪的杜拉也很像个玩具,可以录上她特有的一段絮叨:“这个形象,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形象,只有我知道,这个形象,我却不曾说起。”
我把这个构思和一个朋友说,他刚从北京的“孔乙己酒家”吃完饭,拿着牙签说:“孔乙己酒家门口就有个鲁迅塑像,要不咱们在他下面弄个按扭,一按,他就能背一首诗出来。”
他这么一说,我想起大学校园里那座鲁迅雕像,每次上课从先生身边经过,他要是能忽然说出点什么,那一定能激发我们求学的热情。我们的校园里只有这一处雕像,据说清华大学里的雕像多,有吴晗,有朱自清,有闻一多。清华是理工大学,心灵手巧的人有的是,他们应该在闻一多先生的雕像上添加新装置,让每个学子走过的时候都能聆听先生的教诲:“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谁的心里有尧舜的心,谁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谁是神农黄帝的遗孽。”
特殊人才使用说明
洪晃
我在猎头公司做事的时候经常看到客户要求我们帮他们寻找符合以下规格的人才:上好的人品和职业道德,优秀的专业知识,强烈的团队意识和(与前者完全相反的)个人奋斗精神。
我每次都是打着灯笼满世界找这种人。经过多年反思,虽然已经不做猎头了,还是要推荐两种特殊人才,让找人的CEO们意识到,人无全人,只要用人之长,避人之短就行了。
类别:靓女
规格一般都在1.68米以上,看的书少一些,用的化妆品多一些,说话的声音柔一些,穿的裙子短一些。
靓女的问题在于其功能最好不要在内部使用,如果用靓女作任何公司内部管理,都是风险比较大的。特别是对中年男性CEO之类的管理人员,更要格外小心。比如使用靓女为总经理秘书或助手,其“靓”就会攻内不攻外,经常在公司内部引起纠纷,给公司带来损失。有的私人老板在用了靓女秘书之后,众叛亲离,最后只好娶了靓女,丢了半壁江山。
靓女的使用寿命非常短,如果在财务报表上呈现靓女的价值肯定是在低质易耗一栏中。
类别:搅屎棍
规格:长不到1.60米,基本上是圆形的,话特别多,闲事管得特别多,零食吃的特别多,厕所里聊得特别长。
使用方法:搅屎棍是煽动力和沟通能力非常强的人,喜欢在办公室里搞点政治的CEO可以有限使用。搅屎棍的信息非常多,是个一流的包打听,谁在偷偷上人才网,谁说了对公司不满的话,连谁吃什么避孕药她都知道。搅屎棍对刚刚上任的新老板就有用。
搅屎棍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她提供的信息质量很低,大部分是道听途说,甚至自己瞎编的,这类信息只有参考价值。二是如果管理人员不能有效地使用搅屎棍,她会因此煽动雇员闹革命,充当工会主席的角色,这也是非常烦人的。
搅屎棍用完了就一定要扔掉,不能留。有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在自己公司里雇佣搅屎棍,他们会请外面的搅屎棍,这些人的学名叫管理咨询人员。他们到一个公司,上上下下打听个遍,谁跟谁跟谁跟谁,都弄得非常清楚。然后把工作报告(就是小报告)给新上任的CEO,再出点鬼点子,就完事走人了。
仰望星空的荣耀
何人 图 谢峰
能仰望星空是一种荣耀,我一直是这么觉得。哈代在《苔丝》中,写到克莱尔的牧场时,有一段对光和影的精彩描写:“很久以前太阳也曾在大理石的宫门上投射过奥林匹斯诸神的影子、亚历山大大帝的影子、恺撒大帝的影子,和诸多埃及法老的影子,也是那么一丝不苟……”一样道理,如果仰望星空是一种荣耀,那也将是依仗多少先贤而成就的。当那些已成功地把自己生活提升到有时间去注意咖啡壶工艺的准小资们谈论起夜阑人静,自己仰望星空的经历时,他们八成想到的是:多少年前于同一星空下,也曾投下过阿基米德、哥白尼与伽利略的影子,也曾如对待自己一般一丝不苟……
星空确实是美丽的,这也许是自然界之中最简单的构图,却能表现出摄人心魄的魅力。但我并不喜欢如凡高那将五颜六色的油彩漩涡状的涂抹,《科幻世界》经常登载吉姆·博恩斯的科幻画作,那上面的星空清冷、深邃,如阴郁的大海一般,能让人产生一种被淹没的欲望。
但即使我激动过,陶醉过,却并不代表仅此便有资格获得仰望星空的荣耀。在我常去的一个BBS上,斑竹同他一伙吆三喝四的大虾酷爱谈论星空,经常把此类帖子不厌其烦地接得老长。很多情况下,打头的从自己乘船深夜穿越赤道时亲眼目睹星座起落的经历开始;就有人谈到了康德墓碑上“……头顶闪耀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准则……”最后终于掘墓起尸,聊起了哲人的《纯粹理性批判》。我不知深浅,在直逼三位数的跟帖后又插一句,壮着胆子谈了谈自己冬季观察猎户座的经历,却不料长帖至此便戛然而止。思来想去,也许是自己的品位太低,坏了别人兴致,落得个竖子不足与谋的下场。
于是我这样一个试图加入“革命党”未遂的家伙便注定分摊不到仰望星空的荣耀,那代表着高贵、睿智的标准对我来说遥不可及。入夜,当我独自走在人行道上时,仰睇天路,竟然已经连银河也看不到了。就是这个远非发达的二流城市,也很牛气地凭借着缠绕在楼间、树上的无数小电珠那聚少成多的灯光压倒性地遮蔽了星星。我想,在我的脚下,一定有星光赐予的投影,但是在那无数浮躁的灯光里,我无法看到。
直到后来,我的一位仁兄在自己四楼的宿舍的窗子前架起了一架价格不菲的筒型望远镜。我才获准在他不用时借以仰望星空。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他的镜头并不总是对准高处的星空,而是居心叵测地定在了对面女宿舍的角度。“用这样的倍数养眼已经很过分了,”他同宿舍的一位哥们儿告诉我,“不过,他偶尔也会看看天上的星星,权当换换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