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都是背背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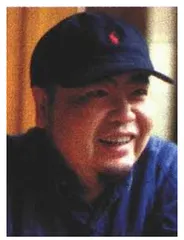

从星光闪闪的奥斯卡领奖台到灰头土脸的北京胡同,从客串于T台上的库尔尼科娃到姓名不详的邻家娇娃,一个又一个不同肤色的背部在同一片天空之下裸露着。套用时尚的术语,无处不在的背和露背装正是街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背是负面的,露背是被迫的。露背装第一次盛行的背景,是上世纪20年代出台的希斯法案。按照这个道德至上的法案,好莱坞的女明星在银幕上不得过分暴露自己的正面。不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朱自清先生在《背影》第一段里引用其父的话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想好莱坞当年一定也是这样勉励自己的。万物皆负阴而抱阳,凡有前,必有后,人有前胸,必有后背,胸不能露,则露其背。随着好莱坞把创作重点从前沿转移到后方,露背装就这样从背后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仍不时地暴露出它终究是道德禁忌之下的机会主义的块肉余生,是一种妥协的策略,一种“前有政策后有对策”的产品。今年2月,《蝴蝶是自由的》在中国最摩登的城市上海演出时,一场原本做身体正面暴露的激情戏最后还是改成了背部全裸。
作为表达方式的一种,裸露可能也是人类的天性。穿着露背装的女人与依靠暴露思想为生的男人,其法一也,皆为修辞学上的隐喻,春夏时装,春秋笔法。露背与袒胸之间的关系不是暗示,而是类推。在这个意义上,露背装就是一件反穿的低胸装。许多年以后,在史蒂夫·马丁和高蒂韩合演的一部很闹的闹片中,好莱坞也作出了不经意的自我解嘲,剧中的这对中年夫妇情意绵绵地回忆当年初相识,男的语女的:“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你穿着一件胸前挖开了一个心形的紧身上衣,像是准备接受心脏手术。”
罗兰·巴特说:“流行毫无内容,除非是在修辞层面。”在修辞层面,相对于正面,我们对任何一幅裸露的背部其实所知不多,除了拒绝、说不、猫匿和背叛之外,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可供刻录或书写警句的肉体平台。据说晚年的齐白石先生有一次为了应酬堵在门口求字的女宾,曾经挥毫在该女宾身上的一件白背心的背面题诗一首,末尾两句是:“九十老人狂大作,姣君身上来题诗。”书罢长叹一声,上车去看“背上有戏”的梅先生的演戏去也。这件原作下落不明,不过,无论是间接题在背心的背面的还是直接题在裸露的背上,相信也会是大面积留白的,这是因为即使脱离了修辞层面而做直面的观察,与正面相比,背部因其幅员辽阔以及缺乏起伏而感觉十分荒芜并且不毛,十分地月球。尽管时尚杂志一直企图以肩、臂、腰为带动来开发出背部的意义,同时美容以及护肤品销售商在“把背当成脸来呵护”的口号下亦致力于在此开辟出一个全新的第二市场,不过这种努力显得十分勉强。相比之下,相信大街小巷里“穿露背装的女郎和光着脊梁的男士”都是为了“凉快”之故的医学专家在报纸上提出的“露背装无助于防暑降温”之忠告,就显得厚道多了。事实上,就单纯的审美而言,露背装的“背论”更是暴露无遗。作为媒体,露背装违背了人类接收信息的一般方式,即无论是书籍、报纸、电视、电脑、收音机还是镜子、表情或者肢体语言,无不是当面的。背后的审视、议论、攻击等等,因为违反了人与媒体/信息的正常关系,所以都是背德的行为。露背装在客观上造成的视线的“跟踪”尽管有助于在城市丛林的狩猎游戏中进一步减弱双方的窘迫并且使乐趣倍增,但是真的猛士却有机会因此而枉做了小人。
人类学家McCracken认为,如果人可以阅读他人的服装,他们所预期的不是新的讯息,而是既有规则的展现与复制,任何不合常规的符码组合将只带来困惑和沟通上的无能。1974年,当已经拥有许多双鞋子的伊梅尔达·马科斯在新闻纪录片里将她雪白的背部大幅裸露在中国观众面前,不知道有多少像我一样的少年在黑暗中目瞪口呆。然而一个女人毕竟不是一个王朝,她的背影并不十分地可堪玩味。二十多年过去了,历史的断裂和不连续性以及身体的非实质化和隐喻性与日俱增,在经验的无能之中,瞻前顾后,都是背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