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称职的机会主义者
作者:舒可文(文 / 舒可文)

裸露的后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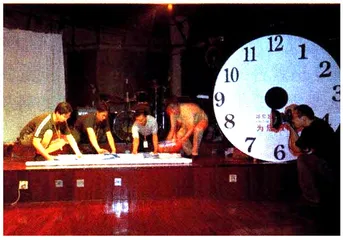
用担架抬上来的《新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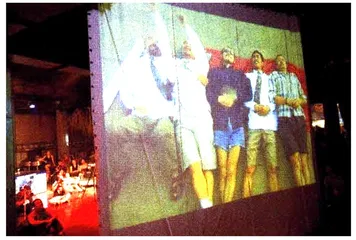
荧幕上放映的是“舌头房地产公司”的新闻

舌头乐队做现场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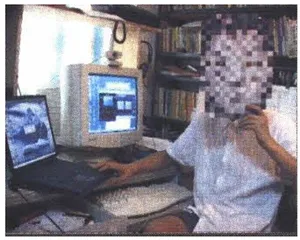
藉着一本叫做《新潮》的艺术杂志的首发式,一个试制试管婴儿一样的游戏在藏酷酒吧热火朝天了一把。现场布置为四个区:A区为表演的发生区,使用大堂东南角侧的常规舞台;B区设置成酷似新闻的演播台,为播音员表演区,使用大堂东南角;C区悬挂投影用的大屏幕,使用大堂东北区;D区为观众席,中间是摄像机、投影机机位和VJ操作台。
既然是个首发式就有新闻发布的意思,游戏很机会主义地采用了新闻报道的形式,叫“新潮新闻”,是对大众传播媒体中的新闻报道栏目的戏谑模仿。它套用了新闻栏目的经济、文化、体育、天气预报之类的板块秩序,将常规内容置换为中国当代艺术界的新闻。预制的“新闻”与实时发生和拍摄的现场事件相互组合,构成一个综合了录像报道、录像艺术作品、戏剧、行为艺术和真实事件的混合媒介活动。
其中有些新闻是真实的,搞笑的手脚做在解说词和采访的提问上:北京大学现代艺术协会主办的一个观念摄影展,天津画家李津在北京四合院画廊的个展是两条真实的展览消息,“播音员”的播报中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准确字眼,伴随着大屏幕切换出的展览现场画面。然后播音员使用的字眼就开始打滑,说李津的画描述了琐事中的平庸和诗意,尤其提出了能吃就吃的艺术理论;说他的新作形象地传达了能吃便是福,吃到肚子里才是自己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诸如此类。然后还有对当事人的现场采访,画家李津好像瞬间明白了这个采访的搞笑阴谋,很知趣地配合出一脸若痴若呆的滑稽。观念展的策展人管郁达先生对着话筒便似乎在酝酿着学术一点的姿态,但是采访者的嘴脸肯定暴露了什么,阻碍了管先生畅所欲言。结果他好像要说,但又说不出什么,不知所云地叨唠了几句,词不达意,倒也映衬了述说观念的艰难。
另一类新闻半真半假,艺术家王迈申请赴美签证被拒签很生气是那一半真,有很多申请人被拒签也是真,那一半假是王迈在面对采访时打扮成了个农民,说他也不想去,是县上让他去的。拒签也没什么,但是交了那405元人民币不退给他让他心疼,“这事儿不能说,说起来就眼泪汪汪的……”他还做出擦泪状。
头发长常常被识别为艺术家的职业发型,光头也是他们的偏好之一种,在这里就模拟了一项社会调查的最新资料,发现艺术家的发型与他的风格和收入有直接关系。画油画的光头占63%,做行为艺术的长发占70%,从事摄影录像电脑艺术的平头占91%。头发的长短与收入成反比。真的吗?
藏酷的环境设计者林天苗、王功新的儿子跟随着父母也是大家的熟人,他被所在的幼儿园开除了。“记者”问到他的父母,他们都对此很莫名其妙,好像说是因为块头太大,或是因为太自由主义?真的吗?
写成文字来叙述才会有这样的追问,在现场搞笑逻辑中,你所能听到的反应是一片笑声,也有没有被卷入其中的人无奈的烦躁。其搞笑的素质酷似流行于酒席饭桌上的段子,赶上有正经事要做的人会对一个个段子倍感郁闷,对于正闲得心慌的人或忙了一天来疏散心情的人,段子既是好的下酒菜,又能满足“叙述”的快感,还能起到交流时尚信息的作用。段子是集体智慧,集体游戏,有传播的能量,也需即兴而发的技巧。段子是机会主义的杰作,任什么天文地理人情世故,段子会随景应市,应时而生,不求常说不衰,就当这儿说这儿了。
《新潮》杂志的主办者之一栗宪庭说这个活动虽然是一笑了之的一个闹剧,但还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作品,这些内容由不同的艺术家分别完成制作,它涉及的都是大家关注的话题,用了轻松化、玩笑化的滑稽模仿方式,这和整个生活气氛是一致的。90年代中期以后就是这样的生活气氛,在搞笑这一点上,这个作品和生活没什么区别。
杂志的首发式真实地被插在新闻中,随之而起的新生儿的哭声却又再次通报了良苦的祝愿也在游戏之中进行。舌头乐队的演出是现场的,对它演出的报道却是一通云山雾罩。
段子的搞笑离不开讲段子的现场,这个设计的搞笑也着意强调它的现场性。后台是裸露的,摄像机在观众跟前晃来晃去地忙着。播报员的桌子下面是玻璃板,三个民工坐在里面,一人拿一支笔在苦苦地计算他们这一年来的各项零零碎碎的收入,他们与发生在这里的一切都毫无关系,他们被机会主义利用了来营造现场的全景感。笑声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如果没有了这部分岂不让双方都感尴尬,好在有一个专属于段子的礼貌——如果你觉得一个段子不好笑,你可以伸出胳臂做一个胳肢自己的姿势。 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