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玛尼、杰奎琳的衣服以及艺术博物馆的贞操
作者:钟和晏(文 / 钟和晏)

大师与酒签
刚刚在中国美术馆结束的“罗思柴尔德木桐堡(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酒签绘画原作展”是个不为人注目的小展览,尽管出现在其中的艺术家足以构成一份异常辉煌的名单:毕加索、达利、康定斯基、夏加尔、巴尔蒂斯、亨利·摩尔……但和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仅仅是大师们为波尔多地区某个贵族佳酿提供的几笔信手涂鸦,这个展览也就注定受人冷落。在开幕式上,木桐堡如今的主人菲莉嫔女男爵也不得不说“你们今天所看到的不是什么杰出的艺术作品,不过出现在这里的确实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家。”从1946年起,罗思柴尔德每年都会请一位当代画家创作一幅绘画用作酒签,这样的展览已经在全世界三十多家博物馆中展出。
即使罗思柴尔德是渊源流长的著名家族,即使木桐堡葡萄酒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或者最昂贵的美酒之一,这种艺术和商品的结缘仍然是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一开始,菲莉嫔的父亲非利普男爵只能请他朋友圈中的知名画家作画,而艺术家们都羞于在酒签上留下自己的签名,直到1955年立体派大师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兴致勃勃地绘制了一幅酒签并签上大名后才改变了情形。多年以来,罗思柴尔德家族固守的一项传统是他们从不付钱给绘酒签的艺术家们,而是每次奉送若干箱不同年代的美酒,这也算是古老贵族和艺术家之间彼此维系的一种尊敬和体面了。
杰奎琳·肯尼迪的华服
5月1日,由大都会博物馆属下的服装协会主办的“杰奎琳·肯尼迪:白宫岁月”展览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幕。引人注目的是服装协会历来在博物馆地下室举办类似活动,这次却登堂入室进入二楼画廊,距离正在举行的“维米尔和代夫特画派”展(Vermeer and the Delft School)几步之遥。这样,通常人们欣赏绘画或雕塑作品的地方如今挂上了杰奎琳白宫岁月期间曾让万众瞩目的各式华服。
大都会博物馆的宣传册上宣称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纪念杰奎琳40年前成为美国第一夫人以及为了探讨她对时尚风格的持续影响力,而艺术评论家们则称之为“令人吃惊地肤浅和滑稽可笑”。相对于去年10月阿玛尼(Armani)在距离大都会仅几个街区的古根海姆(Guggenheim)博物馆举行服装艺术展时评论界的激烈措辞,这样的反应已经足够温和。当时,批判家们将阿玛尼服装展视为纽约艺术机构为了金钱和广告效益的一次卖淫行为。《纽约观察家》的希尔顿·克莱莫说:“事实上,我不知道任何严肃的艺术家、批评家或艺术品收藏家之中,有谁会将阿玛尼的套装视为艺术品?”《新共和》的杰德·珀尔则将那次展览称为“达达主义、民粹主义、庸俗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又一次聪明的混合”。
在这种所谓聪明混合的背后,是阿玛尼展被宣布一个月后,古根海姆透露阿玛尼公司将在3年内向博物馆捐赠1500万美元。而资生堂公司在纽约大学的灰色画廊举行展览后捐赠了50万美元,这对一个大学来说也算笔不菲的财富。去年6月,大都会博物馆就曾取消了夏奈尔的一次服装秀,据称原因是夏奈尔的设计师拉格菲尔德对那场展览过于指手画脚,当然夏奈尔也就立即取消了原定150万美元的捐赠。
让批评家们担心的是,艺术和商业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任何一个公司如果出钱,就能将自己的商业产品冠以艺术品的美称进行展出;如果一家公司足够有钱,它甚至可以买下任何一家重要的博物馆来促销它的产品。即使拉格菲尔德在接受《Talk》杂志采访时,也同意类似阿玛尼、夏奈尔的服装展览与其说是时装公司对时尚历史的兴趣,不如说是一场商品促销活动。至于说到和大都会的那次纠纷,拉格菲尔德讥讽道:“他们其实才不是怕变得商业化,他们只是觉得我太认真了,他们真正要的是支票而不是我。”

艺术品还是商品
对大都会博物馆的馆长菲力普·德·蒙特贝罗(Philippe de Montebello)来说,杰奎琳·肯尼迪的衣服未必是他真心希望出现在二楼画廊的展品,他写在展览目录前言中类似“这次和肯尼迪图书馆及博物馆的合作有助于互相分享对肯尼迪夫人服装的方法学阐释成果”这样云山雾罩的话也极其敷衍。拉格菲尔德的讥讽也许道出了部分事实,“杰奎琳·肯尼迪:白宫岁月”展览由一家著名化妆品企业赞助,由孔岱·纳斯特出版社担任承保人,而孔岱属下时尚杂志《Vogue》的一位编辑理所当然地成了布展人。
另一事实是如今艺术博物馆和好莱坞电影一样面临着票房收入的压力,如果人们不愿意掏钱观看真正的艺术,那么最简单的哲学就是提供给人们他们想看的东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1998年宝马公司在古根海姆举行的名为“摩托车的艺术”那次展览,尽管评论家极尽讽刺,却引来观众如潮和几百万门票收入。何况这种简单商业哲学也可以被提升到民众理想主义的高度,即尊重每个个体的存在,包括他们的兴趣、品位和欲望,而不仅仅视为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一种实用主义态度。
大都会服装协会的会长哈洛德·科达就曾为自己辩解说:“艺术从来都需要权势人物的支持。我们会不会嘲笑美第奇的一幅肖像,因为画中人是艺术资助者并且在自我吹捧呢?”
艺术需要资助与供养,不过当财团和艺术机构或者艺术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狰狞时,类似罗思柴尔德家族和艺术家之间的温情和体面都成了值得我们怀念的东西。何况,在金钱的魔力下一切商品都可以被称为艺术品时,我们也就越来越不知道究竟什么是艺术品了。
(图片为本刊资料)
杰奎琳·肯尼迪的卡梅洛幻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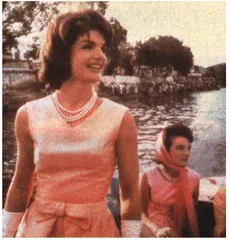
有不少人热衷于发明创造另一个自己,比如迈克·杰克逊就成功地给了自己另一张脸,在那张苍白的人造面孔下他的真实面孔已经完全消失。杰奎琳·肯尼迪的假面则是由几百套华丽的服装、精心的发型和刻意的举止构成,这使她和奥黛丽·赫本一样成为优雅与高贵的代名词,以至于杰奎琳成为第一夫人40年后美国人还会隆重地举办一场杰奎琳·肯尼迪的服装展示来纪念他们的“时尚偶像”。在呈现于公众面前的优雅高贵背后没有人知道杰奎琳的真实个性。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二楼展室的墙壁被粉刷成象征肯尼迪时期理想主义的粉红、橘黄和冰蓝色,里面悬挂的80多套服装中既包括杰奎琳在1961年1月20日就职典礼上的浅黄色大衣和著名的圆桶形帽子,也有同年在维也纳让赫鲁晓夫眼花缭乱的镶满珠子的晚礼服。但是那里既没有肯尼迪夫人拥有的几件毛皮大衣,也没有那件粘满肯尼迪总统鲜血和脑浆的粉红色夏奈尔套装。一切有损于杰奎琳·肯尼迪完美神话的细微痕迹都被小心地拭去,人们似乎更愿意在不无伤感中追怀她曾经有过的美妙生活。
1963年11月31日,在肯尼迪总统被刺一周后的一个深夜,杰奎琳·肯尼迪曾试图通过《生活周刊》的记者西奥多·休·怀特(Theodore H. White)让美国人相信短暂的肯尼迪政府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奇迹的卡梅洛(Camelot)时代,那是美国历史上殷勤的男人和美丽的女人共舞,伟大的事业被成就的辉煌时刻。虽然肯尼迪的卡梅洛幻象很快被证实为一种历史的谎言,杰奎琳以她的服装为道具独立完成的卡梅洛幻象却被长久地保留下来。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显然幻象比真实更加愉悦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