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你快走开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王晓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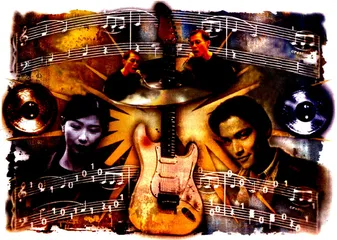
我无意中参加了一个罗大佑网友聚会,聚会的人看上去差不多都30岁左右,他们就像《童年》里的“我”一样单纯。我猛然间想到,在这个文化缺斤短两的时代,居然还有这么一群人在认真地谈论着他们未泯的理想,让我默默地感动了半天。还有一次,在一个酒吧里,音响里正放着罗大佑的歌,周围的人都随声齐唱,坐在我旁边一个酷似谢霆锋或安在旭模样的男孩不停地问我:“这首歌是谁唱的?”那个男孩像见到失散多年的亲爹一样手舞足蹈。
我一直认为,罗大佑像鲍勃·迪伦一样经历了从艺术家到艺人的蜕变过程,迪伦的分水岭是《路上的血迹》,罗大佑的分水岭是《爱人同志》。30年前迪伦在写《时代在改变》时他摸准了时代脉搏,去年在为电影《神奇小子》写插曲《事情在变》时他只剩下了刻薄。罗大佑从《恋曲80》、《恋曲90》到《恋曲2000》,像软件升级一样,但变得越来越华而不实。当然,作为一个听众,你无法让一个走到高处不胜寒并且也到了强弩之末的人按照你的意愿继续“寒”下去,能做到的就是“我再不相信你编的谎言,你也再不介意我的流言”大家都喜欢甜言蜜语,不就是娱乐么。所以我更愿意把现在的罗大佑当成和天王们齐名的艺人来看,而不是去怀旧。
我想,那些在80年代听罗大佑的人,是最投入的。那是个不太物质、不太诱惑的年代,人们对精神上的渴求要高于物质。还没有泯灭理想的人喜欢去探寻真理,因为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所以喜欢用一种沉重将自己压得充实些,罗大佑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文化读本。而今天的未来的主人翁们早已在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下变成电脑儿童,这些聪明的孩子都提着易碎的灯笼,他们在充满诱惑的世界里不再去问“这是什么道理”。
我并非想否定谢霆锋们对罗大佑的喜爱,我只是有些怀疑这种喜爱的盲目性。或许他们能读懂“道一声别离忍不住想要轻轻地抱一抱你”,却读不懂“情到深处人孤独”;也许他们能读懂“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却读不懂“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也许他们能读懂“寂寞的山谷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却读不懂“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所以,这让我想起罗大佑后来和一个词藻华丽、读起来很酷但言之无物的词人林夕合作,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罗大佑不可能再去写也写不出来充满智慧的歌词了,同时也为他迎接更年轻的听众埋下了伏笔。这又让我想起另一个歌手朴树,他尽可能用一种酷和躁动来掩饰他阅历的苍白。同样的还有王力宏、林志炫之流,前者翻唱的《龙的传人》,我越听越感觉我们是“蛇的传人”;后者在糟蹋崔健的《花房姑娘》时让我感觉他是在唱“花房妓女”。但是他的听众却不这么认为,你酷,你有型有款,我就喜欢,我管你是苍白还是黝黑呢。谢霆锋们想看到的是不是“有意思”而不是那些怀旧的人看到的“有意义”。
鲍勃·迪伦在获得金球奖最佳电影插曲创作奖领奖时在台上扮了一阵酷,不过美国的孩子看到这个表情木讷像一个活着的木乃伊一样的人也许没什么感觉,因为没几个未成年人知道这个30年前的青年人的代言人。
假如这个时代没有罗大佑,一切就变得和谐多了,他不适时地出现,结果闹得一些人心里痒痒的,三十来岁的人终于也有机会撒一回娇。
(图片为本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