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什努之死》到《红羽》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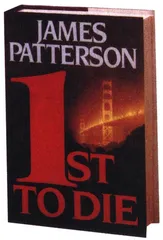
由于文学日益难以摆脱商品化倾向的滋扰,加之美国又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世界文学似乎存在着一种不言而喻的潜流:唯美国文学动向的马首是瞻。这也难怪,一部由英国作家撰写的《哈里·波特》在本土出版后滞销多年,但一进入美国,经过一番堂而皇之的炒作,立即莫名其妙地畅销了起来。但这也反过来说明:在美国出版发行的英文作品不一定都是美国作家的原创。上期我们曾介绍了第二代华人作家的小说《正骨医生的女儿》,本期我们再介绍一部印裔作家的处女作。
作者名叫马尼尔·苏瑞(Manil Suri),他出生于印度孟买,现为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数学教授。小说题为《维什努之死》(The Death of Vishnu),用评家的话说,该书“将孟买一所公寓中的生活和一名仆人的最终回忆结合在一部当代印度的喜剧中”。
故事开始时,维什努正在孟买的一栋公寓小楼的楼梯拐角处奄奄待毙。他伸出一只手,仿佛要挣扎着爬上高一级的楼梯。他刚刚呕吐过,混身都肮兮兮的。不过不必去管他了,因为他的问题差不多在第一页就结束了;而阿斯拉尼太太的问题才刚刚开始,她手中端着茶壶,正站在他跟前。她不想抬起维什努,惟恐他尚未咽气。她刚刚踮着脚尖走出来,给他端来每天早晨要给他喝的茶,如今却不知如何是好。首先,要清理这乱糟糟的场面,谁来付钱呢?再者,茶又该怎么处理呢?她肯定维什努是不能喝了,而且绝不甘心好好的茶就此糟践了,但她也清楚,给一个将死的人喝茶绝对是一件吉利的事。于是她便把茶斟进茶杯,而不去检查维什努到底是死是活,只要她尽职尽责,他的死活也就无妨了。
不管这栋公寓楼是维什努开发的、装修的还是长住的,整个故事全是在楼内及其周围发生。维什努长期以来贪杯醉酒,他曾给予原先一个仆人占用楼梯拐角的权利并为住在一层的两家印度教房客做杂活。姓阿斯拉尼和帕萨克的这两家人都是中产阶段,又彼此较劲。他们共用一个厨房,两家的女人不时地互相偷用东西,而两个丈夫若不是惧内,本可以结成联盟的。这两家的楼上住着富裕的贾拉尔一家,他们是楼里惟一的穆斯林,只是贾拉尔先生并不怎么虔信安拉真主,相反,他却对一切神灵都肯接受,并对周围的店铺一概光临。他们夫妻俩与楼下的邻居相处不睦,彼此猜疑,但他们的儿子萨里姆和阿斯拉尼家的不满20岁的女儿卡维塔却似乎不以此为然。顶层上住着的是一个光棍汉维诺德·塔尼加,终日沉湎于祈祷,几乎足不出户。
作家对楼中当前生活进行的干净利落又不乏喜剧色彩的叙述中插入了维什努死前的回忆。有趣的是,写当前生活固然用的是正常的过去时,而维什努的回忆过去则用了现在时,其含义是:垂死者在提醒我们,所有的时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像是一样的。于是我们便如亲聆维什努的母亲在他儿时的乡村中给他讲故事,她还溺爱地夸张说,他满可以成为上帝降临的化身。我们似乎还体验到他对名叫帕德米尼的妓女的渴想--这恐怕是他所知的最浪漫之举了。我们还能看到他眼见卡维塔长成娇柔美女时那种既有长辈的骄傲又有些许欲望的感受。
坦率地说,我们大家对印度文学(包括英文作品)都缺乏了解,大概只有少数专业人员研究较深。据介绍称,近几年有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全球铺张”、罗辛顿·密斯特瑞(Rohinton Mistry)的“社会现实主义”、阿米特·卓特胡瑞(Amit Chaudhuri)的几乎没有情节的“情感研究”,以及阿伦德哈蒂·罗伊(Arundhati Roy)“过热的喀拉拉”等等流派。其实,诸如殖民主义重压、印巴分治、战争及宗教暴力、水灾、饥馑和疫病这些政治局面与自然灾难都已提供了极丰富的背景,如何用来创作文学作品只是形式问题。当然像纳拉延(R. K. Narayan)则从印度教神学出发,置上述重大事件不顾,专写精巧喜剧故事。他虽为读者所喜爱,对后来的作家影响却很小。然而,本书这种公寓街区的场景虽然回响着密斯特瑞1989小说集的余音,但更像较早一些的作家纳拉延。这部小说的结尾会令人放声大笑,但合上书之后,那笑声就会变成抽泣了。这或许便是本书所反映的更深刻的现实吧!
本期上榜新书《红羽》据报道该是米芙·宾奇这位女作家退休前的最后一部小说了。该书讲的是汤姆·菲扎(Feather,本义为“羽”)和卡赛·斯嘉丽特(Scarlet,本义为“鲜红色”)的故事。他俩在烹饪学校同学而成为挚友,如今来到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开办了一家叫作“红羽”的饮食公司,此举令他们可敬的合伙人和家庭懊恼不已。全书叙述了这家新公司一年中的故事,而以卡赛的姐妹的那场期望值极高的婚礼为高潮。那位姐妹拉着她未来的丈夫及公婆回都柏林成婚,就为了要体会那地道的爱尔兰婚礼风味。全书的情节靠对话来推动,其中交织了许多惯见的内容:从无家可归的凄凉到女权及人工流产,从而使这部当代题材的小说洋溢着传统的主题。女作家宾奇以其简结清晰的笔法展现了一条真理:最终使一对对夫妻结合并构成牢固家庭的,毕竟是爱情而不是金钱。
书中描述的古朴的爱尔兰民族风情令人动容。由于爱尔兰人强烈的民族自尊和宗教情感,加之英格兰多年来对其殖民统治中阻碍其现代化进程,反倒使这里成了罕见现代物质及精神污染的一块难得的净土。这样的背景和真情的主题相互衬托,回荡着一曲遥远但又引人渴慕的圣洁之歌。 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