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141)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邹波 花蕾 路鹿 洪晃 帕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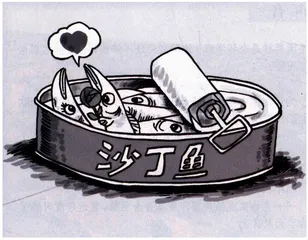
旅行和艳遇
文 邹波 图 谢峰
从表面上看,旅行是一次十足的户外冒险,但只要想想,我们是怎样到达那些地方的……事情好像就没那么简单:飞机,轮船,火车……在整个旅途中,我们几乎一直呆在沉闷的、运动着的、有时是飞翔着的小房间里,长途跋涉。
密封窗稀释掉大部分外景,到晚上,如果你乘坐华北到华南的夜行列车,只能当镜子用的车窗已足够让你烦的了;可要是穿越大西洋的夜间飞行呢--整整12个小时,在海拔数千米的高空,不知身在何处,完全丧失了方向,飞行又是如此完美,没有气流和云团,一片漆黑,机舱纹丝不动,那岂不是更可怕的事?--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绝望地回忆某次飞行:“我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恐惧,飞机永远停在了空中。”
于是,怎样熬过冗长而封闭的旅途成了旅行最重要的冒险。
你瞧,男人女人们在密封的小房间里百无聊赖,但终归该干点什么,可干点什么呢,环顾四周,发现只有两样东西可看:钟表和漂亮的异性。因此,旅行将充满艳遇,枯燥乏味的长途旅行尤其如此。
1941年,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有过一次难受的经历--搭乘小汽船从法国到南美。狭窄的船舱生生挤下350名乘客,接近赤道的时候热带旅行变得异常沉闷,这时候人类学家目睹了许多浓缩到最低程度的调情:“……船上乘客有些是年轻漂亮的女人,她们和其他乘客也已开始眉来眼去,某种感情也渐渐成熟……”
很可能是从这次旅行开始,列维-斯特劳斯对旅行充满了恶感,他开始生活在悖论中;一面否定旅行,一面出于工作需要,必须不停地旅行、必须把那么多时间浪费在船舱里、火车车厢里。在《忧郁的热带》一书开头他痛苦地写到:“我讨厌旅行……一个人类学家的专业中不应该包含任何探险、旅行的成分……这只会使人类学家平白丧失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有效工作时间。”当可怜的人类学家不得不那么紧密地融入“讨厌的人群”中,他也必须抵抗内心涌起的各种乱七八糟的欲望,但谁知道他能否抵挡那些诱惑?说不定人类学家真会忍不住爱上他的某个考察样本:女人,漂亮的女人,漂亮的陌生女人。
在春运期间的京广线上,旅行者随时都可能陷入孟买平民区那样狭促的环境,我们在人群里挣扎,不停地变换视角以抵抗疲劳,就像那些不停变换镜头的城市电影,通过变换挤迫的场景来避免窒息。饥饿、睡眠不足、过分拥挤、肮脏的环境破坏了陌生男女们的矜持和羞耻感--那些肉艳的姑娘们,她们不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却和你摩肩接踵,耳鬓厮磨……所以,在湄公河的渡船上,你会没道理地爱上我这个萍水相逢的男子,正如在上海亭子间狭窄的过道里,我不可救药地喜欢上新搬来的女邻居……
赖因哈德·西德尔在《家庭的社会演变》一书中谈到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欧洲的雇佣工人、学徒的居住状况时写道:“住房紧张,缺少床位,迫不得已产生了青年人身体的接近……一再发生儿童和青少年被同屋居住人奸污、乱伦、同性恋等情况……”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前后才渐渐减少:“……工人有了自己独立的住所,与邻居隔绝,与佣人分离,房间也有了专门化……帮工这种外来人从雇主家中解放出来,并纯化了雇主的家庭,教会所深恶痛绝的学徒与师娘之间的暧昧事件也减少了。”在北京,我常去的那个咖啡馆十分宽阔,我喜欢坐在靠窗子的地方远远看着那个弹钢琴的白衣姑娘,她那么美丽,但距我有10米远,我想,即使她再美,我们彼此始终保持那样的距离,我就不会狂热地爱上她。可谁知道呢,说不定有一天我和她不约而同出外旅行,在拥挤的南下列车上,我们被裹胁在人群里,彼此的身体紧靠在一起,就好像我们意外地堕入18世纪欧洲的青工宿舍,生活把我们卷到一块,我们强烈地感觉到对方的体温和心跳。虽然,以前我们一直保持着10米的距离,但现在,我几乎在搂着你呢,亲爱的,我肯定已经疯狂地爱上了你--我欲罢不能,身不由己。
可是,陌生的姑娘,如果你也在拥挤的车厢,在欲望横流、运动着、飞翔着的小房间里欲罢不能、身不由己地爱上我;如果你也在迷乱的夜间旅途目睹那些艳遇的发生……别说那是宿命。
伪自然爱好者
文 花蕾 图 谢峰
汤姆·汉克斯的《荒岛余生》一出来,我就买了张碟来看。当然我一向喜欢他,但这次光是电影名字就令我如同吃了兴奋剂般开心,更何况片商以“现代鲁滨逊”的名头来宣传呢。所以尽管有影评人批评这部一个人的戏太单调,我还是认真地看完这部片子的前90分钟,看汤姆如何在这个只有椰树的荒岛上生存。
我这样间接地热切地向往着自然。类似的例子有很多。
小学课本里曾有过一篇大概叫《森林里的一天》的课文,我至今念念不忘其中猎人用子弹和苔藓生火取食的细节。中学以前,我最钟爱的书是《鲁滨逊漂流记》,同样流落荒岛,他的生活显然比汤姆丰富得多,许多情节都被我有滋有味地咀嚼过多次。接下来还有吉卜林的动物小说,印第安那·琼斯系列……
去年《生存手册》一出来,我立即买一本来乱翻,不久即对塞莓与毒黑鼠李的区别以及如何用声光烟火来发求救信号倒背如流。
还有电视上的动物世界、人与自然、动物星球等等,至于DISCOVERY系列、国家地理频道,这是伪自然爱好者的最佳道具,哪能错过。
曾经一度,我少女梦中的理想对象是位现代“泰山”,我的人生理想就是与他携手整天在森林里东游西荡。
现在有这种回归自然情结的人也多,所以大些的城市会有什么野外生存俱乐部。我们小地方,没有这种热闹好凑,但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何况我积累了这么多生存经验。我家附近有个荒山,一直是我觊觎的目标。一个人去露营到底还是不够胆量,所以死缠烂打拉上了一向视睡觉为最佳休闲的男友。
当一个周末来临时,那个人下班回来看到我在客厅里,脚蹬皮靴,头戴遮阳帽,身着防水布的外套,下面是有若干口袋的牛仔裤,背上是同样有若干口袋,周围丁丁当当挂满了东西的大背包,它们分别是:装满水的水壶,军刀,手电,毛巾,还有一只小平底锅。目瞪口呆的他二话不说,把我的大包扯下来,发现里面计有:碗,一次性杯子,熟食和饮料(分带汽的和不带汽的)若干,色拉油,调味品,还有几包速溶咖啡,另有一袋化妆品占了小半壁江山,剩下的就是打火机之类的零碎东西。看那个人愣在那儿,我很小心地解释,你要背的是枕头和被子,还有最重要的东西在门口的旅游超市,我看过了,那只帐篷现在打折,原价380元,现在只要320元。
至今我提起这件事仍恨恨不已,我最终还是没能征服那座小山丘。而且因为男友罢工的缘故,我连吃带扔花了一个星期才算消灭了那堆食品。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发那么大脾气,我都声明了我这个自然爱好者前面有个“伪”字。惟一的纪念品是那锅,用来煎鸡蛋--一次煎一只--效果非常好。

好男人
路鹿
朋友小珂前不久像中了头彩一样地真的遇到一个“既英俊又聪明又有钱又文雅”的男人。她老是在我们面前夸张地甜蜜着,今天让我们闻她男朋友买给她的500元一小瓶的法国香水,明天又陶醉地描述着男朋友开车带她去郊外兜风,后天又惊喜地报告她发现他还是个国家二级运动员,游泳一级棒!
她最爱说:“我是他的初恋哦!一点也不骗你们,在我以前,他连别的女人的手也没碰过!这些都是他以前的同学告诉我的!”“骗子!”我们不屑,心里却似猫抓。
小珂继续招摇着她的甜蜜:“他跟那些只想吃女人豆腐的色鬼不一样。他可尊重我了,从来不乱动我。有时候我暗示他可以跟我亲密一点,他都会好温柔地告诉我怕我吃亏,要等结婚以后!咯咯咯咯……”“假正经!”我们同样夸张地表达着自己的嫉妒。
说实话,小珂的男朋友完全可以用“青年才俊”来形容。毕业于最著名的那所理工科学校,在那个人才济济的地方,他依然是十分耀眼的明星。他请我们吃饭,在那家幽雅的法国餐厅里,当他用最诙谐幽默又浅显易懂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他从事的研究涉及到我们用的餐具、各种各样的护肤品甚至是卫生巾的时候,我真恨不得在他身边小鸟依人的不是小珂而是自己。我相信在场的别的女友也都这么想。
小珂说:“我愿意给这样的男人洗一辈子衣服!”我们也愿意。
后来小珂的男友到美国去读博士后,是在世界上最好的那所理工科大学。说是他先走,然后就来结婚带小珂走。我们都不怀好意地提醒小珂:“小心陈世美!”小珂仍然一脸幸福地告诉大家:“我忘了强调一点--他还是一个人品一流的人!”然后就开始规划着要把她的那些家具在出国以前都送人了。她答应要把在宜家买的那张大床给我,另外还有一盏台湾铁艺落地灯。
时隔3月,就在我们以为小珂就要嫁掉,然后走掉,“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的时候,小珂来找大家,抱着每个人的膀子哇哇大哭一场。当即大家义愤填膺:“果真一个陈世美!”“不是……”“你还替他狡辩!”“他打电话来说他其实是一个gay……”我张大了嘴,惊异得舌头都要掉出来了。其他人也一样。“他说他从来就是,对女人不感兴趣,所以一直没有找女朋友。在国内的时候,他不敢声张,怕大家当他是怪物。后来他找我是因为被家人问急了,还有就是他也想试试能不能改过来……到了美国以后他说他认识了很多著名的中国gay,他们都是青年才俊……他说他要像他们一样勇敢面对生活!”
(本栏编辑:苗炜)

三妹子的情人
文 洪晃 图 谢峰
邪了门儿了,天一暖和,三妹子的老情人像雨后春笋一样都冒出来了。
“要一个GRANDE LAITIE,在这儿喝。”三妹子约了我在星巴克说说对付老情人的策略,她一没事就泡在星巴克。“你要什么?”她问我,“给你来个MOCHA 吧。”我们拿着饮料找了一个沙发座,我发现从柜台一路过来,三妹子东张西望,六神无主。坐下,喝口咖啡,三妹子深叹一口气,小身条在沙发里凹进去,还带着点牛奶沫的小嘴,抿着都笑到耳朵根儿了。老情人的出现让三妹子年轻了好多,那样子就像刚得了巧克力的孩子。
我们这圈朋友都公认,三妹子不是个漂亮女人,但绝对招男人喜欢。她也喜欢男人,特别是长得好的男人。说白了,三妹子是个好色的女人,我和她一个公司的时候,一个星期里她至少迟到三天,经常脸上带着一夜的快乐就来上班了。
“说吧,哪几个又冒出来了?”我问。
“我一个朋友的原来的男朋友,他们分手后不到一周,我在飞机上碰到他,我们都是出公差,去广交会,结果什么买卖没做,我们在酒店里没白天没黑夜地过了5天。”三妹子眼睛的焦点虚了,她已经又回到那个不见天日的小屋子里。
“后来呢?”我把她叫回来。
“后来?”她不看我,只看窗外的行人,“后来我们6年没来往,直到昨天晚上我们吃了一顿饭。”她叹了口气,接着说:“我们都在想,如果他不是我的朋友的朋友,也许就不一样了……”
我不想让她再说下去,三妹子现在有老公,有孩子,过得很好,但是看得出来,这个原来朋友的朋友让她动心了。
“还有哪个,说呀。”
三妹子终于又面对我了,满脸坏笑代替了刚才的一丝惆怅,眯着眼睛说“还有一个发小,从小就爱我,其实他也有家了,就是现在想把他和我的感觉解决一下,以后真的就当朋友,他就可以不想别的了。”
“也就是说让你友情出场一夜,是吗?”我得问清楚。
三妹子咯咯地笑着点头。
“还有吧?”
“还有一个是个大花匠,但是我们俩的确配合得最默契。”
“他想再和你配合一次,是吧?”我真不敢相信这个不起眼的女人怎么招了这么多男人。
“嗯。”三妹子认真地看着我说,“洪姐,我生孩子以后就再也没有过那种感觉了,可我还没到那年龄,昨天晚上我是多少年头一会有一种冲动,我想跟那广交会走。”她停了一下说,“那种感觉真的太好了。”
“行”,我斩钉截铁地说:“咱们安排一下吧,把三个都办了。”
“你不想劝我啊?”三妹子惊奇地问。
“这种事拦不住,”我站起来,“咱家老公和孩子呢?”
三妹子的样子有点恍惚了,“老公出差了,孩子在我妈那儿。”突然,她的态度转变,兴奋地说:“行,正好,我也生活一下。”她站起来,“走,陪我买东西去。”
出了星巴克,就在国贸里面转了一大圈,三妹子说,要买漂亮的内衣,一套黑的是和广交会,一套红的是和发小,还有一套白的和比较默契的。买完东西就已经是傍晚了,我说了声“当心点”,就分手了。
两个星期过去,三妹子什么动静都没有,我以为她和广交会私奔了。打个电话到她家,她老公说她出差去广州了。我也没敢多问。终于,昨天晚上三妹子打电话来,约我去她家吃饭。一进门就看见一派热闹、温馨的家庭生活,老公抱着孩子,三妹子在炒菜。酒足饭饱后,老公去哄孩子睡觉。我悄悄地问:“事儿都办完了?”
三妹子笑了笑,拿出一包东西塞我手里。说:“给你吧。”我看了看,原来是几个星期前我们一起买的内衣,标签都还在。“我还有这点冲动就够了,做不做,大概不重要了。”话音刚落,孩子在里面哭了,三妹子转身进屋哄孩子去了。
我被激情撞了一下腰
文 共同提高
对于一个曾经的共青团员来说,在一部意大利电影《咪咪的诱惑》里突然看见了毛主席的画像真是令人兴奋的事,那感觉仿佛突然被革命撞了一下腰。
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很激进,共同组织了学党章小组,清明节的时候,我们以为烈士扫墓为名去公园,学党章第五小组的组长在烈士纪念碑前念悼词,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人民英雄,还是永垂不朽的嘛!”这位同学后来做了领导,经常在有关场合用相同的语气发表演说,比如,“我们的妇女工作,还是姹紫嫣红的嘛!”“我们的麻将棋牌运动,还是欣欣向荣的嘛!”
毕业以后,我彻底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我的工作单位是台资的,整个公司近300人只有一个党员,不排除偶尔有几个未暴露身份的。在一个惊蛰的春季,劳资双方发生了利益纠纷,于是有好事者站出来呼吁组织工会,大家通过E-mail进行了热火朝天的贴大字报和串联运动。并且从上海分公司传来消息,当地员工已经组织了罢工。这让北方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压力,一般来说,上海人一向是因为小家子气和没出息被北方人瞧不起的,没有理由我们还没罢工让他们抢了先。
我是其中的激进分子,在那个寂寞而骚动的年纪,我为如此接近革命而自豪。我贴的大字报犀利、深入,而且雅俗共赏,很快就在群众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每天去食堂吃饭的时候,都有一些美女在旁边指指点点,还有什么比美女的青睐更能激发我的革命热情呢。
这气氛让老板很紧张,连忙找激进分子谈话;安抚坚定的保守派,实施内部分化;通过各部门领导向捣蛋分子施加压力;副董事长特地从台湾飞过来,发表了主题为“我也曾经是穷人,咱们都是一伙的”著名演讲。最后为了平复大家的情绪,资方做了让步,允许组织福利委员会,并承诺在方便的时候成立工会,福委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拔河、游泳和看电影。
令人泄气的是,在全民投票的时候,我以极低的得票率被踢出局。一位美女对我说:我没有投你的票,因为我觉得你不需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天哪,她一定是爱上我了,我想。
在这个惊蛰的春天,我把《咪咪的诱惑》当革命喜剧来看,钢铁工人咪咪和我们每一个不太坚定的革命者一样,随着革命的洪流起过哄,利用革命的便利条件勾引进步女青年,在资本家的高压下腐化变质、堕落消沉。米兰·昆德拉的《玩笑》里有过类似的情节,所有的一切激情最终被消解为悲怆的玩笑,我们只是被革命撞了一下腰而已,不过有的人撞得比较重罢了。
我的爱情原则
文 帕帕 图 谢峰
在一些容易勾起爱呀情啊这类酸溜溜的话题的场合,有时某人会问我你喜欢什么样的异性,若恰逢我心情不错,我会说起我的恋爱三项基本原则:一,她必须比我年长。二,她的学历必须和我持平或更高。三,她必须有过恋爱或婚姻的经历。
这几条对我来说就像基本原则一样不可动摇,尤其第一项,值得不惜代价去捍卫。翻开历史,我能找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拜伦自小就爱上了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很长时间里他一面渴望她母性般的温暖,一面为乱伦的恋情备受折磨;硬汉海明威17岁时狂热地追求着一位年近30的女子;邓肯的苏俄之行使她堕入与年轻的诗人叶塞宁的情网;乔治·桑也比她的蓝色情人肖邦大了6岁。《鹿鼎记》中韦小宝的七位夫人里,至少苏荃和阿珂要年长于他。我读福楼拜传记亦心有戚戚焉,他曾迷恋于名叫爱丽萨的少妇,她与人同居并有个女儿。福楼拜偷看她游泳,吻她留在沙滩上的脚印,夜里守望她室内的灯光,然而从未对她表白过。
关于这些爱着年长女子的男人,时常会被贴上冲动、幼稚、情感脆弱、离不开母性关怀的标签,但却很少有人指出那些对年轻姑娘心怀叵测的老男人们的虚妄,他们盼望的不过是对嫉妒和无奈的一点减轻,对自己成熟(也意味着腐朽)的证明罢了。
我的女友长我两岁多,在恋情公开后,反对纷至沓来,甚至包括与妻子同样年长的“同类”,理由不外女人易老,有违常规。我去国离乡后反对势力大增,劝说者有之,训叱者有之,最有趣的是自愿为她介绍新男友者,满怀道义感或说不清楚的热情,我发现很多人在此方面有比从事工作高涨得多的干劲。在这场斗争中,胜利者当然是我们,对手低估了我们的抵抗力。那段日子,我在去打工途中,读着秘鲁作家略萨的小说,当“我”吻着比“我”大15岁的远房姨妈时,感到了莫大的愉快。“我”发誓要当个作家,我想,他妈的,艺术家就该不同凡响。
我觉得有必要提及另一种人,彼特拉克热爱的劳丽恩只有12岁;爱伦·坡与弗吉尼娅结婚时后者13岁;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是类似情感的集大成,那些9~14岁的小生命是足以燃烧我们爱欲的小仙女。
现在我们看到,有两种男人,一种为大龄女人所迷醉;一种倒在小仙女的光晕之中。以正常眼光看,他们都是不正常的,怪异的,那么,哪一种更接近疯狂呢?
当我感冒或生病的时候,她总要吻我,不容回绝,她要我把病传染给她。我也如此。这是我们的一项游戏,一点甜蜜的小小的疯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