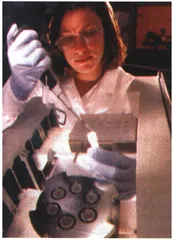艾滋病的药物危机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纪江玮)

艾滋病的救赎之路遇到药品价格的阻碍
马军(化名),一个眉宇间还有些稚气的小伙子,手里提着一大包药,正从地坛医院的诊室里走出。地坛医院感染科的张福杰主任在一旁一再叮咛:“快把药收好了,这么贵的药,千万别丢了。”这包药的确很贵重,价值近3万元,用3个月。
马军得的是艾滋病。他今年23岁,家在河南信阳农村。他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4年前,他准备参加国际劳务输出。做体检时,发现了感染。父母担心他经受不住这个打击,向他隐瞒了这个消息。两年后,1999年,马军开始发病,体质急剧下降,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为了看病,工作以后的一万多元积蓄全部花光。后来马军到北京地坛医院治疗,为国外的药厂做实验病人。这是他惟一的选择:艾滋病的治疗费用是每年100000元,这是他根本负担不起的。
记者见到马军时,他的身体状况不错,从外表上几乎看不出有患病迹象。马军告诉记者,他已开始工作了。每月能挣300多元。但这还远远不够:每三个月到北京来检查一次,3000元的检查费是要自付的。“这些钱主要是靠父母,大约占到家里收入的70%。”马军的眼圈有些湿润,“家里这几年没再添置过新东西。”大量的病人与昂贵的药费1985年,中国发现了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90年代中期艾滋病病毒的传染迅速蔓延。根据艾滋病有4~6年潜伏期的特点,当年的感染者大都开始发病了。根据卫生部最新的统计数字,截止到2000年12月底,中国在案的艾滋病感染人数为22517人,发病人数为880人。但由于漏诊与误诊的普遍存在,据专家估计,实际的感染人数应在60万左右,发病人数估计有6万人。
北京佑安医院的张可大夫对患者增加的情况感触尤深:“临床的压力非常大。而我们国家现在还处于一种非常缺药的状态。”造成这一局面的最明显的原因是,药费太贵,病人太穷。
中国的艾滋病患者在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居多。其中很多是因为卖血感染了病毒。据中国艾滋病第一大省一广东省的调查,无业人口、农民、工人占感染人口的73%。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的张福杰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了这一点:到该院诊治的大多数患者,“经济状况都不好”。
虽然自80年代起,中国就一直在做艾滋病药物的开发与研制,但至今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内目前尚无疗效可靠、经济实用的药物。在这种情况下,治疗艾滋病病毒的药物几乎全部靠进口。
国际上公认有效的疗法是HAART疗法,即俗称的“鸡尾酒”疗法。但其价格贵得惊人。默沙东公司的佳息患与葛兰素公司的双汰滋合用,每月的药费要7000多元,一年是80000多元。每三个月还要检查一次,一年的费用是12000元。艾滋病的治疗是终身的。这意味着患者每年都要花上100000元的药费。一旦停药,会带来病毒的反弹,产生其他副作用。
张晨阳大夫是地坛医院感染科的主治医生。在她所接触的100多个艾滋病患者中,只有四五个病人能自己负担药费。其他的患者只能像马军一样,靠为药厂做实验病人来获得免费治疗。但实验结束以后的治疗,是一个令人不敢多想的问题。
“这样高的药价在中国只有万分之一的人能坚持用。”北京佑安医院的张可大夫对本刊记者说。这个比例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有60万的感染者,而目前国内自费使用进口药物的患者只有五六十人。“这是一个救命的药物,病人都想要这个药,非常着急。可是价钱太贵了。”张可大夫说。
“总体上讲药物的价格是不合理的。价格过高。”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副主任邵一鸣博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邵博士认为,西方的药厂为了收回自己的研发费用,药价相对高一些,是可以理解的。但对比其他药物,艾滋病药物每年一二万美元的价格,高得实在有些离谱。除了药厂想获得高额利润以外,邵一鸣博士不认为还有其他的合理解释。况且,最近在南非,跨国医药公司迫于多年的压力,实行了大规模降价行动,默沙东公司的艾滋病药物降价90%以上。邵博士对此事的评价是:“这说明他们(跨国医药公司)的可操作幅度是很大的。”药物打一折还能赚钱,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价格里的水分有多大。敏感的价格价格对跨国医药公司而言是很敏感的问题。记者在采访世界顶尖的跨国医药公司默沙东中国分公司的时候,看到了该公司为解释价格问题而特意印制的宣传品,这在驻中国的跨国医药公司中是不多见的。一方面说明默沙东公司的公关意识,另一方面也说明公众对于价格问题的关心使得跨国医药公司不能再对此保持沉默。作为艾滋病药物领域的领先公司,默沙东受到的批评也最多。
对于中国病人最关心的降价问题,默沙东(中国)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屈婉文女士从默沙东(中国)位于香港的总部发来的书面答复中,并没有给予正面回答。屈女士在答复中强调,“药物的费用只是治疗障碍中的因素之一”。默沙东(中国)有限公司市场服务经理黄瑞莹女士在与本刊的接触中,认为这个问题,同时还受到操作层面上的影响,“价格并不是我们说降就可以降。价格是要由计委审批的”。
屈女士在答复中反复强调的是默沙东(中国)与国内医疗界的合作,比如赞助有关研究,支持艾滋病方面的宣传等。张可大夫也承认,跨国医药公司的确做了不少“感情投入”。“但是”,张可大夫说,“这些厂家还是要在降价方面做出努力。毕竟治病最要紧。能让病人得到药物是最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