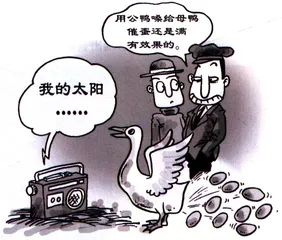生活圆桌(137)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陆离 愚妹 杨不过 劳乐)

天上地下
文 陆离 图 谢峰
回国前把和朋友的初次见面想了又想:两年不见,也不知道她们是胖了还是瘦了;是长发还是短发;个人问题是否得到解决或者有何变化;是否浑水摸鱼挣了不少钱买了房子?在国外期间不断有捷报传来,全是不相干的人的,在中国人的圈子里经过添油加醋一传十十传百,谁谁怎么怎么了,如何如何了得。我把他们的故事全安在我的朋友身上。在即将回国前夕给朋友们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里,我说回去以后等着她们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
约了在什么什么饭馆见,是朋友钦点的,没什么新意,好几年前我们就去过。我时差已经倒过来,在脑子里把到达那个地方的路线图画了一遍。虽说回来后还没出过门,我的感觉因为那个熟悉的饭馆顿时恢复过来一些。
朋友张开双臂在路口迎接我,怕我认不得地方,还怕我在外面遵守惯了交通规则不会过马路了,我感激涕零,和众好友一一拥抱。细心的1吸了吸鼻子,说你用的是国产的沙宣。我暗自佩服,在国外用的也是沙宣,我怎么就没体会出分别来。和众好友鱼贯而入饭馆,一一落座。10只眼睛盯着我上上下下打量不停。我问,怎么了?我是外星来客还是大西洋底来的人?5只头齐摇,不是,不是。2迟疑地说,你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两年之间,能有什么变化?我把脸凑近她们,指着下眼皮处给她们数新添的纹路。她们又齐摇头,不是,不是。我转移话题,还有6,6呢,不是说好要来吗?3答,她坐300路过来,现在正是堵车,还早着呢?300路?我脑子里转了一个圈子,300路不到这里,她起码还得倒一辆车。什么年代了,还坐公共?我不禁叫出声来。10只眼睛都瞪大了探照灯般扫过来,什么年代?就是现在这个年代,你去国不过区区700多天,难道地上一天,天上十年?我道出了实情,在外面听到的都是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全民买房买车的传言,像你等之辈,我以为早已告别公车啦。5姐妹直呼,谣言,谣言,还扔给我一个“切”字。
5姐妹把矛头指向我,你说说你在天上是如何过这700多天的,洋车洋房爽不爽?我?吃饭,上学,睡觉,只此而已。被你们逼着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4眉毛一挑,我看你学了西人的做派,把那些烂事当成个人隐私,越是严刑逼供越是不说。我喊冤枉。冤枉?谁信?她们仍旧众口一词。杀了我得了。我求饶道。等6来了,我原原本本从实招来,你们可不要怪我说的没有新意。5谅解地说,怎么会?那就等6来再说吧。瞧瞧你,这个不大方劲儿的。聒噪的麻雀们终于安静下来。
我叫来服务员,点了青菜豆腐和鱼。也许一切真的未变,连我们一起撮饭的菜色都是老三样呢。
在外滩
文 愚妹
我很喜欢的一位作者写过一篇我很喜欢的文章叫做《在海淀》。我想这是一篇迷人的文字,因为它让世纪末的北京几乎和20年代的巴黎一样迷人。在作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文字流淌中,海淀的麦当劳仿佛变成了左岸的咖啡馆,后殖民主义蛋筒飘散出和爱尔兰苦咖啡毫无二致的香味,而就坐在你对面的那个长发男子,也许就是下一个海明威或者毕加索。夸张吗?谁知道呢。
我喜欢巴黎,也喜欢海淀,但我在外滩。
就是你在电影电视剧明信片,或者你父亲老旧的黑色人造革手提包上可以看到的那个外滩,有整整一排叫不出名字的、古老的但是美丽非凡的建筑,对面黄埔江里面路过的船只和岸上路过的行人一样多。
每天早晚,这里都有很漂亮的男男女女提着公事包匆匆行走目不斜视,就像日剧里面东京地铁的人们一样。即使迎面就要碰到别人的鼻子他们也绝对不会改变行走的路线和速度,而只是稍微侧一侧肩膀,让过去,同时目光还是望着前方,很干练很沉着的样子。我很喜欢看这样的动作,觉得如果放慢了看一定会有一种舞蹈的美感,就像《新龙门客栈》里的梁家辉和张曼玉。有时候天凉了,风吹起他们的衣角,可以看到风衣的衬里和领带围巾是一个色系的。
从这里再往前走不远,就是十六铺客运码头,所以这里也常常可以看到用扁担挑着蛇皮袋行李的人们,他们的脸膛是枣红色的,他们的领口和袖口露出棉毛衫的桃红和海蓝。有时候走累了,他们就在123车站边的小食铺里买上二两生煎馒头,然后把行李卸在路边,就坐在蛇皮袋子上慢慢地吃,一边听轮船的汽笛声。有时候他们小心翼翼地问路,像回答老师提问的孩子,紧张而腼腆。他们的乡音还很重,听得懂的路人就会很快地告诉他们,听不懂的就说一句不知道,然后轻轻地走开,继续走路。这个时候,江风吹得人的喉咙毛毛的,他们呼吸着同样潮湿而冰凉的空气。
这里有著名的和平饭店,是以前犹太人用贩卖鸦片的钱盖起来的,里面有很好吃的小笼包子和不怎么好听的爵士音乐。罗大佑来上海开演唱会的时候就住在这里,走的时候带了一个水晶吊灯,由于花样太美丽繁复,需要拆开来分几次运走。
我每天每天穿着牛仔裤背着帆布包听着张楚在这个地方出没,渐渐地养成不戴手表的习惯,在这里这算不上什么恶习——这里有海关的大钟,而它永远会是一丝不苟地准确。
在外滩,不要问我喜不喜欢这里,我只是经过这里。这里很美丽,但是我不会为它停留下来。
暗恋
文 杨不过
一次老同学聚会,在某人家里大吃了一顿后,没人洗碗。不知道谁想了个招,每个人讲个自己的隐私,谁不愿意讲就去洗。本来以为总有人不愿讲,结果每个人讲下来,几乎都是自己小学甚至幼儿园时如何暗恋班上的小男生小女生,这使我们既逃脱了洗碗的厄运,又不算骗人。
后来我们总结说,一个人要是从来没暗恋过谁,那肯定不正常。然后大家谈起自己当年的暗恋对象,都是一阵唏嘘。那时候水灵灵的小丫头,现在都胖啦,而且还化着吓死人的俗艳的妆,穿着把身上的赘肉勾勒得一清二楚的紧身超短裙,对时间的流逝完全抱着视而不见的大无畏态度。风度翩翩一用中小学生的眼光看——的小小少年,连肚腩都有了,让人不忍心看,还整天惦记着去市场买点便宜货。
我当然也没法子免俗。从小学一路恋过来,暗恋的对象包括同桌、邻居、师兄、体育老师、书店售货员,以及初中的学校里一个年轻英俊的电工。而这无数次暗恋里,最让我尴尬的是大学四年级。那时候忽然喜欢上了一个年轻老师,于是一改逃课本色天天去上课,老师对着空气笑一下就心醉神迷得不能自己,还特别积极的坐在第一排,用极其崇拜的目光盯着他目不转睛地看,最后搞得所有的同学都受不了,坚决要求我别去上课了。
后来临毕业吃散伙饭时,所有人都哭得稀里哗啦,但最丢人的还是我。在半醉半醒里,以及一些家伙的怂恿中,我迷迷糊糊地抱住那老师的胳膊,大哭道:“老师,我暗恋你很久了……”第二天醒来,听别人讲述那一幕,羞愧之极,从此再不敢见那老师一面。
就这样结束了大学时代,原以为暗恋这事儿已经离我很远了,但最近,我忽然老夫聊发少年狂,恋上了同一个城市冤家对头的某报社的某位才俊。我不顾自己20多岁的高龄,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傻丫头一样,刻意出现在他经常出现的地方。正好有个好朋友就是他的下属,于是我经常打着找老同学的幌子混入敌人内部,喝杯水啊什么的,眼睛骨碌骨碌转着,希望老天垂怜我,让我能见他一面。朋友问我:“你是不是想请他吃饭?”我大喜,以为他这么善解人意,谁知他来了句:“你排着队吧,想请他吃饭的小姑娘比考托福的还多。”
整天在朋友那儿泡着,发现没什么用,除了去洗手间,他基本不走出自己的办公室。我又想了一招,他们报社有个内部网,报社的人都经常出没在上面,我先贴了一段“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自以为十分感人,却被众人狂骂曰:“探讨业务的地方怎么能有这种伤风败俗的东西”,后面还有好几个惊叹号。
脸红了一下子,我忍不住又写了一句:“某某,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一副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口气。没想到一个坏小子在下面跟贴说:“等你赢了整个世界,再来找我吧!”
pavarotti
文 劳乐 图 谢峰
我第一次听说帕瓦罗蒂的名字是从一篇科学趣闻里。那篇小文章在讨论人类的声音有多大力度,举出的例子就是帕瓦罗蒂的高音C,说根据科学家测量:帕瓦罗蒂在唱出高音C时,他的声音的力度足以震断一根船缆。那时帕瓦罗蒂是我惟一听说过的出名的外国歌唱家,所以我很自然地把他奉为歌唱家中的第一号人物,就像我那时相信国外只有一个叫理查德·克莱德曼的人最会弹钢琴一样。
后来我知道了更多外国歌唱家的名字,尤其是老和帕瓦罗蒂的名字连在一起的那两个:多明哥和卡雷拉斯。我还知道了多明戈出道前是一个斗牛士,卡雷拉斯得过白血病但没死,帕瓦罗蒂需要减肥;这三个人的共同特点是都绯闻缠身,他们三个站在一起时叫“三大男高音”。不过我感觉自己早年心目中的英雄:帕瓦罗蒂仍是三大男高音中最出色的一个,因为另外两个人都不会他那手用高音C震断船缆的“绝活”。
但我从没听过帕瓦罗蒂唱高音C,而且后来我又知道了那首让帕瓦罗蒂出名的有高音C的咏叹调其实是在一出很长的歌剧里,要坚持听到那个高音C得有很大的耐心。目前我只在一些电视转播的音乐会片断里听到帕瓦罗蒂拖长声音逗和他同台的流行歌手唱《我的太阳》;如果三大男高音都出现,音乐会能更热闹,因为会出现声音拖得更长的《我的太阳》。
前不久我听说三大男高音要来北京开音乐会了。虽然已经对看到“震断船缆”的表演不再抱希望,我还是有些兴奋。但兴奋之余我又听说这场音乐会的最高票价是16000元。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很不划算:今年年初多明戈自己在上海开音乐会时最高票价不过3000元,这次只是增加了两个人,票价最多再加6000元。懂行的人告诉我票价不能这么算,因为这次的票价是和国际接轨:在欧美,很多上流社会的人是以能够参加三大男高音的演出作为他们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的。但另一个更懂行的人的提醒让我彻底打消了听这场音乐会的念头。他说男高音过了更年期后声音会出现变化,弄不好会因为缺乏雄性激素变成“公鸭嗓”。最后我决定回家去听几天前刚买的一张CD,那里面是一些17世纪前的阉人歌手演唱的曲目。
(本栏编辑:苗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