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137)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孙少安 古应春 刘英 胡安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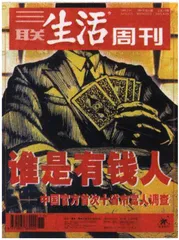
中国的穷人是真正的穷人,但是富人却不怎么像富人。在中国富人身上,我们很少能够看到金钱的魅力,那种健康的、让人着迷的社会推动力。
陕西 孙少安
开汽车的权利
不久前,由上海市环保局主办的“摩托车与环境问题研讨会”上,一位城市交通问题专家建议:轿车进入上海家庭的进度不宜人为地加快,未来10年内上海仍宜发展交通工具多元化格局,应尽速发展电动自行车使之成为城市多元化交通工具中的一支新军。
据报道,这位专家说从上海目前的交通现状看,私人轿车增加,必然会造成交通不畅。据海外测试资料,由于交通不畅,不少轿车不得不把车速放慢,当车速从每小时30公里降为每小时10公里时,其燃料消耗将增加一倍,其废气的排放量也将增加一倍。在这种情况下倒是摩托车或自行车能在车流中穿梭,因为测试资料显示,摩托车在行走时占地是汽车的1/2,停车时是汽车的1/4,而其燃料消费量不到汽车的1/3,因此在现阶段上海的道路交通尚未改善到尽善尽美的情况下,让一部分摩托车取代私人轿车,有利于缓解上海的城市交通现状。
这位专家还指出:上海未来10年内发展的多元化交通工具中还应包括电动自行车,这被当今世界一些城市交通问题专家认为是具有时代性的更轻便的个人交通工具,在未来二三年中有望成为城市交通工具多元化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无论从经济上和环保上都将为市民带来方便和实惠。
真的很奇怪,提出这样观点的人也能被称为城市交通问题专家。环境和交通拥挤当然是要解决的问题,但这样的观点无疑和说穿旱冰鞋去上班是城市发展的主流一样。或者进一步说,和在困难时期跟中国人说多吃肉会得高血脂,还是尽量吃窝头没什么分别,中国需要的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还没有条件享受现代化之后的担忧。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没有开汽车的权利呢?
上海 古应春
给《三联》的一封信
因为曾经为我们带来王小波的杂文,《三联》一直是我最爱的杂志,哪怕在王二故去之后。
而最新一期上关于核酸营养的文章,让我恶心。
只要是学过高中物理学的人,都可以明白永动机不能成立,无需永动机专家或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来证明。同样,只要有最粗浅的生物化学知识,就能明白所谓的核酸营养学是什么玩艺。而且,我听说过生化学家、生态学家、营养学家、分子生物学家,而所谓的核酸专家,是头一次听说,而且什么是真正的核酸产业?骗子就是骗子,不要把自己和产业联系起来,就像制造假药假酒的厂家把自己列入“产业”,要求保护一样可笑。我有朋友就是在搞真正的核酸产业,反义核酸制药,为什么这些真正的有效有据的核酸产业没有出来呼吁什么“保护”,倒是只见到那些“神妙”无比的“保健品”在那儿大喊大叫?
当我还是大学生物系的学生时,方福德是个让人尊敬的名字,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一地步,也许是为了钱,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与骗子同类,我也懒得再费唇舌;但如果只是当初误上贼船,为了自己的面子而一错再错,我想以一个后辈身份请方先生注意;勇于承认和更正错误,比维持错误更能取得大家的尊重。
我不知道所谓的“核酸专家”与“分子生物学家”的区别是方先生还是记者先生提出来的,如果是方先生,我想这笑话也就太大了点,如果是记者,我想请他去查一下:1.所谓分子生物学家,到底研究的是什么??(嘿嘿,我想我话都说到这儿了你不会猜不出来吧??)2.那些诺贝尔奖得主,到底是因为对核酸的研究得的奖,还是因为对狗屁的研究得的奖?
作为媒体,有责任告诉大家各方面的信息,无可厚非,但误导性的不在可宽恕之列,如果有了一个偏向性,希望下期能见到另一个偏向性信息提供给大家让人们充分了解,自行判断。
(编者注:这篇文章选自本刊论坛,署名“疯和尚”)
怀念左大人
新华社报道,在陕北洛川县城南北几十公里国道两旁,曾满是高大的杨柳树,一到夏秋时节荫翳蔽日,清风送爽,称得上是真正的“绿色长廊”。1999年10月左右,县里忽然决定搞什么“绿色长廊工程”,要求将这些杨树柳树全部砍掉,然后栽上松柏和花草。
农民张建国说:“砍树的时候说砍就砍,不论大小,一棵都不准留。当时路两边到处都是砍倒的大树,看了让人心疼。砍完都快一年了,才栽了点松树,种了些花和冬青。可这些花花草草根本不适合我们这儿的气候,又赶上大旱,现在差不多也死完了。”
在洛川至西安的国道上,记者看到这样一块高高矗立的牌子:“进入延安市绿色长廊工程。”可一路看下去,除了偶尔见到一两株小松树,实在看不出一些干部绘声绘色描述的“绿色长廊”在何处。
在西北的恶劣环境中,一棵树要想长大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除了荫凉,杨树和柳树对西北人可能还有更多的意义,在本世纪初的西北大旱灾中,杨柳的树叶和树皮不知救活了多少西北人的性命。在甘凉大道上,最著名的就是“左公柳”,是左宗棠西征时种下的。如今,不会有人指望受灾的时候靠树皮度日,但是看到洛川领导的做法,我们却无法不怀念左大人。
西安 刘英
谁在威胁粮食安全
国家最近公开了一组很少见报的数字:去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6.07亿亩,比上年减少9000万亩。新华社评论员为此提醒,尽管全国粮食储备和商业库存充裕,但播种面积的持续减少仍将危及粮食安全。这是继1996年后,中国官方针对粮食安全发出的又一次预警信号。
现在有一种比较通行的判定,就是把我国粮食面积的减少归结于粮价过低,归结于农村税赋过重,归结于农产品结构调整过快。甚至还认为粮食潜在的安全因素,与种子安全、化肥安全、农药安全一揽子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有关。简言之,就是假冒伪劣太多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些当然都切中了要害,但有个强烈的呼声还是被忽略和淹没了:那就是粮食在政府保护价下的正常流通至今无法兑现!
首先是“卖粮难”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复杂到所有的农村问题都集中在这个焦点上。村长可以把各种摊派塞进粮款结算,电管员可以把吃喝拉撒划到粮款头上冲销,乡里的强力部门同样可以在粮款扣除上念歪经;其次是国家关于私商粮贩不能直接进村收购的三令五申形同虚设,内外勾结的情况已见怪不怪。最常见的是私商粮贩违规到村头收购,然后做通粮库将新粮陈粮掺在一起“交售”给国家,这就等于政府把鸡交给了黄鼠狼看管。更要命的还有,地方过大的粮食事权无法削减,粮食体制改革难以深化。说刻薄一点,就是粮食的“官饭”、“派饭”、“补贴饭”还变相地端着,直至可以像“基金黑幕”那样倒账、对冲,最终把巨额亏损转嫁给国家和农民。当然,陈粮拍卖也不是没空子可钻,至少能通过轮换与私商粮贩结为同盟向国家“搂兔子”。照此下去,纵然盖多少个中央储备库也是白搭。
有关粮食问题,本届政府算是殚精竭虑了。但假如打不掉基层粮食收购那种“猫鼠相好”的关系;抚慰不了农民“卖粮难”到“卖粮赔”的伤痛;即使在农村讲多少次“三个代表”,即使派多少个干部动员农民稳定种粮面积,都可能因积重难返而事倍功半,更难指望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减轻农民负担和提高农民收入了!
银川 胡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