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的方式
作者:王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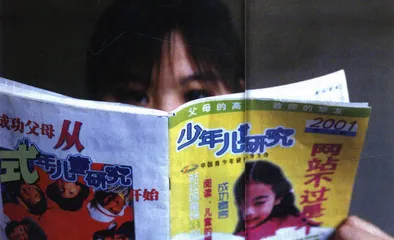
我愿意接受女儿的挑战
童谣风波
让我们再把这些让人闻之色变的“童谣”引述一下:
现在学生真糟糕,
爱哭爱笑还爱闹,
天天上课都迟到,
迟到也不喊报告。
考试作弊有绝招,
又能偷看又能抄,
个个像个韦小宝,
捉弄老师有技巧。
现代老师武艺高,
个个都会扔“飞镖”,
教学更是有法宝,
不是作业就是考。
班里纪律真是妙,
不能说话不能笑。
学生胆敢大声叫,
马上把他父母找。
……
准确地说它们不是童谣,比起“小小子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温婉动情的老调子,它们加入了太多成人式针砭时弊的义愤。但它们来自校园,现在由孩子们口口传唱。造成这一局面的罪魁祸首据称是《少年儿童研究》,报纸和电视都给它作了“污染孩子”的定性,青岛那边除了5个校长要联合抵制这本胆子过大的杂志之外,还有5个家长正积极酝酿把它送上法庭。
想出这一收集童谣再把它刊登出来的“馊”点子的,是中国少年儿童研究中心的知名研究员孙云晓,他同时又是《少年儿童研究》的主编。31首产自校园的童谣——或者说顺口溜、打油诗在这本刊物的2001年1、2期合刊上被隆重推出。平日里只是把它看作家长读物的孩子们,一时间竞相传阅,他们读给老师听,在公共汽车上大声朗读,回到家打电话讲给爷爷奶奶,以为成人会像听相声一样和他们一起开怀大笑。
“我经常为了保护这本杂志的生存,宁愿把我很多较为激进的观点发表在别的地方。没想到,这次在本来没有很大争议的事情上出现了这么大的波折。”孙云晓说。这个没事就到学校和孩子们聊天的研究者,很早就发现孩子们中有非常精彩的语言,“他们形容老师生起气来是‘五官错位,紧急集合’,谁能用8个字就描绘了老师的发怒啊!当我第一次听到‘我要上学校,背着炸药包’的时候,很震惊,这里面既有孩子们痛苦的声音,又充满了调侃的态度。为什么不让家长了解孩子们真实的感受呢?”
但孙云晓的意图被指责为只顾发行量的哗众取宠。老师们感到自己成了这些童谣恶意攻击的重点,而像“李白乘舟不给钱,一脚把他踢下船。桃花潭水深千尺,不会游泳就玩完”之类篡改唐诗的“无厘头”,多少让家长惶惑不已,怎么背唐诗就记得没这么快呢?它们在帮助家长如何教育孩子的严肃刊物上登堂入室,引起的愤怒可想而知。据悉,杂志正因此事蒙受发行上的损失。孤独的战斗
如此饱受争议的局面孙云晓并非未经历过。8年前,根据中日少年在内蒙古的探险夏令营中发生的故事写作的报告文学——《夏令营中的较量》经《读者》转载,曾在全国触发了一场针对现有教育体制的激烈讨论。事关民族荣辱,中国的孩子就真的比日本孩子差了很多?我们的教育真的输给了日本人?一系列令人不安的发问连同反驳文章《杜撰的“较量”》,把各种爱恨情仇加诸到了孙云晓的身上。
孙云晓从一次活动中提炼了整个社会广泛的真实危机,最终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甚至《人民日报》也投身进来,为这场持续近一年的大讨论留下两个重要声音,“黄金时代缺少了什么?”“为孩子改造成人的世界”。但这一次,没有一致对外的目标,面对和反驳的只有自身,孙云晓就显得孤单起来。
“这次反对我最激烈的,竟是平时最支持我,与我关系最密切的老师和家长们。”孙云晓说,“我们一直得到信任,很受欢迎,当我们想进一步实现我们的主张,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时候,却在无意间触发了一座大火山。我这才知道自己对于社会的进步估计得过于乐观了,实际情况复杂得多,人的观念的变化是最艰难的。”孙云晓说。
“为什么让孩子那么开心的东西,大人却那么紧张?是不是我们的教育太规范了,太习惯于净化教育?必须用一种方式说一种语言,却让儿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孙云晓说,“这些校园童谣其实代表一种信号,是孩子们内心压力的宣泄,大人应该有宽容力与理解心。我们的真正目的也在于此。有人为这种‘低级趣味’大惊失色,怕教唆了孩子,我并不担心。教育不能太脆弱,五加二(五天上课两天放假)等于零的效果,就说明我们给予孩子真实的东西太少了。”女儿的反诘
就在半个月前,孙云晓18岁的女儿恰恰对父亲的宽容力进行了一次公开检验。2月14日,孙冉在《中国青年报•冰点》用整版篇幅,发表《我眼中的日本同龄人》一文,与2000年10月父亲的《夏令营中的较量》的续作《千年警世钟》的观点形成明显对比。
“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孙冉说,“父亲指出,中国孩子在许多方面都不如日本孩子,真的是这样吗?父亲写‘较量’的时候我还小,还不懂,但当我长大了,有过多次和日本同龄人接触的机会后,我有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孙冉利用两次赴日参加民宿活动,调查了日本15个省的学生。通过发放的115份问卷(回收了91份有效问卷),她得出结论,“我的关于中日孩子勤劳问题的调查报告发现,中国的孩子在学习、家庭劳动方面都比日本孩子强,在体育运动和社会劳动方面不如他们。我们这代人的素质并不比日本同龄人低。”
孙冉的文章被敏感的新闻界视作一次女儿对父亲说“不”的例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谈话节目甚至把演播室搬到孙云晓的家中。孙冉在访谈中坦承,她认为父亲有些问题的看法过于偏激,譬如对爬山前夜中国孩子兴奋地嬉笑不睡觉、爬山途中一路高歌的批评,“我觉得搞得过分紧张不太好,作为孩子没那么多想法,本来就把这一切看作是一种体验,大人却看着我们走每一步都担心。对问题过于敏感、过于主观可能是搞儿童教育工作者的通病。”女儿甚至说,大部分时间对父亲的教导听不进,“因为这些事毕竟离我们还很远。”
“到底是我的心态太沉重了,还是他们的心态太轻松了呢?”孙云晓不胜感慨地自问,“我还是很愿意接受女儿的挑战,只要我女儿是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不过他也知道,如果女儿的文章是在当年《较量》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发表的,他很可能会接受不了。时间增长了他的容忍力。“所以,以后我们影响成人的方法会变化,要用更稳妥更懂得他们的顾虑是什么的方式让人们接受。”孙云晓说。 童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