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吃一颗革命果子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于)

现在的社戏至今还沿续鲁迅笔下的形式(谷嘉 摄/Fotoe)
《鲁迅先生》
去年,革命史诗剧《切·格瓦拉》在首都剧院小剧场上演,演员情绪饱满地表演,观众情绪更饱满,不少人流下了眼泪。张广天怀抱吉他坐在舞台边,应该很满意。因为他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方式诉说革命。看《切·格瓦拉》的很多人是冲着时髦来的,但不小心就吃下了革命的果子。今年,张广天又准备了另一粒革命果子:民谣清唱史诗剧《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的著作是“毛选”外中国最有名的读物,连带“赵家的狗”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条狗。只要跟对中国文学史有一点了解的人提那条狗,都能接着说“何以多看我两眼呢?”还有的人能完整地背诵:“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多看我两眼呢?我怕的有理……”通常人们呈现鲁迅先生这一经典段落的方式是叙述,现在张广天给它谱上了曲,可以唱了。能唱的不止这几句话,还有鲁迅先生几首著名的诗。经典文字被配上音乐不是新鲜事,《毛主席语录》就曾经在特定时刻被全民颂唱,但对现在年轻一代来说,这样的做法还是有些不可想象,如何能把音乐和“我以我血荐轩辕”捏在一起呢?
除了给大家吃革命果子外,张广天还有更大的抱负,就是创作出具有本民族特性的音乐剧。中国没有自己的音乐剧是不争的事实,造成这种局面既有技术上的原因,也有认识上的原因。在张广天看来,要写出中国音乐剧,就必须同时了解传统音乐剧和民间音乐。尽管话说得很谦虚,但他仍然认为目前在国内,他是最有把握写成音乐剧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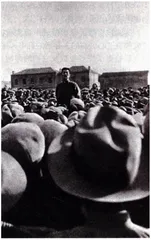
鲁迅在北大讲演
要写音乐剧,首先要面临的就是中国文字发生方式和音乐的关系。现在的大陆流行音乐不争气,屡屡被人骂,而且越骂它越糟糕。有的乐评人干脆从根本上否定了在中国创作出流行音乐的可能性,理由是流行音乐是为西文诞生的。这个理由现在又被用来否定创作中国音乐剧的可能性。而在张广天看来,正说明现在的音乐形式需要改革了。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先生早就说按字行腔,“文革”时也有人写出过《论词腔关系》,可见不是中国文字不行。
《鲁迅先生》的剧本已经写完,如果顺利的话,5月份观众就可以看到舞台上且行且歌的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了。
革命的文艺炒作
很多人和张广天聊天的时候会产生时空错位的感觉,因为他的革命性太强了,连《切·格瓦拉》的炒作也被他定性为“革命的文艺炒作”。此次选择鲁迅先生的故事作为创作题材,也有着一定的“政治目的”。他要通过这出史诗剧来恢复鲁迅先生精神的精髓,强调鲁迅不是一个精英分子,而是认识大众力量的革命家。
对人民的强调,使得张广天被划入“新左派”。他不认同这个称号,觉得“毛主义分子”的称呼更确切。原因之一是他认为现在的那些“新左派”名不符实,并不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在评价别的艺术作品的时候,张广天的标准依然是革命与否。他把利用日常生活的趣味、沉溺于现状的作品统统划入庸俗的范围。至于他自己的作品,他曾撰文一篇,说资产阶级用时尚美学来搞精神渗透,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只要作品中有斗争性和创造性,甚至是破坏性。人们对类似张广天这样的艺术家最大的怀疑是,他会不会迟早也被他所反对的东西吞没。《切·格瓦拉》剧场外卖的T恤不能不让人这么想。(图片均为本刊资料) 切·格瓦拉张广天音乐剧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