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旅途》到《波斯新娘》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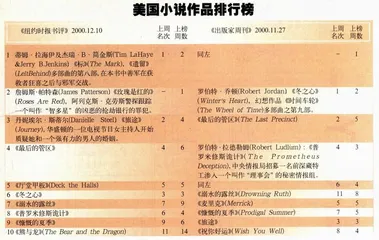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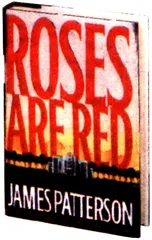
我们又看到了丹妮埃尔·斯蒂尔的作品上榜。我们委实难以说出这部《旅途》是她的第多少部作品或者这是她的小说第多少次上畅销榜了,但我们可以肯定她是世界上作品最畅销也是最多产的女作家。她的每部作品精装本可销上百万册,而平装本还要多出两三倍。在已出版的近40部作品中,大多已译成30多种文字,在全球发行了4亿多册。她现在的年收入高达250万美元。她写的多是言情小说,但她不同于她的英国先辈简·奥斯丁和布朗蒂三姐妹——在她们的时代,囿于家庭条件和道德风尚,都生活在极其狭窄的圈子里——现年53岁的丹妮埃尔·斯蒂尔有着独特的个性和火热的感情。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聪明而又任性。她连大学都没读完,却成了举世闻名的小说家。她18岁就嫁给一位26岁的出身法国名门的银行家,现在已经有4次婚史,其中的第二和第三任丈夫分别是银行抢劫犯和吸毒犯。她的婚外恋史也浪漫得如同传奇。我们当然不能说她是在“体验生活”,但这些一般人罕有的经历确实为她的小说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如今她这部新作,以电视台节目女主持人为主人公,她嫁给了一个有权势的人,但她的婚后生活使她提出了种种疑问,不啻是作家自己的反思。
倒是一部未上榜的新作令人感兴趣,那就是詹姆斯·巴肯(James Buchan)的小说《波斯新娘》(The Persian Bride)。
詹姆斯是英国人,祖父约翰·巴肯爵士(1875~1940)是苏格兰政治家(曾于1935~1940年任加拿大总督)和惊险小说家(作品有《三十九级台阶》、《绿斗篷》等)。他本人曾任《金融时报》的驻外记者。虽说很多记者都梦想当作家,但成功者却只在少数——他们有幸将写报道练出来的清晰、简明的文笔用于小说。评家认为,他目前虽然在美国还没什么名气,但这种情况不会延迟太久。
《波斯新娘》是他的第六部小说,以20世纪最后25年的伊朗为背景。
故事的主角和叙述者是英国青年约翰·皮特——一个很让人误以为是格拉罕姆·格林笔下的主人公。他从不知晓自己真正的父母,也未在书中忆及自己任何有意义的往事。他一心耽于外出周游,1974年春首次出国,沿着所谓的“嬉皮士路径”走过慕尼黑、贝尔格莱德和伊斯坦布尔,最终到达伊斯法罕。他选择这座波斯古都落脚,只是因为听说那里很美,再无别的理由。
故事就从皮特到达伊斯法罕开始。他剪掉了他的长发,伪造了一张大学文凭,以便取得教授英语的资格。他就此得到了在当地一所语言学校任教的工作,校长却警告他必须“像狮子一样强壮”,否则,他的学生便会杀死他。皮特十足天真地答道:“先生,我能应付。”校长却说:“天啊,你做不到的,约翰,到时候我只好解雇你喽。”
原来,皮特的学生全都是些魅力诱人的妙龄少女,她们穿着淡蓝色的裙子,齐踝白短袜,披巾轻拂。他当即就倾心于一个聪明伶俐、身材瘦长、眼睛漆黑的姑娘。她名叫施琳,是王家空军一位将军——法拉姆的女儿。“她的亲吻是我18年来遇到的惟一一件事:其余的一切便是睡眠和盲目了。”不消说,法拉姆将军没看上这个女婿;这对青年只好秘密成婚并出逃。他们得到了驻伊斯法罕的好心又有毒瘾的苏联顾问将军的协助。他用一辆丰田吉普把他们送到海湾一座小镇上一处废弃的苏联人的住所。这对年轻人在那里沉浸在越来越深的爱情中,幸福地生活了一年多,施琳生下了一个女孩。他俩意识到国王的秘密警察迟早会抓到他们,便设法离开伊朗。他们的计划落空,皮特与妻女失散了。
可怜的皮特的命运就此每下愈况。他在满目疮痍的伊朗四处流浪,寻找他的家人。他用一首诗来总结自己的命运:“幸运、欢乐、悲伤和我/一起栖身于这个世上。/幸运躺倒,欢乐跑开;/只有悲伤和我继续游荡。”
本周法国书评
一组流动的拼贴画
英格丽德·卡文是个德国女人,生于战后德国,活跃于七八十年代的德国歌坛和影坛,德国最著名的电影导演赖纳·W·法斯宾德是她的丈夫,法国导演让—皮埃尔·拉赛姆(碧姬·巴铎和简·方达等一系列漂亮女人的丈夫)和时装设计师伊夫-圣罗朗是她的好友。法斯宾德已经死了,他的遗物中有些手稿,没有题目,内容是关于英格丽德的,大概分8个部分(也可说是章节或者场景)。近期一本名为《英格丽德·卡文》的书在法国畅销书榜连续排名前列,但它不是传记,而是小说,作者是法国人让—雅克·舒尔,他与英格丽德共同生活了20多年,可能是出于对法斯宾德的崇敬,更可能是出于对英格丽德的爱情,他用前者的手稿给后者写了书。
主人公是英格丽德和夏尔,夏尔就是作者,假名不是为了掩饰身份,而是他不敢用第一人称写作。那些大名鼎鼎的男人都是小说里的人物,比如伊夫·圣罗朗“走路拖沓,好像髋部要用点力气才能拽动整条腿,声音柔和,但又略有异样,好像舌头有点小毛病”。英格丽德也是被细细审视的,她的少女时代不愉快,她的优雅并非自然,她对身体的运用也不自如,在那个喜庆和消费的年代,她知道那种奢华生活的脆弱,她的内心其实有着隐秘的慌乱……
这本小说刚在法国得了文学大奖。《解放报》书评说:“它有很多种读法——70年代纪事、美学宣言或者私人日记。它最成熟之处在于整个的统一性,仿佛多种材料的完美糅合,让人完全看不见缝合的痕迹。”《新观察家》说,“在字里行间,尤其是书的最后部分,舒尔最终立起了一个形象:一个歌手,一个女人,这同时也是小说本身的形象,就像一组流动的拼贴画,神奇的,同时又是犹犹豫豫的,直到最后才确定下来。走近英格丽德的歌声与生活,走近法斯宾德、圣罗朗和舒尔,也就是走近了他们那个年代的梦想。” 文学小说伊斯法罕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