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或者住人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三联生活周刊)
一 农居
开始全是农村。那时候大伙都在大地上诗意地喘息。喘够了或者喘得实在不行了,就回家去。进门之前先进院子,院子里有树,树上拴着不太长膘的猪。或者没有树,那猪就在猪圈里,猪圈在你睡觉的地方的旁边。院子里有等待转动的石磨,有牲口槽,有兔子笼,还有草垛。跟一些活动在院子里的鸡呀羊呀的小型动物打过招呼之后你就可以进门了,跨过门槛绕过门口灶旁的媳妇或者老妈,看了一眼灶口边上烤着的馒头或者红薯,你把锄头、犁头或者草耙靠墙放下免得砸破了屋里的水缸。吃晚饭了。你吃完了晚饭,开始劈柴、铡草,把小鸡小羊赶到他们睡觉的地方。屋里有人纺线,有人织布,有人看电视有人打牌,还有你的孩子在追跑打闹。你朝地上唾了一口唾沫,然后又幸福地叹了一口气。因为你知道炕已经热了,而炕上还有更加火热的生活。
在很南的南方,你不烧炕,你家里有一个火塘。火塘上面有一个支架,支架下挂着一口锅,锅里是水或者食物。火塘旁边是用来涂抹食物的佐料,有油,但是很少炒菜。家里虽然是暗的,可火塘边上的妻子和家人脸上映着暗红色的火光。
这就是你的家了。你知道离家不远的地方是你的田,你明天还要去的地方。不过,不用着急,你用不着手表,因为你不用和别人协调你的时间。你的生活就只是你自己的,在你的家里和你的田里,事情都是一样的:你不是在劳动,不过是在照顾你自己。

80年代钢琴在农家中(安哥 摄/Fotoe)
二 四合院
四合院属于传统民居的一种。也就是说现在比较少见。按照传统,这是给一个家族准备的封闭空间。每一个四合院上空,都有属于这家庭的独立的一方天,里面住的是数量恰当、相互之间有辈分关系的多个家庭。
在四合院里,长辈和晚辈既住在一起又不住在一起。所以既有请安的必要,又有请安的可能。每天早上,晚辈要到长辈屋里报到,晚上回家,则要进行晚点名。考虑到较老的人通常都会较早睡觉然后较早起床,所以这实际上给双方都造成了不便。一方面,长辈每天早上都要在迫不得已的沉默中(因为大家都还没醒)等待晚辈的出现;而另一方面,长辈每天的就寝时间等于是通过道德压力而为晚辈设立了某种门限:9点以后回家的都算夜不归宿。当然不排除一大早长辈就开始踢腿吊嗓子的情况,但那通常都会造成某种家庭不和。而这显然一点也不符合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四合院由于人口数量适当,所以通常房子中央都会有一个空场,更大的,有好几进的那种四合院甚至有多个空场。北京人利用这些空间的方式主要是种树、养鱼、搭凉棚避暑。据说当时衡量小康之家的标准并非是美元而是“天棚、鱼缸、石榴树”。空场的另外一个功能是充当剧场之用。在其中既可以进行以娱乐为目的的演出,比如堂会;也可以进行关于家族或者家庭内部事务的演讲和尖叫。后者通常以女性演员为多(这说明女性在家族/家庭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不过,对四合院,我最羡慕的是他们吃饭的情形。因为既可以一起吃,也可以“回屋吃”。这种统一基础上的分裂非常符合我们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

大大的“拆”字被涂在许多北京四合院的墙上,蔡元培故居在多方努力下被保存(曾力 摄)
三 杂院
传统没落之后就变成后现代了。而四合院没落之后,则变成了杂院。这里面住的是数量过多、相互之间又没有辈分关系的多个家庭。一早一晚的请安虽然没有了,但频繁的问好却必不可少。“大妈,我回来了”,“二叔,您吃了吗?”“阿姨早”,“小张,今儿怎么这么早就下班啦?”“哦,我请了病假想把家里那床腿修一修”。由于没有血缘关系托底,日常事务变成了感情的载体,而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谁家里的事情都是大家的事情,至少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和四合院不同,杂院里的当然状态就是各回各的屋里吃饭。但是,有时候谁家做了好吃的(比如饺子),也会给处得好的各家送去一碗,然后到了饭后每个碗送回来的时候,里面都会有各家当天的食物。这就是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同之处:劳动人民的每一点幸福都是靠自己的行动挣来的。这些行动就包括讲文明,懂礼貌,以及没有性别歧视地团结身边的人民群众。
有时候,邻里之间的亲密关系甚至会达到一种令人感动的地步。这不仅仅是指一家有难、八家支援的极端情况。而是说,一家的孩子也是全院甚至整个胡同的孩子。换句话说,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权力关系越出了家庭的界线:“去,给大哥买包烟去,找回来的钱算你的。”所以,大杂院里长大的孩子会有一种先天的帮会倾向(不一定有暴力成分),因为大杂院本身就像是一个没有酋长(但是有长老)也不流动的部落。
和四合院比起来,杂院的居民当然不可能请得起堂会。但是似乎每个胡同里都至少有一个会拉胡琴的,七八个能唱戏的,三四十个真正会下象棋的人,甚至还会有一两个会讲故事的叔叔爷爷。再加上笼鸟和猫,杂院仍然是住户主要的娱乐所在地。杂院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是自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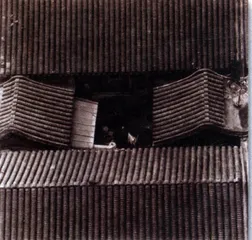
杂院改变了四合院原来的居住者和居住方式
四 单位筒子楼
如果按照建设资金的来源和厕所来划分建筑物的类型,那么筒子楼应该和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学校里面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一起归入公共设施。因为他们都是使用公共资金建设的,内含公用厕所的建筑物。
筒子楼里最壮观的事情是大家在一起做饭,所以知道别人都做的是什么饭。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却可能是厕所的共产主义化。事实上,由于筒子楼是建国后才有的新生事物,所以在很多情况下,筒子楼都是单位建房。它和食堂、澡堂一样,是单位福利的一部分。所以,住户们也大都会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而这些住户并不会因为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就变得更亲密一点,情况恐怕完全相反。因为单位上的那点龌龊全带回到了家里。这样一来,既然大家都要上厕所,而且往往是在同一时间上厕所,那么大家就很可能把对长工资、评职称、分房子、出国考察甚至找对象这样一些稀缺资源的争夺投射到对厕所这一同样稀缺的资源的争夺上。从而使得厕所成为肢体暴力和语言暴力的发生场所。他们打架,还骂人。
厕所还往往因为另一个原因而引发争执。由于筒子楼的下水管道的质量往往不是那么好,再加上年久失修,所以经常会发生堵塞和漫溢的情况。谁来修?房管所的那些人是指望不上的。只能靠住户们自己。而这时,就会发生大型的推诿和争执。
当然,生活不仅仅是上厕所。生活还包括串门和聊天。但是,和杂院里面的居民不同,由于筒子楼的住户之间有上下级关系,或者更加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串门”的含义和院子里的住户有明显的不同。这里,有时候感情成了事务的载体。
在筒子楼里,生活只不过是工作的延续。因为,让你休息就是要你走更长远的路。

60年代建造的大楼(曾力 摄)
五 单元房
与筒子楼、杂院比起来,单元房的最大特点并非厕所的私有化,而是他人生活的不可见性。因为每一个单元都高度自足。
没有了公共的做饭过道和方便厕所,大家进了自己家的门之后就不用再出来了。而按照居民委员会的防火要求,楼道里面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所以,你也无从通过每家门口或者过道的废旧物品来判断他的健康状况、生活水平、饮食结构或者有无不良嗜好。
同样,防盗门的主要功能也许并非防贼,而是防止家庭内部矛盾的扩散。有人试过,从里面把防盗门锁上之后,就算是趴在门上也听不到里面的动静。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隔绝了小道消息的传播。
事实上,单元房居民的惟一的公共活动,就是他们不定期地要被一个叫做楼委会的半官方组织叫去开会。内容通常是布置春季、秋季和冬季的防火任务,“五·一”、国庆、春节的防火任务,以及其他时候的防火任务。有时候,隔壁楼发生了盗窃事件,楼委会也会组织户主们学习一下,主要是传达最新动向,并告诫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过,楼委会也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由于单元房也往往是某一单位自己盖的房子,所以,有时候捐款资助困难同事的活动,会集中在楼委会那里进行就是把钱交到楼委会。
所以,单元房里的人际关系可能是这样的:户主们都相互认识,由于工作和开会的原因。而每家的其他成员,则可能都不认识。而且,实际上只有电梯工才知道每个人的事情。
单元房也是一种不断进步的住宅类型。这主要体现在它的治安方面。现在,有的楼会用一些铁栅栏把自己围住,然后留一个门走人和车。而这个门晚上通常是会锁住的。所以回家太晚就必须要翻门而过。体重或者柔韧性不符合要求的人,就只能要么乖乖早回家,要么另做打算。从这里我们也能看见“身体”正在取代“道德”成为所有与可能性有关的事情的关键概念。

塔楼里的单元房改变了人们的习惯(本刊资料)
六 公寓
单元房继续进化,就变成了一些别的东西。在“花园”和“广场”这两个名字中,前者听起来更适合于人类居住。当然,“家园”更好。“公寓”则是这样的:小区要有大块的绿地,要有停车场或者车位,要有单独的健身中心和娱乐中心,而且房间里要有多于一个的厕所。我的意思是,有一个厕所必须在卧室的里面。
公寓最吸引的人的地方是,那里没有居委会,也没有楼委会。而物业从道理上说,是为我服务的,所以从道理上说,我可以想开会的时候才去开会。至于人际关系,有家人、同事、哥们儿和各种程度的异性朋友,还怕自己闲着不成? 四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