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127)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清泠 笨笨 窦婉茹 路路)
古典的情怀
文 清泠 漫画◎谢峰
自小起,看到书上那些形容女子春愁闺怨的描写,总是不能明白那些女子的眼泪从何而来。
始终不懂,林黛玉为什么要葬花,为什么对着花哭成那样,“呜咽一声犹未了,落花满地鸟惊飞。”读《西厢》时,一句“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何至于“心痛神痴,眼中落泪”呢?枉自了她“世应稀”的花容月貌,专做这无益的事情,真真的派定了她是下来还泪的了。
也不懂,杜丽娘唱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赏花便赏花了,难得去一次花园,不像春香那样开开心心地玩着,你发什么呆惆什么怅呢?更不懂,冯小青好好儿地生活着,不愁衣不愁食,却因着这个不知所谓的杜丽娘写出了“人间自有痴于我,伤心岂独是小青”的断肠诗句,抑郁而死。

直到20岁以后,无意翻到“葬花”一节,看那黛玉的呜咽之语:“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就像和尚参透忽成正果,我也一下子恍然大悟了!黛玉葬的并不是花,而是在葬着自己的青春;她哭的并不是春逝,而是哭着自己不可预知的那销蚀中的年华!
我虽然害怕光阴蹉跎,年复一年,怕的要死,但毕竟我是不会掉眼泪的,更是不可能去葬花了,也没有多少功夫去“挑灯闲看《牡丹亭》”。那些古典的情怀在心灵的深处,它似乎与现实生活非常远,比我们的青春离得还远。
偷书记忆
文 笨笨
初三时有段时间对中印战争历史有点兴趣,爱去市图书馆翻翻书。图书馆在一条僻静小巷中,极少人光顾。我至今记得一个人逡巡在无数蒙尘的书籍间,东翻西找,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无人知晓的宝库。图书馆开架部分几乎全是国内当代小说,我在那里看了金庸的《连城诀》、《张洁文集》、《陆文夫文集》、《王蒙文集》以及丛维熙、高晓声等等。
正是冬天,我特意穿上一件大号军大衣,大衣里别有乾坤——我挂着一个军用书包。在书架林立的房间里,我拼命将喜欢的不喜欢的书往包里塞……这样干了整整一个寒假。
也就是这时候,我在书架上发现了陈映真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全集》中的一本。是纪德的两篇小说:《伪币制造者》和《窄门》。棕色简装封面其貌不扬,竖排本。吸引我的是里面扉页的作家素描,画的可谓有神。的确是台湾出版社出的。想不到这小图书馆里居然有台湾出版的书!我不假思索,塞进了书包。
然而我地毯式搜索所有的开架书籍,却再没有发现其他获奖作家的文集了。
于是我壮起胆子向织毛衣的那位管理员询问,答案是这套书应该是凭借阅证借阅的,纪德这本估计是因为偶然的原因才出现在开架书里的,而其他的都在那个小窗户里面呢!
怎么办?我一定要把它们拿到手!
于是我花钱办了借阅证,借出了其中的两本——海明威和福克纳(一次只能借两本)。回家翻着这两本书,真不愿意还。可是一想到还有更多的文集等着我,半月之后只好重回图书馆还书,以便借出下两本。管理员在借阅证上盖上还书日期,又在下面一行盖上新的借阅时间。
这时我发现了手续中的一个不小的漏洞,足以让我将这套书完全占为已有。原来借阅证上一行空格可以填写两本书名,而按照图书馆的规定这两本书只要在半个月内还就可以了,并没有规定必须两本一起还。也就是说我还一本书时告诉管理员一声另一本书还再看,下次还就可以了。而他盖章时看上去却是将空格里的两本书注销了!(天!我不知道现在我说清楚了没有。想到那天,我至今激动不已!)
我真如此行事了。我小心翼翼,计算两个管理员轮班时间。如果这一次在其中一个手下借的书,我会还给另一个管理员手上。借两本书,还一本,留下一本。第二次去再借两本,下次仍然还一本。我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干这件事情,既提心吊胆,又激动人心。一直持续到初中毕业,我拿到了图书馆里大半的《诺贝尔文学奖全集》。
如今手里存有的只有纪德和另一个希腊诗人的,其余的不知所终。现在想来也许它们实在应该呆在那个小图书馆里,也许它们的命运会好些。也许我应该是一个图书管理员,也许我的命运会有些不同。
(本栏编辑:苗炜)
告诉他,我烦他
文 窦婉茹 漫画◎谢峰
跟约翰·列侬相比,我更喜欢保罗·麦卡特尼。
我不太喜欢过于激烈的思想和行为,可能是我年纪大了。约翰·列侬和大野洋子那场轰轰烈烈的“bed peace”(床上和平),我一直不认为那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像列侬这种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了都让人极度震惊的人,我通常都是敬而远之,哪怕是对他们遗留下来的精神产品。我喜欢看到人家心平气和,就像保罗·麦卡特尼,不哗众取宠,不声嘶力竭,不动声色地伟大着,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地活着。麦卡特尼对太太Linda一往情深,据说Linda患乳腺癌逝世前,麦卡特尼夜夜守在床边,寸步不离,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患难真情比列侬和大野洋子的几天几夜不下床要深刻伟大得多。说到才华,麦卡特尼写的是全球播放率最高的歌曲,而早在Beatles时期,所有写着“Lennon-McCartney”作曲的作品,有一半是麦卡特尼独自创作的。
这当然不是在贬低约翰·列侬的成就,列侬是一个“英雄”,一个“Legend(传奇)”,不是谁想贬低就贬低得了的。
今年的12月8号是列侬遇难20周年,到处都在播放各种版本的《Imagine》,到处都是有关约翰·列侬生平和音乐的回顾,这种铺天盖地的势头是不多见的。我随便登录一个搜索引擎,打上“John Lennon”的名字,电脑一下子就找到了26.1万个网址!
我一边惊讶,一边忍不住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怀念列侬?20年后的怀念和20年前又有什么不同?
约翰·列侬唱:“你可以说我是个梦想家/但我不是惟一的一个/但愿有一天你能加入我们/世界就能合而为一。”
有一个网页上呼应:“This page is dedicated to John Lennon, a man who taught us to imagine a better world.(献给约翰·列侬,一个教会我们想象更美好世界的人”。)
这大概就是中产阶级的怀念方式,因为一般来说能够用诗一般的语言纪念列侬的人基本上都是吃饱了饭的。我明白了为什么颜峻说,“今天纪念列侬是一种非常雅皮的举动”。
约翰·列侬唱:“人人都在谈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但我们这里想说的只是:给和平一个机会。”
有一个网站欣然会意,将站名取为Give Joke a Chance,给笑话一个机会!里面列举了有关约翰·列侬的笑话,基本上都是黑色幽默。版主怕惹列侬迷不高兴,还特意写上,“如果你受不了就别看”。
有一个比较好玩的笑话是这样——“What did Yoko say when Lennon was shot?”(大野洋子在列侬被杀的时候说了些什么?)——“Ono-Ono-Ono!”(她在说:“噢不-噢不-噢不!”)(注:大野洋子的名字是Yoko Ono)我一边看,一边很投入地笑了。我尊敬列侬,但我实在不觉得怀念一个人就非要一把鼻涕一把泪。幽默是另一种层面,或者也可以说是更高层面的缅怀。
“Give Joke a Chance”,多么轻松自然的怀念方式。我希望以后当我再做某某人纪念版标题的时候,能够不再用“告诉他,我爱他”这种如泣如诉的煽情语气,而是奋笔疾书“告诉他,我烦他”。再苦大仇深,都要给笑话一个机会。

新词语
文 路路 漫画 谢峰
名主有花
出自亦舒小说,不用解释其含义。
王老七或七歌:
钻石王老王是大家熟悉的短语,李泽楷就是标准的钻石王老五,比他差一点的未婚男人比如张朝阳就可以说是“王老六”,有点钱又不打算结婚的大龄男青被叫为“七哥”。
不沾膜
不是什么塑料薄膜之类,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指不和模特儿打交道。
私字一闪念,黄金滚滚来
一句俗话,不用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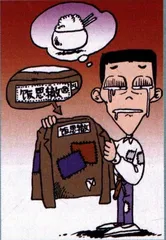
饭思辙
不是名牌“范思哲”,是想“饭撤”,去哪里吃饭
18般兵刃,你专门练“贱”
周星驰有台词说“犯贱犯贱犯贱”,可人人免不了“犯贱”,所以你18般兵刃专门犯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