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爆炸”压力下的基层法院:东莞试点
作者:王鸿谅(文 / 王鸿谅)
( 东莞中院副院长陈葵 )
从立案开始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徐哲看起来比实际年纪成熟稳重得多,他是湖南人,今年27岁,在法院系统已经从业7年。2003年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之后南下考公务员,在广州面试却因为不懂粤语受挫,赶着东莞法院系统公务员招考的最后一天报了名,2003年9月开始,就成了东莞市法院立案庭的一员。徐哲记得:“那时候东莞法院跟东莞中院还在一栋楼里,立案庭在地下B层,5个立案窗口,4个民事和1个知识产权,没有叫号机,也没有人做诉讼引导,封闭式的玻璃,一个对话的小窗口,当事人总担心法官听不清楚,要凑着窗口大声说话,说着说着,就低着头很别扭地从窗口伸进来了。”
立案庭在法院的传统构架中属于审判辅助部门,因为这里的工作就是收案、排期和一些统计工作。徐哲负责民三庭的立案受理,就是交通肇事,“能看到许多伤残的人,激动起来他们会把假肢取下来给人看,许多人真的很可怜”。这个立案窗口,教会了徐哲观察和倾听,“绝大多数都是外来农民工,文化不高,很多事情也说不明白,2003年的时候,请律师的人还不多,很多人不懂怎么填写表格,就会有自称律师的人来揽业务,填一份表800元,我跟同事们很看不下去,就整理了一个表格出来”。他自己做了小纸条,给当事人排号,让他们不用一直站着排队;他还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用书面的方式,写下需要补充的材料和要点,让他们不用跑冤枉路。他一直记得一个黑龙江伤者的家属,“来来回回跑了好多次了,每次我都会仔细跟他说清楚,他都说好,可下次来材料还是都不齐,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就找了张纸给他详细写清楚还需要哪些材料。那是我第一次用书面方式来给当事人做提醒”。
“法院里也有很多人觉得立案庭的工作很轻松,就是坐在那里决定材料收还是不收。”徐哲笑,“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常开玩笑说,我们就像医院里坐堂问诊的大夫,要给人把脉的,要做出判断和分析,还得给别人解释清楚,坐到立案窗口,你才能清楚地看到,来打官司的都是什么人,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徐哲在立案窗口一直工作了5年,后3年都在石龙镇。2005年,专门受理交通肇事的民三庭搬到了石龙镇上,分管民三庭的新领导,是东莞中院的副院长陈葵。去了之后,徐哲才知道,民三庭的移址办公,正是东莞法院系统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尝试——交通肇事的保险和解。东莞的交通肇事案有三个特点,现任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院长陈葵说:“70%到90%的受害者是外地人,70%到90%的肇事车是外地车,70%到90%的肇事车司机也是外地人。”这就导致,假如交通肇事真的进入诉讼程序,肇事者因为种种原因早就跑了,案子就算判了,受害者也拿不到赔偿,社会效果很差。2005年的时候,整个东莞两级法院系统也只有1万多件案子,而交通肇事1年就有4700多件。“所有的车都买了交强险,都涉及保险赔付,为什么不能让保险诉前介入呢?”陈葵说,“涉及保险赔付的部分,法官开庭主要就是审查票据,然后算出最终的赔偿数字,保险公司反而什么都不用做了。”
 (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立案大厅 )
(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立案大厅 )
徐哲记得:“搬到石龙镇之后,民三庭的新立案窗口就变成开放式的了,保险公司的和解员到场,从立案环节就介入,如果双方能够达成调解,法院就不收诉讼费。”陈葵解释说:“我们那时候就考虑,用减免费用的方法,来鼓励当事人尝试诉讼之外的纠纷解决方法。”实践证明,“本地保险公司的案件有60%都能调解”。
隐藏的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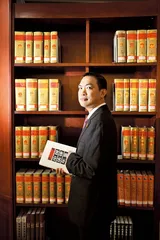 ( 立案庭主管庭长陈志良 )
( 立案庭主管庭长陈志良 )
当陈葵开始尝试交通肇事案的保险调解的时候,整个东莞两级法院的案件数量,已经从2001年的2万多件,到了2006年的4.7万多件,但整个法院系统的编制,并没有相应的扩充。这些案件,绝大多数都在基层一审法院,也就是东莞法院,其中民事案件占到九成。刑事和民事案件的比重,倒是没有太大的地域差异,在全国范围都类似。
案件的膨胀在2009年到达一个顶峰,突破了12万件。酝酿已久的东莞法院拆分也在终于在2009年1月1日成为现实。原有的东莞法院一分为三,分别是第一、第二和第三人民法院,将东莞的32个镇重新划定辖区。其中,东莞第二人民法院的辖区有6个,分别是长安、虎门、沙田、厚街、大朗、大岭山6个镇,每个镇都有相应的支柱产业,经济活跃,决定法院归属地的时候,综合各方因素,虎门和长安是最后的选择,长安镇政府主动拨出了一块地,盖起了法院大楼,把法院留在了长安镇。陈葵也从东莞中院副院长调任东莞第二人民法院院长。
 ( 6月4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右)参观上海世博会英国馆 )
( 6月4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右)参观上海世博会英国馆 )
2009年新挂牌的东莞第二人民法院,一开始就遇上了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全部编制68个法官,1年接的案子是3.1万件,比2001年东莞两级法院的案件综合还要多。身为院长的陈葵当然最直接地感受到了这种压力。“我自己办案最多的一年,大概办了100多件案子,已经觉得非常累了。而2009年,东莞二院的数据是,一线法官人均结案492件,就算把不在审判岗位的法官也算上,人均结案数摊下来,还有400多。”她回忆说,“那时候,真是马上找人都来不及,这些案子里,系列案只有几千件,绝大多数都是个案。怎么办,只能想办法来改变,所谓能动司法,我们刚开始,真是被动的能动。”
法治建设的快速推进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举措之一就是大力快速地发展法院,整个90年代,司法机关始终在以极大热情迅速向基层渗透,甚至出现过“乡乡建法庭”的口号和高潮,可是,在这个进程里,国家对于司法的实际投入资源非常有限,很大程度上依赖法院扩大案源(增加收案数量,尤其是标的额大的经济案件)和收取诉讼费实现原始积累。随着司法权力和管辖范围的扩大,原有的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出现萎缩,甚至遭到压制,而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纷纷退出原有管辖领域,任何纠纷中想获取求助的当事人都被推到了法院。
最明显的例子,1990年4月19日司法部发布《民间纠纷处理办法》,对基层人民政府的民间纠纷处理做出了具体规定,试图创立一种调节+裁决的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但是199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如何处理经乡(镇)人民政府调处的民间纠纷的通知》,提出“民间纠纷未经乡(镇)人民政府调处的,当事人如直接向法院起诉,不得拒绝受理;民间纠纷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又反悔的,当事人如向法院起诉,法院应受理;法院所做的裁判或裁定内容不涉及原调处意见的维持、变更和撤销,但可以纠正原处理;乡(镇)政府所做的调处决定,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不予执行”。根据这个司法解释,乡镇人民政府调处与其他行政机关的民事调解及人民调解,不产生阻却法院主管的效力,对当事人也没有任何约束力。
司法在基层的急速推进,最初正是以否定或取代人民调解以及基层政府的纠纷解决的姿态出现的。人们在法治的浪潮中却很少看到或承认其另一面:过多的诉讼会加剧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和紧张,增加经济生活和市场运行的成本,贬损自治协商、道德诚信、传统习惯等一系列重要的价值和社会规范,使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衰退。结果,在以法律的名义迅速破坏原有的社会规范和秩序的同时,由于国家并不能提供适应民众需求、符合情理的纠纷解决机制,结果却在民众和当事人的自发推动之下,使一种最具传统特色的救济方式——信访得到了畸形发展。
这时候,陈葵在石龙镇上的尝试,就显现出了价值。“前两年的摸索,已经开发出了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纠纷解决的模式,包括基层村委社区、人民调解员、台商协会、报销公司、行业协会等等。”陈葵感叹说,“其实人民调解员制度,本来就是我国基层纠纷解决机制制度设计中的一环,以前也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但随着司法的扩张,慢慢衰落了。我们重新把这条线索建立起来,把人都动员起来,慢慢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丰富的资源,全国的人民调解员有800万,而他们实际调解的案子不到600万,整个东莞有8000名人民调解员,一年调解的案件也只有1.6万件。”现在,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登记在册的人民陪审员有31名、保险公司和解员有34名、司法协理员有133名、人民调解员有1518名。
东莞基层法院的案件中,还有一大类属于劳资纠纷,第二法院民一庭副庭长江和平分析说:“这跟东莞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东莞的产业结构以外向型加工贸易企业为主,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外来人口的和本地户籍人口的比例,完全倒挂,整个东莞本地人口170万,外来人口超过1000万。”劳资纠纷的增长,也是从2004年之后开始,2001年整个东莞两级法院的劳资纠纷还不到1000件,而2009年,这个数字突破了2万。这种变化,跟两种因素有关,江和平分析:“一个是新《劳动法》实施之后,工人自我保护的权利意识的觉醒,一个是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在2009年到达顶峰,今年的情况有所好转。对东莞这个经济中心来说,经济形势差,纠纷才会增加,经济形势好,整体的社会形势也会安稳。”与交通肇事案一样,劳资纠纷也属于可以调解的范畴,徐哲觉得,“最不好调的,还是那些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的”。
调解速裁的实践
新的东莞第二人民法院大楼在长安镇涌头村107国道边,立案大厅一开始就建成了开放式的。徐哲又回了立案庭,还到开放式的立案窗口坐了一个月,然后跟主管庭长陈志良商量,能不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尝试一些调解工作,“就像在石龙镇做的那样”。徐哲笑着说:“以前我觉得,调解就是坐下来讲道理,做思想工作,想怎么做都可以,后来才知道,调解也是一门科学。”
东莞第二法院的全部法官,从2009年开始,都陆续参加了新加坡和香港地区专门机构组织的调解培训。培训是陈葵的主意。2007年,陈葵到香港考察,在香港的小额钱债法庭,观摩到了一次调解。“法官很耐心地算了一笔账,告诉当事双方,如果这个案子不调解,要打官司,时间大概要多久,产生的诉讼费用会是多少,判决结果出来,双方各自负担多少,如果调解,费用又是多少。那是个8000港元的纠纷,如果打官司,诉讼费全部算下来有十几万港元。最后双方选择了调解。”这让陈葵很惊讶:“原来调解还可以这样做。”
陈葵本来想在国内寻找培训机构,结果一无所获,“连本实用的教材都没有”。有的机构可以开课,也无非是找大学里的老师讲一讲,再找老法官讲一讲,没有任何系统。最后还是只能到香港寻找资源,香港调解中心的创办人萧咏仪几乎主动递过了橄榄枝,她从未在内地给法官做过这种培训,这种机会对于她也是一次难得的尝试。2009年初,第一批学员15人在东莞接受了为期5天的培训,紧接着是第二批和第三批,每次30人,课程做了更适用于内地的调整,为期3天。所有法官全部得到了培训。还有8名法官参加了新加坡和汕头大学联合开办的培训班,考下了新加坡的调解员证书。民一庭副庭长江和平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徐哲有同样的感叹:“第一次把调解当做一门科学,事实也证明,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研究规范又实用。”接受了培训的这些法官们,最深刻的观念变革来自香港的理念,“调解是修复关系”。陈葵刚刚到国家法官学院给其他法院的法官们讲了一次课,上课前她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调解的目的是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说,案结事了。”这就是我们的传统观念与科学之间的误区。
有了这样的培训作为背景,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试点单位,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在逐步建立起包括行政调解、人民调解、行业协会调解在内的多元立体的非诉纠纷解决协作机制的时候,为了进一步整合各种资源,实现诉讼与非诉讼的有效衔接,在立案庭附设专门机构——调解速裁中心。这个中心2009年10月正式挂牌。“这就像一个联动平台。”立案庭庭长陈志良说,“使案件繁简分流,提高审判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简单地说,需要求助的当事人从进入立案大厅开始,就有了各种选择的机会,诉讼引导员会解答疑问,并且告知多种选择途径,如果愿意调解,可以去大厅的人民调解员窗口,也可以选择法官调解,还可以立案,选择速裁程序,当这些都无法解决当事人的纠纷,那么,就进入正式的诉讼环节。
调解速裁中心的价值在于,把诉讼这个最后一道防线之前的那些缓冲地带,重新修复起来。陈葵觉得,必须建立起这些分流和缓冲的机制,“如果所有的纠纷全部涌向法院,不管增加多少司法人员,法院始终会不堪重负”。更重要的是,一些民事纠纷,判决未见得是最佳的解决途径。大岭山法庭庭长尹绍彬讲了一个案例:“一个仓库,老板承包给了一个经理,经理找了一个包工头来修理屋顶,包工头又找了一帮小工,结果一个小工出事了,摔了下来,重伤住院,谁来陪?怎么赔?这种案子,如果要打官司,肯定是先治疗再做行情鉴定,就算有了判决,也未见得能够执行,也许还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果是有固定资产的还好,如果没有,连执行都执行不了。可这样当事人就不理解,他还是会来找法院,搞不好,就会变成恶性案件或者群体性事件。”这个案子,最终是调解的,因为那个包工头没有资质,出事之后一度想逃走,被法院找到了。最后和仓库两方老板谈,他们同意出一半费用,前提是包工头也必须赔一半,而对包工头来说,他还是希望继续在东莞谋生的,一半的费用他也能承受。
尹绍彬是1998年来法院的,他说:“那时候,东莞法院里电脑都没几台,判决书要自己手写,写了再改,最后定稿了,再拿给专门的电脑录入人员,听起来很费时间,可那时候还真不觉得的,一个案子,法官可以到基层两三次了解情况。现在办公设备都现代化了,可案子越来越多,能匀给每个案子的时间,反而少了,以前那种办案方式也不可能了。”觉得,真正把纠纷解决的各种机制理顺了,法官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办案了,才能够真正对具体问题的法律理解和适用有更完善的观点,并且体现在判决书上,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法院终究还是法院,当判则判,“当事双方完全没有共同点的,就不适用调解,强行调解,反而会让当事人对法院产生诸多误解”。■ 基层法院司法调解压力法院调解法律东莞爆炸法制试点诉讼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