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谈判在科学的带领下重新起航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袁越)
 ( 12月4日,在坎昆沙滩上,环保主义者上演了一场抗议秀。其中一名示威者扮成北极熊,以唤起人们关注它深受气候变化的危害 )
( 12月4日,在坎昆沙滩上,环保主义者上演了一场抗议秀。其中一名示威者扮成北极熊,以唤起人们关注它深受气候变化的危害 )
冷清的会议中心
从天堂到地狱,只花了一年时间。
去年此时的哥本哈根,天寒地冻,但贝拉会议中心的气氛自始至终火暴异常,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一年后的坎昆,阳光沙滩,但会议中心却冷冷清清,偌大的代表注册大厅里见不到几个人,预计参会人数只有去年的1/3,记者更是少得可怜。
为了保证会议顺利进行,墨西哥政府在各主要路段都设立了兵营,公路两边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士兵。大会第一天因为有墨西哥总统出席,会场外甚至停着一辆装甲车,车顶架着机关枪,冷冰冰的枪口正对着排队进场的代表们。可当代表们进入会场后,迎接他们的却是一支墨西哥民间小乐队(Mariachi Band),乐手们穿着夸张的礼服,每人头上戴着一顶墨西哥大毡帽。留着一撇小胡子的歌手在吉他、手风琴和小号的伴奏下唱起了民歌,嗓音嘹亮,极具穿透力,屡次让隔壁会议室里的主讲人摇头叹气,自嘲地说自己无论如何也竞争不过音乐的力量。
这还不算最糟糕的。坎昆大会的主办方把主会场和边会场分别安排在两个地方,之间相隔8公里。而主会场也被分成三个部分,代表们必须走出空调房间,穿过一片阳光地带才能到达另一个会场,或者媒体中心。主办方解释说,穿梭于两个会场之间的大巴车烧的都是生物柴油,总算让代表们不再抱怨了。
 ( 2009年7月,格陵兰岛西海岸融化的冰川 )
( 2009年7月,格陵兰岛西海岸融化的冰川 )
不过,这样的安排正好让大家体会一下气候谈判大会的庞大规模。谈判会议的数量如此之多,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回顾一下这些会议的由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气候谈判的本质。
坎昆究竟在开哪些会?
 ( 为配合气候变化会议召开,坎昆在酒店区附近兴建了“气候变化村”宣传环保理念 )
( 为配合气候变化会议召开,坎昆在酒店区附近兴建了“气候变化村”宣传环保理念 )
大家都喜欢把今年的坎昆气候谈判大会叫做COP16,其实在坎昆同时在开6个大会,以及无数小会和边会,复杂无比。第一个会就是COP,全称叫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国大会。这个公约1992年开始谈,1994年正式生效。该公约并没有列出任何具体的减排指标,而只是规定了气候谈判的总目标(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一定水平,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以及根本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两条是所有气候谈判的基础。目前该公约一共有194个缔约国(地区),大家每年年底凑在一起开一次大会,今年是第16次,因此叫做COP16。
1997年的COP3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最终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的第一承诺期内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消减5.2%(以1990年为基准),其中各个国家的减排承诺并不一样,欧盟为8%,日本为6%,美国为7%。此后,又经过了8年艰苦的讨价还价和复杂的细节修订,以及艰难的授权过程,《京都议定书》终于在2005年2月正式生效。目前《京都议定书》一共有192个签字国(地区),是气候领域目前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减排文献。《京都议定书》缔约方每年底凑在一起开一次大会,简称MOP。今年是第6次,因此叫做MOP6,这是坎昆召开的第二个会。
 ( 12月6日,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议程过半 )
( 12月6日,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议程过半 )
如果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当做宪法,那么《京都议定书》可以被看做是一部法规。COP和MOP大会的参加国几乎重叠,讨论的议题有些类似,因此经常混在一起开。大部分国家都是用一套人马对付两个会议,只有美国例外。美国是《京都议定书》谈判的发起国之一,当年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为《京都议定书》的达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由于美国国会的反对,美国最终没能加入《京都议定书》,被排除在了MOP会议之外。
COP和MOP大会每年都会讨论30个左右的议题,它们被分成了政策和科技两大部分,分别由“执行附属机构”(SBI)和“科技咨询附属机构”(SBSTA)负责。这两个附属机构相当于“谈判机器”,每年都要开几次会,今年是第33次会议,这也是坎昆召开的第三、四个会。事实上,这两个会才是坎昆的主角,代表们的唇枪舌剑大都发生在SBI和SBSTA会议中。
 ( 12月1日,在坎昆街头游行的墨西哥农民。12月4日,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在坎昆宣布启动2800万美元的适应资金,为穷国农民设置“气候危险保险”,帮助他们保护庄稼、维系生计
)
( 12月1日,在坎昆街头游行的墨西哥农民。12月4日,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在坎昆宣布启动2800万美元的适应资金,为穷国农民设置“气候危险保险”,帮助他们保护庄稼、维系生计
)
《京都议定书》第3.9条规定,必须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前7年开始谈判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指标,于是在2003年举行的蒙特利尔COP11/MOP1大会上设立了“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AWG-KP),专门负责这项谈判。谈判进行了3年,终于在2007年底召开的巴厘岛COP13/MOP3大会上通过了《巴厘路线图》。这份曾经让环保人士激动不已的文件并不是谈判的最终结果,而只是为下一步谈判制定了一份详细的计划而已!其结果就是又增加了一个“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AWG-LCA),目的在于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到全球减排大军中来。从此,气候谈判又多了两个会。今年的坎昆会议是AWG-KP的第15次会议,以及AWG-LCA的第13次会议。
AWG-LCA和AWG-KP代表了气候谈判的两条不同的轨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双轨制”。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是双轨制的坚定支持者,他们认为这体现了《公约》制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但一部分发达国家,以及那些对气候灾难格外敏感的小国(尤其是小岛国)则试图推翻双轨制,把大家拉到一条船上来,为发展中国家也套上减排的紧箍咒。这就是坎昆谈判的两个焦点问题之一。
 ( 11月5日,飓风“托马斯”肆虐海地沿海地区,带来倾盆大雨,引发洪灾和泥石流 )
( 11月5日,飓风“托马斯”肆虐海地沿海地区,带来倾盆大雨,引发洪灾和泥石流 )
除了上述这6个大会之外,坎昆每天还要召开各种各样的接触小组会议,以及各个利益集团的秘密会议。再加上数量庞大的各类边会,使得每年的气候大会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山会海。坎昆本来只是一个度假胜地,没有足够多的会场,主办方只好把会议分散在多家旅馆,让那些需要同时关心这些会议的非政府组织成员和记者们叫苦不迭,纷纷抱怨时间不够用,腿脚吃不消。正式谈判代表们也多次公开表示要求提高谈判效率,减少工作量,否则又会出现哥本哈根大会的情况,大家不得不面对一份又一份“秘密文件”,根本没时间仔细琢磨。
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规定,这轮“后京都”谈判应该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完成,但由于各国立场分歧太大,导致哥本哈根会议差点一无所获。虽然最后草草通过了一份《哥本哈根协议》,但部分国家的代表抱怨会议程序混乱,过程不透明,拒绝接受这份协议。最后COP大会只好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在正式文件中没有认可这份协议,而只是表示“注意”(Take Note)到了这份文件,并责成代表们回国后再考虑是否在协议上签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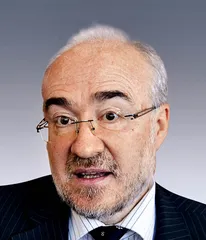 (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
米歇尔·贾拉德 )
(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
米歇尔·贾拉德 )
从内容来看,《哥本哈根协议》和《京都议定书》有着根本不同,它没有对排放指标做出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而只是要求各国分别提出各自的减排承诺就可以了。唯一的硬性要求就是升温幅度不超过2℃,但却没有给出达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碳排放量上限,于是这个目标形同虚设,没人当真。
截止到坎昆会议开幕前为止,已经有140个国家在《哥本哈根协议》上签了字,并有超过80个国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减排承诺。但是这样的自主承诺是否足够了呢?我们是否还需要一个新的《京都议定书》呢?这就是这次坎昆大会的另一个焦点问题。从第一周的谈判结果来看,这两个焦点问题都远未得到解决。
为什么气候谈判会这么难?有一种意见认为,所有关于环保的谈判注定都很艰难,因为保护环境肯定需要某些利益集团做出牺牲,没人愿意这么做。这个说法并不正确,《蒙特利尔议定书》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这份议定书的目的在于消减含氯氟烃等工业气体的生产,保护臭氧层。含氯氟烃是重要的化工材料,在电子光学清洗剂、冷气机、发泡剂、喷雾剂和灭火器中均有应用,所涉及的利益集团相当多。但联合国于1985年设立专门机构讨论此事,只花了两年就通过了《蒙特利尔议定书》。此后又经过多次修改,逐步加强管制,每次改进都进行得相当顺利,其谈判过程甚至可以用“乏善可陈”这4个字来描述,完全没有《京都议定书》这般吸引公众眼球。最新的观测显示,南极上空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蒙特利尔议定书》已经见效。
《蒙特利尔议定书》和《京都议定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除了两者的难易程度相差很大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人类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不足。含氯氟烃对臭氧层的破坏作用证据确凿,臭氧层对地球生命的保护作用也广为人知,因此来自民间的呼声很高,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政治家们也必须想办法克服。气候变化就不同了,至今还有相当一部分民众没有从心底里相信人类活动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因,其结果就是气候变化变成了一个典型的自上而下推行的环保运动,来自基层的动力不足。
“欧洲为什么一直在气候变化领域表现得相当激进?就是因为欧洲的科普做得好,民众普遍相信科学,相信气候变化的危害。而民众一旦态度强硬,就会逼着政治家向前走。”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博士对本刊记者说,“反观美国,科普工作一直做得不好,民间的怀疑论者很多,导致美国的政治家也不那么热衷于此事,他们要考虑选票的!”
看来,在气候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还是要回到根本,回到科学上来。
气候变化研究的新进展
“2010年几乎肯定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的前三名。”世界气象组织(WMO)秘书长米歇尔·贾拉德(Michel Jarraud)在大会第二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1~10月的陆地+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比1961~1990的平均值高0.55℃±0.11℃,1998年同期数据为+0.53℃,2005年同期数据为0.52℃,后两年已经被证明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两年。”
据贾拉德介绍,WMO多年来一直采用来自英国气象局(Met Office)、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数字,今年又引入了欧洲气象中心的数字,结果同样证明2010年的前10个月是有史以来最热的10个月。要想知道2010年是否会成为年度总冠军,则要等到明年2月份才能见分晓。
“很多人对此有疑问,他们说今年初不是很冷吗?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判断某个年份的平均温度是高是低,必须从地球的整体来看。”贾拉德补充道,“比如今年初欧洲和美国确实很冷,但降温幅度并不大,还比不上1996年那次严冬。与此同时,今年北极地区、加拿大大部,以及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大部都偏暖,所以总体来看2010年是很热的一年。还有一个反例:2003年夏天欧洲虽然经历了酷暑,但从整体来看,2003年反而是地球相对较冷的一年。”
来自WMO的数据显示,不管今年的最后两个月如何变化,2000~2010这10年肯定将成为有记录以来地球最热的10年。除了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外,地球上所有地方的这10年平均温度都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除此之外,北极冰盖在今年9月19日融化季结束前的总面积为有记录以来第三低,仅次于2007和2009年。平均海平面也达到新高,而且上升速度加快。1993~2008的平均海平面上升速度达到了3.4毫米/年,这个速度是20世纪平均速度的两倍。
与此同时,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持续上升。据联合国“全球碳计划”(Global Carbon Project)项目主任理查德·豪顿(Richard Houghton)博士介绍,今年9月份的大气二氧化碳含量达到了389.2ppm,是自人类诞生以来的最高值。因为金融危机的缘故,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2009年下降了1.3%,但2010年强势反弹,预计增长率将超过3%,这使得2000~2010年这10年的碳排放平均年增长率仍然维持在2.5%左右。相比之下,1990~1999年的碳排放年增长率只有1%。
换句话说,虽然气候变化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关注的焦点,但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在逐年增加,而且增长速度也越来越快,其增长曲线位于IPCC的各种气候模型的顶端,就是说比绝大部分专家事先估算的速度都要快。
这就很自然地引出一个问题:《哥本哈根协议》中80多个国家提出的自主减排承诺是否足以将升温幅度控制在2℃以下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欧盟委托一个研究小组进行了一年的研究,研究小组成员在这次坎昆大会上汇报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结果显示,即使按照最好的情景来计算,也不大可能完成2℃的任务,两者相差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下同)。如果按照更可能的情景来推算,两者之间的差别更是扩大到了惊人的100亿吨!
这个结果完全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做出的。根据豪顿的介绍,目前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有47%留在了大气中,而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占到全部温室气体总效应的64%。也就是说,温室效应有很强的累积性,如果现在不立即减排,指望将来技术发展了再减,就来不及了。按照这个思路,科学家们计算出到2020年时全球总的碳排放必须控制在440亿吨以下,并在2020年后以每年3%的速度递减,才有超过2/3的可能性将升温幅度控制在2℃以下。目前的温室气体年排放量为480亿吨,已经超出了40亿吨,这就意味着碳排放量必须在2015年达到峰值,然后迅速下降才行。如果坎昆会议没有新进展,大家完全依照《哥本哈根协议》来行事,那么2020年最有可能的碳排放量将为540亿~550亿吨,2℃的目标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时间不等人。欧盟的研究小组在坎昆报告说,目前北极冰盖和格陵兰冰川的融化,以及亚马孙热带雨林的生态系统都已接近临界点,一旦超过临界点,崩溃将无法制止,后果不堪设想。可问题在于,冰川、冰盖和亚马孙热带雨林对于一般人而言都太过遥远,引不起大家的兴趣。但是,今年的极端天气现象频发,生命和财产损失严重,研究表明这和全球变暖有着密切的关系。
“今年出现了很多戏剧性天气事件,比如俄罗斯的高温和巴基斯坦的洪水,还有亚马孙流域和中国西南地区的干旱,以及中国舟曲和非洲国家贝宁的暴雨,这都是非常罕见的。”WMO旗下的“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项目主管格萨姆·阿什拉(Ghassam Asrar)博士在坎昆的一次边会上发言指出:“莫斯科今年7月份的最高温度达到了惊人的38.2℃,7月平均气温比正常值高出7.6℃,比在此之前的最高纪录高出了2℃多!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一现象与全球气候变化有直接的关系,但平均温度如此大幅度提升肯定与气候变化有关,这在100年前是根本不会发生的。”
气候研究的另一个重点领域就是飓风。WMO报告称,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飓风的发生频率也许会下降,但高强度飓风的发生频率肯定会增加。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飓风研究专家廖淦标教授在坎昆大会上报告说,根据他的研究,中北美洲历史上只有中世纪暖期(900~1100年)的飓风强度和目前一样达到过一个小高峰,这说明大气温度很可能与飓风强度密切相关。
事实上,墨西哥就是超强飓风的受害者。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有4个强度为4级以上(最高5级)的飓风光临过这个国家,这种情况在20世纪最后的30年里总共只发生过4次。2005年那次4级飓风威尔玛(Wilma)把坎昆海滩上的沙子尽数卷走,墨西哥政府不得不花费7000万美元从加勒比海底挖出沙子来填补空缺。
“虽然目前还无法证明某个具体的极端气象事件‘源于’气候变化,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气候变化将改变极端气象事件的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阿什拉博士总结道。
问题在于,老百姓对这种概念性的描述不感兴趣,他们需要的是实际的帮助。就拿飓风来说,廖淦标教授在讲座中提到,2003年登陆北美西海岸的一次飓风的路径直到登陆24小时之前都没有被预测准确,结果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一次成功的极端气象事件中期预报比任何漂亮的言辞都能打动民众的心,可惜的是,几周至几个月范围内的中期天气预报一直是世界性难题,在这方面气象学家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就是提高气象观测的广度和精度。WMO专门为此开了一个边会,向代表们介绍了气象观测领域所面临的问题。WMO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lobal Climate Observing System,简称GCOS),该项目负责人亚德里安·西蒙斯(Adrian Simmons)博士介绍说,这个系统承担起了对地球大气、陆地和海洋的气候监测工作,来自全世界的气象学家们建立了一个遍布全球的测量网络,对大气温度、风向、风速、大气成分、河流水量、冰川和冻土带的面积和厚度、海洋的温度、酸度和盐度,以及海平面高度等几乎所有与气候有关的数据进行测量,并和所有该领域的专家共享。但是,这个观测网还不够全面,非洲和南美洲的观测点还是非常稀缺,在研究一些影响范围遍布全球的气候现象(比如气溶胶的大范围迁移)时就显得力不从心。
另外,涉及陆地生态系统的测量方法学还有待改进。“全球陆地观测系统”(Global Terrestrial Observing System,简称GTOS)的负责人贝弗丽·劳(Beverly Law)博士介绍说,目前对北方森林面积的估算存在10%~25%的偏差,而热带雨林面积的估算误差甚至高达100%。因此,关于森林对碳排放影响的估算存在25%~100%的偏差,这显然不能满足气候谈判的要求。
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在海洋。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0%,海洋对地球气候的影响大于陆地,但人类对海洋的检测远远落后于陆地。“全球海洋检测系统”(Global Ocean Observing System,简称GOOS)负责人基斯·艾弗森(Keith Alverson)博士在大会上介绍说,规划了很久的“全球海洋检测系统”截止到2010年9月仅仅完成了62%,而且大部分工作完成于金融危机前,2008年之后就基本上停止了,因为来自各国的研究资金没有到位。
另外,海洋检测系统的维护费用很高,这方面的资金缺口同样很大。比如一种用来观测ENSO循环(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海上浮标(Buoy)矩阵虽然已经建成,但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损害却占了浮标总数的23%,这些被损坏的浮标因为缺钱而一直没有修理,这对科学家研究并预测ENSO循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每个国家的代表在大会上都表示海洋观测很重要,但具体到行动上却都不愿出钱。”艾弗森抱怨说,“海洋经济占了全球经济的5%,相当于2.7万亿美元,可目前投入到海洋观测系统中的钱每年仅有10亿美元,我估计这个数字需要加倍才能满足海洋研究的基本需要。全球观测系统可不光是为了研究气候变化,它与老百姓的生计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GOOS的观测结果能够帮助沿海居民更好地预测渔汛,以及预报飓风,意义重大。”
对于沿海居民来说,没有什么比海平面的持续上升更恼人的了。艾弗森指出,海平面的上升并不是均衡的。虽然全球平均海平面持续上升,但最近20年里太平洋东北部的海平面却一直在下降。“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洋流方向和强度不同,以及海水温度的差异所造成的。”艾弗森对本刊记者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更加关注局部地区的气象预测,因为气候变化对每一地区的影响都是不同的,需要区别对待。”
事实上,强调局部研究与服务意识,是WMO近几年的关注重点。气候学家们越来越意识到,气候研究不能总是搞大而全,而是必须想办法为各行各业提供气候咨询,让每一个具体的人从气候研究中受益,只有这样才能让老百姓认识到气候研究的重要性,并逐渐扭转公众的偏见。
这个态度也影响到了“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政策。就在坎昆大会上,IPCC各部门负责人召开了一次大会,向代表们汇报了预计将于2014年推出的第五次气候评估报告的进展情况。第三工作组共同主席拉蒙·皮克斯-马卢加(Dr.Ramon Pichs-Madruga)博士介绍说,IPCC将改进气候模型的研究方式,过去IPCC过分强调理想情景,未来将加强研究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新的气候模型研究将更加务实,其宗旨从“为政治家制定气候政策提出要求”改为“为政治家制定气候政策提供帮助”。
最后,让我们回到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即人类活动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是否真的导致了全球变暖?这个问题虽然在主流科学界已有定论,但民间持怀疑态度的人很多,而这次坎昆大会并没有给出太多值得介绍的新进展。但是,科学家们想到了一个更加直接的理由,那就是海洋酸化。这一现象与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直接相关,可以很容易地进行测量,其危害也可以定量研究,其科学基础远比气候变化清楚。就在这次大会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了一份关于海洋酸化的调查报告,并把这一问题同食品安全联系了起来。
这份报告指出,每年大约有25%的大气二氧化碳被海洋吸收,转化为碳酸,从而改变了海洋的化学结构。自工业革命以来,海洋的pH值降低了30%,这一变化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是自恐龙灭绝(6500万年前)以来最快的。如果人类目前的碳排放速度一直保持到21世纪末期,那时的海洋酸度将再降低0.3个单位,这就相当于将海水的酸度提高150%。受海洋酸化影响最大的是珊瑚和贝壳类海洋生物,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改变将极大地影响到海洋鱼类的生存。
海洋鱼类为30亿人提供了15%的动物蛋白,另有10亿人的主要蛋白质来源就是鱼,海洋酸化具有很大潜力成为气候变化领域的一把利器。
“科学家们,请你们接受挑战,勇敢地站出来澄清事实,这是说服公众的唯一方式!”UNFCCC新任秘书长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女士在UNFCCC组织的一次高级别边会上发言说,“过去几个月一些人对气候科学家的攻击再一次证明了科学的重要性,这件事说明气候科学研究的结论正变得越来越清晰,终于开始触及了一部分人的自身利益,所以他们才会想尽办法攻击科学家,以此来影响气候政策的制定。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政治家从来都是比科学家慢一步的,科学家应该不断地挑战政策,为政治家指引方向。”
菲格雷斯女士是哥斯达黎加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政治家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Jose Figueres Ferrer)的女儿。这位费雷尔依靠军事政变上台,却立即把军队解散,并把权力交给了民选总统。此后他曾经三次当选为哥斯达黎加总统,该国在他的治理下成为中北美洲政治最稳定,民众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菲格雷斯女士一生从政,曾经担任哥斯达黎加气候变化谈判代表,直到她被任命为UNFCCC秘书长为止。“我以前曾经生活在美国,现在终于不再受这份罪了。”菲格雷斯女士笑着说,“我现在生活在德国,我注意到德国的科学教育贯穿于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我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么做的好处。哥斯达黎加也是这样,我国政府不但非常重视环保,而且愿意采用科学的方式保护环境。事实上,在我就任UNFCCC秘书长之后,我欣喜地发现很多国家在本国采取的政策要好于他们愿意拿到谈判桌上来的政策,我觉得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背后有科学家在撑腰,科学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相信保护气候对他们有好处。”
但愿菲格雷斯女士的观察是正确的。■ 碳排放科学京都议定书带领谈判起航坎昆全球气候变化气候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