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未来的人 ——专访《连线》创始人凯文·凯利
作者:陈赛(文 / 陈赛 石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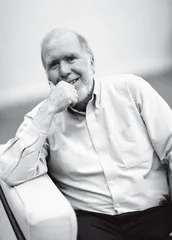 ( 凯文·凯利 )
( 凯文·凯利 )
27岁那年,凯文·凯利在以色列游历,那时他还是一个到处流浪的自由摄影师。在前往耶路撒冷空墓的途中,他经历了一次近乎神启的体验。他以为自己只剩下6个月,于是结束旅行,回到旧金山老家。
最后3个月里,他独自一人骑自行车自西向东穿越美国,共计8000多公里。一路上,他丢弃了所有东西,最后到达时,除了自行车外一无所有。旅途中,没有未来的痛苦折磨着他,“未来是生而为人的根本之一。没有未来,你就被剥夺了部分的人性”。
与上帝约定的那天早晨醒来,他重获生命,也重获未来。在一个叫《美国人生》的广播节目中叙述这段经历时,他的声音中有对生命和未来的无限珍惜和狂喜。从此之后,他是一个活在未来的人。他参与创办了一本关于未来的杂志《连线》,写了一本叫《失控:机器、社会与经济的新生物学》的书。沃卓斯基兄弟在拍摄《黑客帝国》时,要求所有的演员必须阅读3本书,其中就包括《失控》。这本书中,他从多个学科最前沿出发,通过大量生动的实例揭示和阐述复杂系统的一般原理,并预言了互联网、集体智慧、虚拟现实、云计算、物联网以及人工生命等的出现。
20年后,这本书被一群中国的业余爱好者翻译成中文,并得以正式出版,成了对他书中所提出的“蜂群思维”、“集体智慧”的最佳实践。最近,凯文·凯利为这本书的宣传来到北京,所到之处,受到中国“极客”圈的热烈追捧,喧嚣浮华之中,只有这位老“极客”一如既往的朴素淡定,没有半点架子。
当他告诉我们,最欣赏的作家是梭罗时,我才惊觉他甚至在外貌上都与梭罗很像:结实的体格,敏锐的蓝眼睛,庄重的态度,还有那一把大胡子。在创办《连线》之前,他与梭罗一样,住在树林里,自己挖井,用大树和石头造房子,过着简单的生活。
 ( 《连线》杂志办公室 )
( 《连线》杂志办公室 )
30年来,他用梭罗观察自然的眼睛观察技术,把技术作为一种生命体来研究。他的科技视野中总是带着温暖的宗教关怀。在他的新书《技术想要什么》中,他说,技术是生命的延伸,为生命提供了选择、机会和可能性,通过技术的视角,我能看清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黑莓中可以看到上帝。
梭罗有一句名言,旅行是一种视角,而不是地点。这位19世纪的旅行爱好者一生大部分的旅行都在自己的家乡。凯利也是一个旅行者,他一生走遍了世界的许多角落。他告诉我们:“我安排自己的一生最大化的学习,而旅行是学习最好的方式。每一个新地方都能教给你新的东西。”
年轻的时候,同龄人都在上大学,他却离开大学去亚洲游历。上世纪70年代初期,亚洲的旅行非常便宜,一年才2000美元。他脚踏廉价的运动鞋,身穿破旧的牛仔裤在亚洲的偏远地区游荡,一晃就是8年。间或回到美国挣些钱,然后再去往遥远的东方。亚洲给了他新的视角,让他了解到世界不同的运转方式,他懂得了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要事先计划好,大型任务可以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并借助最少的规则来完成。
当我们问他,现在作为技术先知的生活与当年在亚洲漫游的生活有何相通之处时,他说,他把互联网视为一个“外国”,就像一个新的亚洲。它向你开放,你能看到许多新事物,刚出现的传统。
三联生活周刊:集体也许能翻译《失控》,但他们能写《失控》吗?
凯文·凯利:恐怕不能。自下而上的力量很强大,但我并不认为集体智慧能做一切事情。我一直相信自上而下的,编辑的价值。很多艺术和创造,都需要自上而下的全局视角和个体智慧。旅游指南,或者烹饪书,可以有很多人一起来写。信息类的书,比如维基百科也可以。小说也有人尝试过。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失控》中两个主角,天才和群氓。在网络时代,群氓固然可以有伟大的建树,那么一个天才的角色应该是什么样的?
凯文·凯利:天才可以决定一个发明或者创意的具体细节,比如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决定了今天电灯的形态和电网的结构。
但是,回顾发明的历史,你会发现,一个天才独自发明一种东西的情况是很罕见的。大部分时候,是几个人同时有了同样的想法或发明,比如一共有23个人发明了电灯,这些发明者之间毫无交集。电话、电池、蒸汽机、无线电,无不如此,就像这些“东西”到了一定阶段想要被人发明出来一样。
有人专门研究过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发明家,发现他们都是“高度联网”的人,他们的社交面极广,研究和发明涉及多种领域。这就像买彩票一样,彩票有很多运气的成分在里面,但你必须买了彩票,才能参与到这场游戏里。这些发明家之所以赢,不是因为他们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网络。他们买了更多的彩票,所以比别人更幸运。
所以,从某种角度而言,创意本身不是自足的,它们必须彼此依存和交互,有自己的议程,是一个生态系统。就像你口袋里的iPhone,它需要成千上万的“中介技术”才能发明出来,并维持运转。英国发明家查里斯·巴比吉从1830年设计“分析引擎”,具有现代计算机的一切雏形,CPU内存等等,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发明不可能实现,只能到100年之后才能重新发现。
三联生活周刊:你写《失控》距离今天已经有20年了,它真的没有过时吗?
凯文·凯利:如果是物理学,20年前的书必然过时了,因为物理学在不断发现新的东西。但在复杂适应系统领域——生态环境、生物机体、经济、社会组织、计算机网络都是复杂系统,并没有新的科学发现,所以这本书里基本的论据仍然是有效的。如果今天我重写这本书,还是这么写,只是会有更新的例子,更多的证据。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是非常惊人吗?
凯文·凯利:互联网是发展了,但对互联网作为一种系统运作的理解却少有进展。无论在人工生命还是机器人技术,抑或是生态学或仿真学领域,并没有出现新的重大思想。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
凯文·凯利:我不知道。也许我们在等待一些数学上的重大突破。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一切系统的运作都以信息为基础,但我们不知道“信息”是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不知道“信息”是什么?
凯文·凯利:对,信息是什么?它如何自我组织?如何在系统内部增强秩序?如果你从系统的角度看世间万物,则万物都是系统在处理信息,比如向日葵,它的生长和进化就是一个信息处理的过程。企业的运转也一样,金钱是一种信息。
苹果和橘子,哪个有更多的能量,哪个有更多的物质?更多的电?这些都可以测量。但如果你问,一个西瓜和一架喷气式飞机,哪个东西更复杂,包含更多的信息?答案是我们不知道。
科学家研究过信息的物理构成,但我们仍然没有好的定义。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从一个比较日常的定义来说呢?按照你的理论,我们应该让信息失控吗?
凯文·凯利:那些自以为能控制信息的人,要么是不诚实,要么是与世界脱节。这个世界如此多的信息,你怎么可能控制?你也许能选择,但你选择的一切东西都是不确定的。所以,正确的态度是接受事实——你不可能看到所有东西,你会对绝大部分东西无知,退一步,从那种纠结的感觉中释放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你一方面拥抱技术,另一方面又与技术保持距离?
凯文·凯利:是的。信息的爆炸是无限的,但我个人是有限的存在。无限对世界是好的,因为它为每个人创造机会、选择和可能性,让他们找到自己才华的表达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无限对个人是坏事,它会耗尽你。在世界的无限和个人的有限之间,你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我的态度是,支持外部世界的无限化,但自己选择一种有限的生活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失控的边界在哪里?维基解密是你所说的失控吗?
凯文·凯利:维基解密很了不起,它给黑暗之处投入光线。秘密就像癌症。一个任何靠秘密运转的组织,他们以为自己需要秘密,其实是在内部啃食自己。CIA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秘密,到后来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这种秘密的机制没有设置任何反作用力。新闻媒体是一种反作用力,但不够强大,因为它们在国家法律的界限之内。维基解密是处在国家之外的媒体,所以强大。我相信法律,也赞同规则。但法律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市场也一样。
“失控”一定会有界限,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它在哪里,只能不停地往前探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能做到维基百科、维基解密,我们本来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可能的,但以后我们会找到更多可以做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是单一的系统呢?你怎么判断一个系统是失控了,还是控制过度了呢?
凯文·凯利:没有中心,没有老板,就说明是去中心化的。在一个企业里,如果老板或者CEO抱怨他们不知道底下人都在做些什么,在我看来这是好事。如果老板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那就糟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才说,技术为每个人提供了表达自我和实现自我的机会。是什么技术让你找到了自我,以及表达自我的方式呢?
凯文·凯利:我大学只读了一年就辍学了,没怎么学过写东西。我是通过写电子邮件和聊天室的帖子学会写作的。那时候还没有Web,我们通过一个邮件列表互相写邮件,在邮件里谈论媒体的未来、安全和隐私问题等等,有点像今天的微博。后来有人看到我的邮件,给了我一份编辑的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有什么作家或者书对你影响特别深刻吗?
凯文·凯利:有两个作家我很崇拜,一个是亨利·梭罗,他也是一个崇尚自然,又热爱科学的人。我没有练就他那种写作风格,但我学习了他的写作视角。他的视角是深刻而广泛的。
还有一位女作家,她叫安妮·狄勒德(《溪畔天问》),她在26岁时得了肺炎,痊愈后想更深地体验生命,于是花了一年时间住在顶客溪写作,她专门写自然界中小东西的哲学意义。她的文章激发了我写作的欲望,但我无法与她相比。
对我的写作影响最大的是斯图尔特·布兰德,当年我的老板,《地球概览》的创始人,也是一个老“极客”。他的文章属于电报体,信息密集而主题宏大。我也一样,我喜欢写大而深刻的东西,像启示录。
三联生活周刊:我理解你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但你说“在黑莓中看到上帝”是什么意思?
凯文·凯利:当我们进入自然,比如一片雨林,看到红木、鸟、灌木丛,会有一种和谐的感觉。自然中有智慧和庄严,让你感觉到那种比我们更大更复杂更久远的存在。那种智慧已经存在了数十亿年——进化是一种学习,也许无意识,但植物、动物的进化是持续40亿年的学习。
我想我们的技术也开始了这种学习的进程。随着技术越来越复杂,它会获得生物式的学习能力,甚至我们的学习能力。在未来,当我们注视自己发明的这些技术时,会有类似于注视自然的感觉,你会觉得它的存在有更大的意义,它反映了宇宙,反映了数十亿年的学习,深刻而优美。
三联生活周刊:你好像不愿意谈论技术的负面影响?
凯文·凯利:每一种技术都会制造它的问题。某种技术越强大,它被滥用的后果就更严重。比如互联网很强大,但互联网一旦被滥用,它的反作用会很可怕,我认为我们还没有见识到互联网最可怕的副作用。但我一向认为,我们利用技术创造,比利用技术去破坏,哪怕只要多出1%,日积月累,就是进步。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将来我们能发明出比人类更聪明的机器吗?
凯文·凯利:是的,但我想我们应该发明与人类思考方式不一样的智慧。发明与人类一样的智慧没有意义,你可以用10个月制造出来(十月怀胎)。世界上并非只有一种智慧,智慧有上百种不同的维度,你的计算机在某个维度上就比你聪明。
三联生活周刊:你能谈谈《连线》吗?
凯文·凯利:《连线》一直有很强的个性。伟大的杂志通常都有独特的个性,比如《纽约客》、《名利场》、《滚石》。在《连线》工作的人,其实都没有这样的个性,但他们组合起来,就呈现出那样一种个性——热情、乐观,政治上右倾,亲市场,但社会态度上又偏左,主张共享、开放、透明,有点共产主义。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的《连线》与你当年做主编时的《连线》有什么不同吗?
凯文·凯利:会有微小的差异。我是来自上世纪60年代的嬉皮,主张没有秘密,透明共享,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连线》现任主编)会偏右一点,他更看重市场和竞争。但伟大的杂志能被不同的编辑来解释而仍然保持核心的个性。《连线》仍然是《连线》。■ 活在连线创始人未来专访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