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只知当时 无论后来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方向明)
 (
方向明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日子:
1994~2002 )
(
方向明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日子:
1994~2002 )
事件一:史玉柱的巨人集团倒塌
在1997年,当巨人集团资金链已断,讨债者盈门之际,我与皮昊是第一个也是唯一走近史玉柱的记者。我们在空荡荡的珠海巨人集团总部,与史玉柱谈了3天。在3天中,我们在其总部也只见到3个人:史玉柱、程晨(史的助理)、陈国(财务总监)。因为已无他人可见了。
在中国媒体中第一个独家报道了巨人集团兴衰史的真正来历。也许败局已定,无回天之力了,史玉柱当时出人意料地沉静,清晰地梳理了巨人集团从创业开始的全部心路和心迹。由此,我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题为《巨人狂写兴衰史》。后来,这篇报道被中国传媒界誉为中国民营企业的第一部兴衰史。
巨人集团的衰亡,也曾被评价为中国民营企业成败的第一个缩影。但我当时预感到它不会仅仅是一个缩影,而将构成一个现象。因为,中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风起云涌已10年,也到了一个坎儿。果然,在1997年的那个时点上,中国民营企业接二连三地出现失败的案例,如三株、红高粱、沈阳飞龙、太阳神等等,也就构成了我的《研究失败》系列。由于当时真实记录了一批民营企业失败的全过程,这些史料后来被人多次抄袭,甚至被某人合集而名噪一时,真是可笑至极。
记得当时不少人曾经鼓动我起诉那位抄袭者。我当时对他们说,研究失败应该告一段落,应该转向研究成功。因为中国民营企业一定会从失败中爬起来,走向更大的成功。
 ( 李孟苏
1997年6月进入三联,是最早的一批文化记者。早年的栏目是“人物”,因其在英国生活背景,常年写关于英国文化的“话题”栏目,后来又做过家居、时尚。参与的封面故事有《2006年最佳产品与设计——“乐活”与创造》、《中国消费者改写奢侈品消费规则——穿普拉达的人民》等。 )
( 李孟苏
1997年6月进入三联,是最早的一批文化记者。早年的栏目是“人物”,因其在英国生活背景,常年写关于英国文化的“话题”栏目,后来又做过家居、时尚。参与的封面故事有《2006年最佳产品与设计——“乐活”与创造》、《中国消费者改写奢侈品消费规则——穿普拉达的人民》等。 )
在“研究失败”的过程中,我一直是百感交集。这些民营企业家都曾经有过非凡的创业经历,但终究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双重局限,而由盛及衰。尤其是他们在经历了极为惨痛的挫败时,他们面对我真实且真诚地袒露心灵煎熬时,我时不时也会有一种揪心之痛。在此后的很多年中,我一直试图以舆论的力量帮助他们东山再起。但可惜的是,东山再起且重振雄风的只有一人,这就是史玉柱。在2000年我策划“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时,我力荐史玉柱为首届年度人物,也在当年我策划CCTV“对话”栏目时,我用两期长达100分钟的节目让史玉柱重新浮出海面,并续写了其东山再起的传奇经历。
我觉得我欠他们的,因为他们以自身的惨痛让我们《三联生活周刊》成就了影响力。我至今不能忘怀,那些因失败而沉默的企业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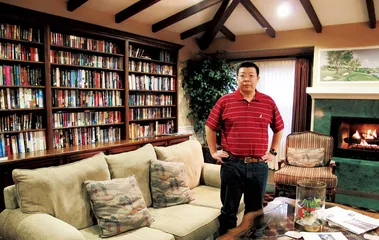 ( 皮昊
1996至1998年在《三联生活周刊》担任记者,其间撰写封面文章和经济专题。十几年过去了依旧对周刊净土胡同时期记忆犹新,参与《中国股市跨年度风云》、《巨人集团兴衰史真正奥秘》《“阎王”传奇——“渤海二号”幸存者17年后吐露真情》等封面故事的报道。 )
( 皮昊
1996至1998年在《三联生活周刊》担任记者,其间撰写封面文章和经济专题。十几年过去了依旧对周刊净土胡同时期记忆犹新,参与《中国股市跨年度风云》、《巨人集团兴衰史真正奥秘》《“阎王”传奇——“渤海二号”幸存者17年后吐露真情》等封面故事的报道。 )
还有一件不能忘记的小事,采访史玉柱时,只能给我报销单程机票。因为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经济相当拮据,这绝不是靠钱堆起来的媒体,而是靠梦想和精神撑下来的媒体。
事件二:希望集团裂变阵痛
 ( 王星
1997年入职至今,2001至2007年任驻法记者,负责有关法国社会、文化各领域的报道。回京后开设了玩意、鸡毛蒜皮、博物等栏目,其中“博物”旨在探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以图说的形式详细讲解各博物馆的馆藏精品乃至“镇馆之宝”。参与过封面故事《等待罗大佑》、《开战星球》等的采写。 )
( 王星
1997年入职至今,2001至2007年任驻法记者,负责有关法国社会、文化各领域的报道。回京后开设了玩意、鸡毛蒜皮、博物等栏目,其中“博物”旨在探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以图说的形式详细讲解各博物馆的馆藏精品乃至“镇馆之宝”。参与过封面故事《等待罗大佑》、《开战星球》等的采写。 )
在中国,最著名的家族企业莫过于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氏四兄弟。即使在今天,如果将刘氏四兄弟的资产全部加起来,依然堪称中国最富有的家族。
就在1997年,刘氏家族四兄弟发生了“从传统奔向现代”的一场阵痛,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分家。此举堪称中国家族企业的一个里程碑事件,而《三联生活周刊》成为这一事件的见证人和记录者,不仅全程报道了这一事件,而且深刻地剖析了其分家的时代根源,真实反映了这一中国最大家族企业的产权演变轨迹。
事件缘起于1997年11月4日的一则企业小公告。刊登在《经济日报》和《中国证券报》上,公告不足300字,但立刻引起我高度关注,因为此前我研究过这个家族企业。当时传媒界并未普遍关注到,这一则小公告所透露出的中国最大家族企业的惊天秘密。
小公告称:“根据希望集团董事会的决议,希望集团下面只设大陆、东方、华西、南方四个二级实业公司,分别由刘永言、刘永行、陈育新、刘永好负责。并同时决定,自1997年6月3日起,由刘永行董事长出任集团的法人代表,代表希望集团对内对外活动;由陈育新总经理主持集团的日常工作;刘永好不再担任集团的法人代表。”
再普通不过,一则企业法人变更的寻常公告。但其不寻常之处,是因为希望集团当时是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并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连续3年列入世界500巨富排行榜中。这则公告明面上只显露出,中国最富有的刘氏兄弟的关系微妙变化,但经过采访方知,此公告折射出一个拥有几十亿资产家族的深层内幕。
早在一年多前,社会上层就传闻刘氏兄弟正在“分家”,但刘氏家族对此秘而不宣,不对外界做任何具体解释,使内幕变成一道铁幕。刘氏兄弟讳莫如深,只有《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真实揭示了这个神秘家族究竟发生了什么。这篇报道后来被商学院评价为“对中国家族企业的第一次深入解读,前所未有”,并成为经典案例。
事件三:中国VCD“大国不是强国”
在1997年,中国产业界最大的响动是中国VCD行业的“第一次联盟”。自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产业发展史上堪称“颠覆性创新”的只有两个行业,一个是VCD,另一个是小灵通。我至今仍将VCD称为“行业”,而非“产业”。
之所以称这两个行业为“颠覆性创新”,是因为按照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发展趋势,本不应该出现这两个行业,但中国人自己生生造出了两个新玩意儿,一个叫VCD机,一个叫小灵通电话,改变了全球产业的技术发展节奏。
VCD机是中国人真正的原创,当年安徽万燕把今天看来非常普通的数字解压缩技术,装进一个铁盒子里,就成了VCD机,刚上市时售价竟达5000元/台。于是,中国蓬勃兴起了一个年产上千万台且产值达几百亿元的新兴行业,它的出现不仅搞垮了总理亲抓、十几个省集资兴建的亚洲最大的录像机生产基地——大连华录,而且逼得索尼、三星等国际产业巨头也不得不跟在中国人后头生产VCD机。
正是因为中国VCD是一群“野小子”,因此在江湖上彼此杀得血雨腥风,拼得你死我活,几近自生自灭。在行业发展的生死关键点上,这一新兴行业的领头“狼”们,秘密地坐下来召开了一次VCD圆桌会议,此会的目的是要结成中国VCD联盟,形成群狼。
《三联生活周刊》又一次独家披露了此次圆桌会议的全部内容。更可称道的是,在这篇独家报道里后来形成了传媒界的两个流行语,一个是“大国不是强国”,另一个是“先驱成为先烈”。后来媒体频频借用为中国是“是彩电大国而不是彩电强国”,“是汽车大国而不是汽车强国”,“是手机大国而不是手机强国”……
“先驱成为先烈”的第一个经典案例就是VCD的发明者安徽万燕。后来中国媒体通用此语比喻过早夭亡的开拓者。
时至今日,这两个颠覆性的创新行业都已昙花一现。但是在13年以前这次圆桌会议上,这些领头“狼”们的预见至今仍令中国产业颇为玩味与深思。在开创者“万燕”成为先烈以后,后起之老大“爱多”也继之成为先烈,继而第三度的老大“新科”如今也不见踪影。
在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当年那些凶猛非常的雄狼身影吗?万利达?金正?新科?四通?小霸王?新天利?厦华?我还记得,当时爱多的总经理胡志标说:“民族品牌要争取到绝对的市场份额必须以低廉的价格取胜,这是唯一生路。”也是唯一死路。
这场会议所形成的联合宣言最后成了一纸空文,所以中国VCD堪称“倒在血泊之中”。
出人意料的是,当时我在《三联生活周刊》的这篇报道发表后,立刻被“中央最高决策参考”刊登,并被国务院领导者批示,也在多次高层会议上反复引用这篇报道的观点。当今中国产业研究第一权威路风教授称这篇报道为“中国第一产业报道”。他就是看了这篇报道,将VCD行业作为其研究中国产业的“初始之作”的,其报告中的资料均源于此,以及后来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刊登的《VCD死亡档案》。
今天,在中国家庭还摆着VCD或DVD,而世界上早以电脑替代其功能了。因为技术的趋势原本就不应生出这个玩意儿,但中国人造了它,《三联生活周刊》全程实录了这一令世界瞠目的“颠覆性创新”。
事件四:公费生走进历史
1997年,最大的“民生事件”是公费生全部改为自费生。国家教委宣布高校招生改革并轨,公费生走进历史,从此中国迈进“自费自立上大学”时代。
在当年出现了一个年度关键词——贫困生。《三联生活周刊》率先撕开了60万大学“贫困生”的相对贫困状态,更揭示了他们“物质贫困与精神压抑的双重窘迫”。时至今日,13年过去,这一弱势群体仍然是社会话题,一个绵延10年以上的话题。
当一个时代结束之际,我们有必要还原一下原貌:当时,中国有1050所高校,在校生约300万人。据国家教委统计,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约占15%~20%;而全国学联调查,“贫困生”高达30%,至于“特困生”约占5%。
这是相对当年社会经济状况而言的,即使一个中等收入的工薪家庭,供养一个大学生一年约1万元,也是一个不轻松的负担。因为当年北京市职工的平均月收入尚不足1000元。
这篇报道绝不仅仅是率先揭示了一个社会问题,而且它在当时最凸显了《三联生活周刊》的办刊理念——“一本杂志和它所倡导的生活。”我依稀记得,当时主编朱伟力主做此篇报道,但“贫困生”们却因心灵阴影而不愿接受采访,使报道很难进行下去,朱伟则站在杂志社四面透着寒风的办公区,脸红脖子粗地大声嚷嚷非做不可,也就在这位“偏执狂”的强迫下,逼出了这篇反响极大的报道,并且在其“高压”下生成了此报道立意“自费敦促自立”。
当我今天面对已到而立之年的“80后”,他们当年正好赶上这一拨儿,《三联生活周刊》对他们反复强调“成人意识”,而与他们交谈后又不禁慨叹“想自强难自立”。
“当自强难自立”是《三联生活周刊》当年告诉社会的一个真实判断,也是一个前瞻性预见。10余年过去,来自各种机构的调查都在验证当初的预见:今天的大学生“自主意识”与日俱增,“自立能力”每况愈下,“自食其力”的状况越来越不乐观。
当时我觉得真是高明,认为大学生自费上大学可以敦促大学生自立,但是当时非常强烈地意识到大学生当自强难自立。
事件五:两大刁民撞在一起
中国消费者的“刁民意识”始于王海,而重于何山。1997年,中国第一次大肆讨论“王海与何山现象”。王海这个人的名字竟成为当时的十大流行词语,以至于在一些大型商场竟然贴出了“防火防盗防王海”的条幅。更引起争议的是,王海凭借打假竟然成为百万富翁,但他仍不知足,嚣张地高喊“打假应成千万富翁”。而且,王海之举的道德伦理之基更让很多人难以接受:“以打假暴力,反造假暴力。”
我们当时预见到“王海现象”将导致千万个“王海”在成长。但是就在社会舆论普遍认为王海是个绿林好汉时,法律专家何山这位《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起草人之一却走上了以身“试”法的道路,以买假而打假。因为王海别出心裁的打假不仅使他名声大噪,而且使他获利颇丰。有人捐给他10万元办公司,王海的公司在1997年初成立。
而在此时,法律专家何山以身试法,按照王海打假索赔的做法,“买假打假”进行了一次司法实践,这位《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起草人之一,亲自买假货,亲自索赔,亲自诉讼,终于使王海之举得到司法肯定。
《三联生活周刊》费尽周折弄到了王海的“打假日记”,又跟踪了“何山打假”的行踪。
让偷偷摸摸做贼般的“打假”彻底阳光化。
事件六:点子大王何阳成为通缉犯
在1997年,这一事件成为中国咨询业“聪明反误聪明事”的第一案。何阳事件引起刚刚呱呱坠地的中国咨询业的第一次信誉危机,也引起了中国咨询业的第一轮自嘲式的悲叹:拍脑袋的感觉与抖机灵的点子,几近于诈骗。
的确,中国咨询业的起步阶段是从一个歧途走向另一个歧途:点子公司变异为咨询公司,咨询公司又变异为管理公司。
写完这篇报道5年后,也就是2002年,当我兼任《麦肯锡高层管理论丛》的执行主编时,我更深刻地感觉到咨询业是一门科学,必须要靠数据库和案例库形成理性判断,并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形成智慧。
事隔17年后,在创意滥觞于中国的今天,又冒出来一批创意大师、策划大师,大肆风行。可惜的是,本土的咨询业并未真正成长起来,国际咨询公司的咨询仍居主导。只要人们还迷信点子和灵感,中国的咨询业就不可能真正成长起来。
事件七:“阎王”传奇
在中国传媒界有一座里程碑,这就是“渤二事件”。在20世纪80年代初,渤海二号海洋石油钻井平台翻沉,死亡72人,由于媒体的大胆报道而酿成一场政治风暴:海洋石油勘探局4位领导因渎职罪被判刑,石油部长宋振明被解职,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受到记大过处分。
但是事情的真相并非如当时所报道。事隔17年,我撞见了在这个曾经震惊中国的历史事件中的两个默默无闻的生还者。他们整整被冷藏了17年。报道此事,当时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好在副总编辑潘振平和主编朱伟都不是怕事之人,此报道一出立刻酿成了一个传播事件,竟被300多家平面媒体转载,而在1997年的时点,中国是没有互联网的。
后来,我碰见当年报道“渤二事件”的记者,她因此报道成为80年代中国最著名的女记者。她对我说:“你给‘渤二事件’翻案了。”此话让我感到脸红,其实写此报道,我并无翻案之心,也无正名之意,我只想为那72名死难的灵魂洗白一下。因此我对那位大姐只说了四个字:“只是还原。”
事件八:嘉化改制
1987年我曾写过一篇《株化改制》的报道。事隔10年,1997年我又在《三联生活周刊》写了一篇《嘉化改制》。“株化改制”讲的是企业如何转变市场机制,而“嘉化改制”则讲的是产权改造。
在这10年间,中国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有过两起著名的事件。一个是关广梅现象,另一个是山东的“陈卖光”。那么“嘉化改制”在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进程中究竟有何意义?这是一个千余人的中型国企的厂长,以450万元买下了1.5亿元的国有资产。这场改制被工人称为一次“流血的改革”。
1987年6月18日,对于重庆嘉陵化工厂1206名职工来说,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命运抉择。他们从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从干活挣钱的“企业主人”,变成能够主宰企业的大大小小的股东。当自己的命运完全执掌于自己手中时,他们非但没有感到喜悦,相反,他们却感到了一种失落,忧心忡忡。
中型国有企业彻底卖给职工,嘉化首开中国先例。因此,它必然成为中国企业产权改革的一块活化石。
后来,在我的策划下,中央电视台一套对“嘉化改制”做了一个长达45分钟的调查性专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同年,TCL的产权制度改制也悄然启动。我没敢写,怕给他们惹麻烦。
嘉化改制是一场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TCL改制也是一场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前者是一夜之间,而后者则用了长达3年,而几乎同时起步的联想、方正的产权改革则用了长达10年才到位。嘉化改制不算是中国公有制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里程碑,但却堪称一个经典的缩影。
在《三联生活周刊》这篇报道的结尾,我引用了嘉化改制设计者之一当时给我讲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一个国有企业的职工患上重病,因他享受公费医疗而不怕花钱,但必须到指定医院就诊,这家医院按固有的常规疗法,让他吃了1000多元的药也不见好。后来,这位职工打听到民间一个中医,手中有一偏方专治此病,只需花100元,他多次询问单位领导可否报销,领导回答需要研究,结果病情延误,这位职工去世。死后,单位念其贡献,又买了个1000元的骨灰盒,厚葬。
也就在这一年,联想的总裁柳传志对我讲了他那句著名的话:“我决不做改革的牺牲品。”也是在那一年,四通总裁段永基也对我讲了一句著名的话:“革命的首要问题是产权。”
事件九:《三联生活周刊》的1997岁月
在1997年,作为《三联生活周刊》的一员,我给杂志写了12个封面故事,这个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因为《三联生活周刊》成熟了,不会再将杂志的品质与命运系于几人之手。
然而,我很怀念那段拼死拼活的日子。《三联生活周刊》的总编辑董秀玉、副总编辑潘振平、主编朱伟,以及我,都是一样的苦力般的“传媒民工”。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与朱伟合作的景象,他总是一副“包工头”的嘴脸,吆三喝四,训东骂西,然后撅着屁股拿周刊当“自留地”一样耕耘,脸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掉地摔八瓣儿。朱伟是一个“种杂志”的好把式,他年长我10余岁,还与我一样勤奋。
当我翻开《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那些发黄的报道时,毫无“无冕之王”的感觉。但那些铅字却深深刻着中国历史的划痕。在今天看来,1997年《三联生活周刊》的若干报道已成里程碑的事件,但我觉得其主要魅力还是历史事件本身。我及我的同伴们,只是发现者,只是记录者,而不是创造者。看着这些报道,猛然想起我们当年的一个共同梦想:“倡导者!”
在我人到中年之际,我更怀念的不是这些报道,而是当年那些一起苦中作乐的同伴们:皮昊、邢海洋、武汉、张晓莉、王秀全、李建泉、王荣环……他们是当年与我在记录历史的人,今天也都成了“人物”,只是都还健在,均未成为“历史人物”。
1997年,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个转折点。一本杂志开始步入正轨,开始有了影响力,也奠定了它的历史方位。■ 1997只知史玉柱无论打假当时后来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