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旅程
作者:王恺(文 / 王恺)
 ( 王恺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日子:
2005~至今 )
( 王恺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日子:
2005~至今 )
李大人
每天上三联书店那个灰暗的类似夹层的办公室的时候,都会在楼下那家著名的陕西面馆买个肉夹馍,热气腾腾的贫民食品,惶恐而饥饿地吞咽进去,典型的以食物缓解焦虑。那是2005年春节后几天,刚到三联,就像黑户,就愿意自己被人看不见,能够躲藏在角落里偷偷待着。另一方面,又有点虚荣,有点浑不吝,急于能做点什么,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办公室狭窄而昏沉,如果不开灯,白天也那么无精打采。一格格的小隔断如身份界定,新来者坐在边缘地带,和李鸿谷领导下的金童玉女们距离别提多远了,当然是心理距离。终日听他们在那边隔断里欢声笑语,越发产生融入集体之心,可就是融不进去。年纪大了,做不出拿个笔记本在朱文轶同学身边做虚心求教的样子——他是那时候的三联金童,随口一说什么都能成金。一有什么难题,新人就围拢,小朱老师一边谦虚着,一边讲解着。
没想到后来和他那么熟悉。2008年,我们在小岗村采访的时候,住在农民严鸿昌家,几人睡在类似大通铺的农民家二楼,因为不知道要写什么,每天晚上和李鸿谷在那里装腔作势地讨论,此时间,小朱同学往往像当年崇拜他的我们一样,掏出小本来记录。包括后来下农田,他也不忘记在拖拉机头掏出小本,密密麻麻写字,随时随地记录,他的掏小本形象深入我心,成为日后笑闹的永恒动因。
2005年,只能在这边的小隔断里苦挨了下去,其实和幼儿园的孩子一样,新同学来了,总是怯生生在集体边上徘徊,渴望被收纳,就这样开始了三联时光。
 ( 程义峰
2004到2006年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偏重社会热点新闻报道。代表作《马加爵的三重世界:一个贫困生的极端生活方式 》、《辽源大火与被它考验的人们》、《警贼同盟与火车站的谋利空间》、《台湾头号悍匪的末路江湖》。现在新华社工作。 )
( 程义峰
2004到2006年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偏重社会热点新闻报道。代表作《马加爵的三重世界:一个贫困生的极端生活方式 》、《辽源大火与被它考验的人们》、《警贼同盟与火车站的谋利空间》、《台湾头号悍匪的末路江湖》。现在新华社工作。 )
隔着5年的时间距离,数不清的乡村和城市的空间距离,我回到那个昏昏的画面里,对躲藏在角落里的自己说,别这么矫情。
“李大人”来布置任务了,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他有这个外号,我恭敬地称之为李老师,然而被他嘲笑不止一次,往往弄得我张口结舌。李大人有上天入海的求真精神,对一切被崇拜者、体制、权威皆予以怀疑,对我们所受的教育包括教育体系尤其怀疑。后来才明白,这种怀疑论,是周刊社会部必不可少的做新闻的基础,如此这般,才能破成见而求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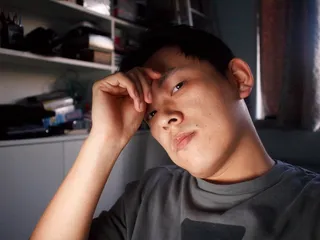 ( 尚进
2002年底入职至今,热衷一切新兴前沿,这些新兴前沿的技术或商业新潮大多以特别报道的栏目在周刊呈现,与此有关的封面故事如《最佳产品与设计》、《名牌时代的时尚逃兵》、《联想全球化的攻守之道——柳传志、杨元庆的形与势》等都有他的参写。 )
( 尚进
2002年底入职至今,热衷一切新兴前沿,这些新兴前沿的技术或商业新潮大多以特别报道的栏目在周刊呈现,与此有关的封面故事如《最佳产品与设计》、《名牌时代的时尚逃兵》、《联想全球化的攻守之道——柳传志、杨元庆的形与势》等都有他的参写。 )
他对我这个没怎么做过新闻的人则予以关心的怀疑,先是对我的基本采访能力予以不信任。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在我来面试的时候,反复问我,比如说,你现在要做一个空难采访,你告诉我,怎么去那个城市?怎么去找你的采访对象?我糊涂中回答,不就是坐飞机先到那个城市吗?然后坐出租车去找采访对象啊。陪在一边面试的李菁和吴琪欲笑不便,欲走不能。
到三联5年了,感谢苍天,基本上没怎么发生过空难。2010年何其不幸,先是4月份的波兰总统坠机,9月又是伊春空难,一年内做了两个空难的采访,我果然兑现了自己进三联的那句傻话,先是坐飞机去那个城市,然后坐出租车去找人——其实又有哪个采访,不是按照这种形式在进行呢?
在荒凉的城市里,在陌生的环境中,我都会短路地想到当年那个面试。
不过当年,只有这种采访能力,他简直不屑于再追问。不知道怎么我糊里糊涂被招了进来。后来对我的怀疑转了方向,是针对我的大学教育的,总是问我,你说哪个历史学家比较好?你们学院派的体系里面,哪本历史著作值得推荐?现在中国最好的历史学家是谁?你写新闻不要写成论文好不好?
可怜我仅仅一个小硕士,哪里就成为学院派的代表了?后来发现这是李大人的思维方式,他见过太多僵硬的学术论文和高校师生,妄想一二三把事情说清楚的学术论文套路,在三联基本没出路,他着力改变的是我僵硬的套路。
“我们能把事情说清楚吗?”在那个小会议室里,李鸿谷像哲学家一样提出了这个命题。讨论的是抗战。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周刊要做若干期,本年度最大专题。身为新人没有任何资格发言的我被叫去参与,原来是李鸿谷想叫我发挥历史系查资料的特长,去看老报纸,从1931到1945年,故纸堆里的细节,也是最真实的细节,从无数碎片的历史中找出真正的抗日战争。
“究竟什么问题才是真实的抗战问题?”李鸿谷由哲学家摇身一变成为历史学家,我本来幻想发挥读了几年二战史的特长,告诉他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新方向指向哪里。可是李姓历史学家哪里关心这些,他告诉我,他对研究成果没兴趣,关心的是,如何能够用我们获取的各种资料——报纸的、学者的、历史传记的——去建立一个新的历史阐述体系。
“能传播的体系。”神奇的小黑板,后人无数传说中的小黑板那时候还在会议室,侃侃而谈的李姓历史学家站在跟前,七画八画之中,一个路线图出现,条条路径,引向了最终的叙述方式,以天为载体,一天中,几点几分发生了什么,此事件参与者是谁,事件背景如何,6天构成一个宏大主题,每期主题被逐渐引带出来。
恍如史景迁来到现场,黄仁宇亲自出马。所有的细节、故事和鲜活的口述,都可以通过“那一天”有了一个好的集合。那一瞬间,我想李大人是很满足的。
现在已经完全没印象这仅仅是我幻想的画面还是真实存在过,李大人的历史学家的姿态倒是一直保留下来,周刊日后多次做历史题材,一次比一次艰难,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李鸿谷自己的不满足,总要突破前面的框架。可是,哪里能找到那么多框架呢?于是,大家不得不每每陪他做沉思状,想着能有什么新的突破。而在李大人百般为难自己的同时,常是主编喝住了他的胡思乱想,在诸多办法中找到了一个最可行最漂亮的办法,陪在一边的我们,在心里就偷着舒了口气。
漫长的抗战
鉴于我第一篇稿件就被主编退回重写的开端,李鸿谷不得不对我展开外松内紧的控制方法,查老报纸、复印老报纸,只是粗活,更重要的活,还是写作和叙述的细活。可是他大概没有想到,粗活和细活,我都不合格。
去国图查老报纸的胶卷,茫然不知道什么是想要的,第一期做1931年的东北抗战,我把《顺天时报》乱翻一遍,上至张作霖家族如何规划沈阳,下至当年的沈阳城的妇女衣着,全部复印回来。李大人恨铁不成钢,因为那些细碎的历史资料里,既没有指向,也没有多少价值,我满足的只是自己不求甚解的好奇心,还振振有辞地告诉他:“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现在人重构历史,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好奇心去重构的。
他倒是也没有痛斥我,只是告诉我,我们之所以翻检老报纸,是希望寻找到多方材料,能够丰满我们以往单薄的历史叙述。他也没有更深地鄙视我,可说句老实话,我哪有资格重构抗战历史。
折腾几回后,貌似找了几条路径:亲历者的采访,旧报纸,社科院历史所书库里的资料集,当事人的回忆录,几方面结合,顿时丰满。我还记得,在写淞沪抗战的时候,那本落满尘土的历史所汇编的抗战资料集给我的满足感,感觉自己回到了战场,俯瞰着悲惨大地。战场的地点,双方的进退路线,看资料,结合战地地图,居然能被自己摸索明白。而另一方面,战火纷飞的上海因为其特殊性,租界里舞厅的舞女在搞跳舞救国,捐款给前线,历史复杂而有趣。
老报纸上的新闻记者写的报道很有画面感,苏州河边住宅十室九空,几只波斯猫被主人抛弃,饿得在垃圾筒里找食,第二天再去看的时候,两只大白猫的尸体躺在地面。“众生自在劫难中。”看到这种句子,才明白,自己以往大学课本上的抗战叙述,是多么的干枯和没有可传播性。
我从没有做历史学者的梦想,不过在那些埋头在资料室的时间里,还是常常产生幻想:硬生生地花时间,在这里埋头做学问,重新写几本历史书也不错呢。
那几只大白猫的画面,常使我想起历史学家吉本写《罗马帝国衰亡史》时的故事。看到罗马的历史废墟上几位修道士的身影,让他产生了冲动,结果花了若干年时间去研究罗马帝国的历史。我没有把自己妄想成吉本的能力,只是,周刊虽然只做了初步的历史重叙工作,但是确实使若干人,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都有重读历史的兴趣。
历史八卦的兴趣也在增加中,这是李菁同学的独门秘技,我是刚刚接触,不过也兴致勃勃。抗战做到了敌后根据地的专题,我去写延安1938年的一天。2005年的延安还是个简朴的城市,大规模的石油开采还是后来的事情,在毛泽东纪念馆唯一的那位教授的家里,我一边吃着他家晾晒在窗台上的大红枣,一面兴致勃勃考证毛泽东和江青刚结婚时住的窑洞的方位。这能解释一个历史问题,为什么1938年9月29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夜晚,毛泽东深夜没有留在延安东郊的桥儿沟会场休息,而是骑着他的四川矮脚马回到了他在杨家岭的住宅,因为那时候他和江青的关系已经得到了组织批准。
一边听他说,一边脑子里想到了毛泽东牵马过河的影子。
李鸿谷对我集中于历史八卦的恶习很不满,教育我八卦是为主题服务的。可是我酷爱着这些,看到当时在延安的苏联记者写的毛泽东一边抓虱子一边和大家开会,我如获至宝;看到《冈村宁次回忆录》里面他关于南京监狱里的秋天如何萧瑟的记录,我也赶紧抄录。我们的抗战史,充满了诸如此类的细节,实在说,有的很别致,有的真是没有必要。
2005年,抗战6期专题做下来,始终按照最初的以“天”为载体的叙述方式,我做完一期才明白,这个“天”,在时间之外,其实有更开阔的空间概念,最内核的,还是《三联生活周刊》坚持的历史观,花了巨大篇幅重新叙述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抗战的历史事实。6期专题卖得非常好,不过,即使做了这6个专题,我还是三联的新记者,并没有完全成长起来。
2005年的日常生活
记忆中的2005的生活只剩下一个主题,就是周刊。那时候,我三天两头往上海跑,这是我曾经生活了多年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三联生活周刊》是一个冉冉上升的传说,我一方面很骄傲,为自己在里面工作;一方面很羞愧,因为我只是周刊的小喽啰。
见到自己的老同事,还有父母亲,只有一个核心主题,就是《三联生活周刊》是什么样的:主编如何要求凶猛,同事如何聪明伶俐,我如何苦苦挣扎,标准的走火入魔。甚至两个同事在外头一碰面也没别的话题,三下五除二就过渡到周刊的八卦,主编的喜怒哀乐成为每次的生动细节。其实这种生活很不正常,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真的就那么糟糕地沉浸其中。
记得过了年在吴哥窟旅游,在LP推荐的一家精美的柬埔寨汤馆邂逅谢衡,两人没怎么惊叹异国重逢的巧合,坐定之后立刻开讲三联诸事,旁边一起旅游的朋友很不屑地说我们,典型的三联附体。
为什么会附体?心理学家肯定能给出准确的解释,对于我自己而言,没什么合理解释,就是魔症,这个魔症从没进三联的时候就开始发作,还记得没来三联的时候,李大人开出了良好的诱惑方剂:你不是喜欢调查中国底层社会吗?来三联后,我们打算派你去县城,一个县城待一个月,让你好好看看真实的中国。李大人的论点是,中国的现实目前是遮蔽的,我们三联的记者,正是要拨开云雾见真相的。这种说法,实在是太有诱惑力啦,对于我这种常年在上海看话剧、泡爵士酒吧的人来说,简直是另一片天空啊。
我不是一个有新闻理想的人,可是,三联能满足我所有要求,新闻的,非新闻的。
事后明白,这种一去县城一个月的好日子完全没有可能实现。毕竟周刊的出版周期控制在那里,而且新闻的要求永远是把悬空的剑——县城倒是常去,可是哪里还是自己游山玩水时到的县城?眼前全是愁云惨雾,像是旧上海歌星吴莺音的歌曲。“莽莽神州,淹没在迷雾中。”全是和采访有关的问题,找不到采访对象怎么办?采访对象拒绝了自己怎么办?现场进不去怎么办?稿件糟糕怎么办?
焦虑综合征自己看不出来,在别人眼前却很分明。在吉林采访化工厂爆炸,找很多年没见的亲戚帮我联系了一个饭局(这是社会部记者的常态,为了稿件,别说多年没见过的亲戚了,就是昔日的仇人,只要知道内情,也恨不能马上化敌为友,只要你能说点东西)。席间倒是什么人都有,政协的,化工厂的医生,吉林市安全生产局的干部,可是大家都有所顾忌,话题转来转去就是不说化工厂爆炸的事情,我怎么提问题众人也不回答。席间政协同志讲了个概念,当地大企业往往比市政府还有势力,对市政府命令带搭不理,我耳朵竖了又竖,又不敢打断他,又巴望着他详尽点,简直恨不能化身孙悟空,钻进他肚子里把话掏出来。
好像我亲戚看见我神情紧张得不对劲了,让这位老同志说详尽点,结果老同志又绕开了,讲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什么市政规划问题。
那晚上受尽折磨,好像是一碗精美的菜肴就在眼前,可是,你就是没办法尝上一口。沮丧着,哀叹着,后来写了个“大企业裹挟的小城市”交差,被慧眼的主编看出来,说是,有概念没细节,采访不深入。
2005年就是一连串的失败采访。在温州采访贪污市长杨秀珠,因为话题敏感,加上并不是当年的新闻,属于老账新翻,所以几乎没有人愿意多说话,我甚至动了上公园去找那些义愤填膺的老头们听街谈巷议的心,可是也告失败。后来还是李菁动了怜悯之心(神奇的李菁,每次在紧要关头都有法宝),拿出了几个电话,让我一一打过去试试。我终于找到了“人大”的一位领导,他也很详尽地讲了杨秀珠的温州故事。
杨秀珠应该是一个传奇,从一个汤圆店的店员起家,到拆迁房子的干将,再到主管房地产的建委领导,最后以副市长终局,大时代给了她无穷的机会,而且她又都抓住了机会,最后事发逃去法国的结局都弥漫着温州特殊的传奇气息。事实上,每个点都有深入进去的可能——如果是现在的我去采访,肯定会很老老实实地一点一滴地追问。
可是那时候我满脑子的概念建构,妄想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好文章,在很多能深入的点上都不知道怎么进去,采访很不详细。面孔又薄,找到了杨秀珠当年汤圆店的同事姓甚名谁,甚至到了温州老城市那家老汤圆店门口,也不敢进去询问,怕别人拒绝,最后还是写故事梗概式地讲了个杨秀珠大事记。糟糕到无以复加。
不过印象中最终还是走进去吃了碗擂沙汤团,南国特产,豆面撒在汤团上,奇香。是的,我就是这样化采访失败为吃的动力的,这也是我在三联怎么东奔西走也没瘦下来的原因。在盐城采访新四军,一位管资料的老先生怎么也不肯给我资料,只把几本没用的普及读物给我,我也是化悲痛为吃,一边吃着盐城特殊的香气迫人的土鸡汤,一边安慰自己,没事,没事,天塌不下来。
在安徽一个小县城采访禽流感,好不容易混进了被封锁的村庄,刚刚和一家养有鸭子的人家聊天几分钟,就被警察从里面拎了出来。我听见他用对讲机汇报,抓到一个自称是记者,但是没有记者证的人,我终于爆炸:谁自称啦?
也许是那种暴发很震慑,刚出了村庄,他就把我赶下警车了。四顾只有土黄色的大地,还有脸红红的、满面酒气却把村庄看守得铁桶似的乡村干部,仰头长叹,吃饭去,只要不吃鸡鸭就行。去了县城,居然还有蟹黄汤包,我紧张地想了想水族和鸭的联系3秒钟,还是沮丧化为的贪吃动力占据了主导。
且吃去。现蒸的汤包,极香,那一趟县城没白去。
现在我已然明白了各种进入现场的方式,哪怕是站在现场外,也能三下五除二搞定看守者,不讲现状也可以,让他讲出现场的昨天,前天,啰唆的、外围的叙述,比起一根筋的叙述,枝叶围绕主干,说不定有更好的空间感。一个成熟的记者,在现场外面能获得的东西,不会比在里面少。
可惜那时候哪里懂,只知道往里面死冲,然后悲壮地被驱逐。不过,确实满足了一个又一个县城漫游的理想,只是这理想和当初的梦想大相径庭,想起了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我的痴人说梦般的县城漫游记,没有写出来的,应该比上了杂志的好看。
2005年是没有摄影记者跟随的年代,一个个的现场,只能自己孤军奋战。三联招收的新记者的第一年,按规律都要经历各种重大新闻考验,矿难、贪污官员、爆炸,我一个没落下,一个没做好,写了些无声无息的稿件,发在后面的版面充页码,最担心的,永远是主编在收到稿件后的眉头紧皱。
那一年我得到过主编的表扬吗?完全没有印象。三联是个奇怪的单位,没有中间过渡的编辑阶层,我们的稿件,包括我这个新记者的稿件,都是直接发给主编,所以永远直接面对最真实的考验。李大人永远只有一句话:我相信主编的判断力。你有百般理由,可是到了最后,主编毙掉的稿件永远是坏稿件。我的座位是背对走廊,主编走过来都看不见,都是他到了身后,把打印出来的稿件往桌子上一甩,瞬间心惊肉跳。
吴琪和王鸿谅,那时候已经是两位游刃有余的记者,虽然我年纪比她们大,可是却不如她们成熟,快乐,更不及她们勇猛。还记得主编一次次从他的小房间出来,走到我的座位前,不满地说,你要向你两个师姐学习。说的就是她们俩。
这两个快乐的女性,一天到晚花枝招展地走进办公室,轻松地搞定一切,也是她们俩,在我彷徨无计,屡次遭受主编毙稿打击的时候安慰我:别放在心上,主编的宠爱和批判都别放在心上。她们像富有智慧的沧桑老年人,告诉我,宠辱不惊,要有你自己的标准,一定要如此,你才能在三联待下来。2005年底,为了她们这句话,我放弃了辞职回上海过小日子的打算,见旧同事,还是滔滔不绝地说着三联故事,强硬支撑,没有想到,一直撑到了现在。■ 漫长旅程三联生活周刊杨秀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