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堡的音乐味道
作者:王星(文 / 王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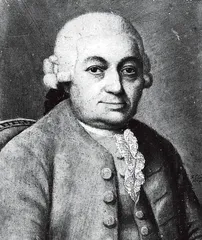
其实,汉堡一直是一个音乐味道很重的城市。除去披头士和音乐剧《猫》之外,在古典音乐史上,这里至少也能以勃拉姆斯和门德尔松的出生地存名,何况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歌剧院。然而,即便对德国人来说,汉堡也是一个太容易被首先联想到贸易与技术的城市。如果说披头士当年的成功展示了这座港口城市自由贸易式的宽容,在古典音乐领域,汉堡留给多数人的印象则带着几分技术味道——毕竟,钢琴制造业在这个城市里太过鼎鼎大名。
无论是就其规模影响还是所制钢琴的音色特点而言,总部恰位于汉堡的施坦威(Steinway)都堪称钢琴制造业中的王者。2010年9月初来到汉堡,正逢施坦威钢琴艺术节。名为“艺术节”,却没有许多艺术节中常见的竞技项目,因为竞技部分已经在此前的施坦威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中完成,在汉堡的艺术节更像是为优胜者们准备的一次假日旅行,所谓“与音乐同乐”而不只是“演奏音乐”。虽然也有演奏会,但更多的是逛动物园、坐游船,一切日程安排都考虑到了孩子们的年龄。最后一天是参观施坦威的工厂,工人们的一丝不苟与孩子们的雀跃恰成对比。这些身价高昂的钢琴在袒露出自己的种种机关、构件后,看起来更像是某种拼插玩具。当孩子们在调音室外随意弹奏半成品“裸琴”时,那些在音乐厅里大名鼎鼎的曲目也第一次完全失去了它们的作者赋予的各种新愁旧怨,成为纯粹的音响游戏。
第一届施坦威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开始于1936年,即施坦威的第一架钢琴诞生100周年之际,此后就有了每两年一度的施坦威钢琴艺术节。参观钢琴工厂是音乐节期间的一个颇受欢迎的常规项目,说起来也是由来已久,只是这种演奏者与制琴者之间的互动却并非施坦威之首创。事实上,西方音乐史中一直有钢琴演奏家乃至作曲家与制琴师互访的传统。1777年,莫扎特曾拜访当时的钢琴制造名匠斯泰因(Johann Georg Andreas Stein),那时他的兴奋恐怕也近似于仿佛看到新玩具的孩子。关于斯泰因的钢琴的描述已经成为莫扎特书信中最为人熟知的段落之一:“无论你如何触键,音质总是均衡的。它从不会发出刺耳的尖声,从不会过强、过弱或是完全失声。与其他钢琴相比,斯泰因的钢琴别有独到之处,因为它们带有擒纵机构。100个制琴师中只有一个会费心想到这点,但假如没有擒纵机构,击键后很难避免出现尖声和振荡。弹奏斯泰因的钢琴时,无论你击键后手指是否移开,琴槌击弦后会马上落回原位……”莫扎特的描述相当专业。在钢琴制造史上,斯泰因确实是附带擒纵机构的“维也纳式击弦机”钢琴的奠基人之一。称其为“维也纳式”,是因为斯泰因的女儿后来将家族产业移至维也纳。斯泰因家族后来又成为贝多芬的朋友,为他提供过钢琴。
莫扎特拜访斯泰因是在德国南部的奥格斯堡。1789年4月,莫扎特由维也纳北上普鲁士,多数传记将此次近两个月的旅行定义为“求职之旅”。莫扎特北行的终点站是柏林,没有记载他来过更靠北的汉堡。然而,这并不代表汉堡在18世纪对于音乐家没有吸引力。恰恰相反,音乐史上倒是留下了另一段轶事:泰勒曼(G.Philipp Telemann)自1721年担任汉堡大教堂乐长后就不愿离开,莱比锡来邀请他担任乐长时,他反而将这一位置让给巴赫,自己终老于汉堡,直至1767年去世。这里所说的“巴赫”自然是最著名的老巴赫(J.S.Bach)。莫扎特和巴赫家族之间的关系颇有些渊源。“伦敦巴赫”(J. C. Bach)自不必说,他称得上莫扎特最早的恩师兼挚友,除此以外,就是“汉堡巴赫”。
“汉堡巴赫”全名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C.P.E.Bach),说起来其实是老巴赫的一堆孩子中当年事业最成功的一个。他与汉堡结缘也因为泰勒曼的缘故:1767年,泰勒曼去世,留下乐长的位置后继无人,次年埃马努埃尔·巴赫就奉腓特烈大帝之命接任。泰勒曼实际上也是埃马努埃尔·巴赫的教父。与他的前任一样,埃马努埃尔·巴赫也终老于汉堡,直至1788年去世。假使说莫扎特和“伦敦巴赫”之间是一见如故的忘年之交,莫扎特和“汉堡巴赫”之间的关系更接近未曾相见但神交已久。在18世纪后期直至19世纪初,“汉堡巴赫”的名声实际上远盛于他的父亲——海顿的音乐启蒙大多得自他创作的练习曲,莫扎特称颂“他是父亲,我们都是孩子”并亲自指挥演出过他的清唱剧《耶稣复活与升天》,甚至脾气乖戾的贝多芬也没少说他的好话。他的著作《论键盘乐器演奏艺术的真谛》是当时的权威典籍,至今仍是研究18世纪键盘乐器演奏方法的重要依据,同时他也被奉为近代奏鸣曲式的创始人。“汉堡巴赫”声名落于他的父亲之后,据说始自舒曼那个年代。舒曼说:“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音乐家,他还远逊于他的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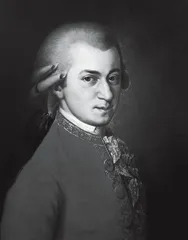 ( 莫扎特和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 )
( 莫扎特和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 )
北上柏林时,莫扎特曾途经莱比锡,特意在这里弹奏了老巴赫曾演奏过的管风琴以示致敬。从时间上看,莫扎特不曾拜访“汉堡巴赫”是因为后者当时已经去世。如今想要探访“汉堡巴赫”也不容易,除非确实有心,否则很少有人会留意到,他的墓地就在汉堡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圣米歇尔教堂(St. Michaelis Church)的地下墓室里。
圣米歇尔教堂始建于17世纪,逐渐成为汉堡最重要的教堂,但随后几百年间因雷电、大火、轰炸几度被毁但又几度重建,目前的建筑是1983至1996年重建的结果。尽管它的地下墓室是欧洲最大的,但整座建筑中最著名的还是钟楼。倘若不想跟随大批参观者登钟楼观光,略付点小费就可以说服看门人免票直接进入墓室。墓室里有教堂自身历史的常年陈列,刚进去时很容易被展柜的灯光晃得忽略脚下一块块方砖上镌刻的墓志铭。小心地从脚下墓碑的间隙一路走进去,墓室尽头最显眼处是一处看不出供奉何人的祭坛,其次醒目的是18世纪重建教堂的建筑师索宁(Ernst Georg Sonnin)的墓地。转过半圈,熟悉了墓碑的排列年份后才回首发现“汉堡巴赫”的墓地就在入口不远处。一块不大显眼的标志牌指明这里是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的长眠之地,但最与众不同的还是墓碑上方插在水杯里的一支粉色玫瑰。静心细看,玫瑰还在微微颤动,即便知道是临近通风口的缘故,却也平生敬意。周围间或有四五游客,驻足此处的却是寥寥,于是那支玫瑰益发多了几分神秘。
 ( 汉堡施坦威的制琴者 )
( 汉堡施坦威的制琴者 )
寻找当年“汉堡巴赫”的故居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几乎所有的讲解员都以“汉堡的老建筑大多毁于战火”来回应这个问题。唯一可以猜度的是按常规乐长的住处不会距离教堂太远。出教堂四处逡巡一圈,几乎迷路之际却见一幢红砖楼上有铭牌:“1809年2月3日,雅各·路德维希·费里克斯·门德尔松·巴尔托迪出生于此地。”
圣米歇尔教堂距离现在的汉堡市政府不过10分钟步程。虽然几经重建,因临近港口,这片区域一直是汉堡的行政与贸易中心、繁华富庶之地。不亲临此地,很难真正明白门德尔松在那个年代的音乐家中所拥有的独到的优厚家境。门德尔松的祖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是著名哲学家,属于汉堡颇有名望的“康德学派”,有“智者纳达”之称;门德尔松的父亲是汉堡的银行家,母亲是当地珠宝商的千金,以文化素养和音乐才能闻名。门德尔松本人却很难说是汉堡人,因为他们全家在1811年就因拿破仑军队占领而迁居柏林,此后再未返回汉堡。只是门德尔松晚期创作的《伊利亚》在后世学者看来自“汉堡巴赫”的《荒野中的以色列人》借鉴颇多,说起来也算续上了在老家汉堡的这点邻里因缘。
 ( 汉堡市景 )
( 汉堡市景 )
尽管在宣传册子上以门德尔松和勃拉姆斯的出生地为荣,但真正让汉堡认可为“自家人”的还是勃拉姆斯。2010年9月5日,施坦威钢琴艺术节最重要的节目“天才儿童音乐会”在汉堡久负盛名的莱茨音乐厅(Laeiszhalle)举行。音乐厅前的广场便以勃拉姆斯命名,音乐厅内还有一尊雕塑家克林格(Max Klinger)创作的著名大理石雕像,雕像上众女簇拥,勃拉姆斯身裹长袍淡定立于其中,膝下另有一做崇拜状的少男。
莱茨音乐厅距离市政厅的步程并不比门德尔松家的相对位置远多少,只可惜方位远离港口等传统繁华地界,从“鹅市”等地名上看,情调也降低了不少,但这里就是勃拉姆斯的父亲和他本人早年活动的区域。关于勃拉姆斯的出身,大多数可见的介绍是:“1833年5月7日,在德国汉堡的贫民区一个职业乐师家庭里响起了婴儿的哭声。”如今来到汉堡,可以在距音乐厅约800米处一个很幽静的小巷里发现勃拉姆斯博物馆,馆中有多种语言的勃拉姆斯生平介绍,甚至有略牵强的中文译本。馆藏也算可圈可点,只可惜这里根本不是勃拉姆斯曾经住过的地方,只是有人捐赠出的老房而已,隔壁据说还在筹建泰勒曼的博物馆。拜访勃拉姆斯真正的出生地,对异地人来说是需要些勇气的,因为那里已经是一片涂鸦满目、酒徒高歌的待拆迁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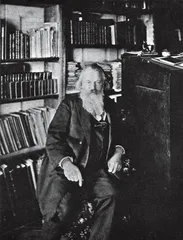
勃拉姆斯出生不久他的父母便搬离了这片如今已近荒芜的住宅区,但随后的住处也没有更多的改善。循历史记载寻找,勃拉姆斯一家的住处一直围绕在莱茨音乐厅一带,而具体地点连博物馆中的讲解员也无法精确定位,除司空见惯的战火原因外,只说是勃拉姆斯的父亲根据工作地点的远近和薪水的多少经常搬家。能依稀寻到的几处故居都距离汉堡的圣珀利(St.Pauli)区不远,而圣珀利区中如今最著名的是“绳索大街”(Reeperbahn)。这条街的名字缘自当年此地聚集了很多为船舶制造绳索的匠人,如今这里多的却是善在桌上与钢管边起舞的女郎。当然,还有披头士。
一直让汉堡引以为荣的是列侬的那句名言:“我出生在利物浦,但我成长在汉堡。”20世纪60年代初,初具雏形的披头士乐队来到汉堡,在绳索大街的Star-Club、Kaiserkeller、Top Ten和Indra几家俱乐部驻台演出,他们于1962年新年之夜在Star-Club的现场演出他们的第一张录音专辑。尽管列侬等人此间曾因劳工问题被德国当局驱逐出境,但后人已经普遍认可汉堡是披头士的故乡,如今更是在绳索大街上建起了披头士的纪念馆。
 ( 依次为:门德尔松、勃拉姆斯、泰勒曼
)
( 依次为:门德尔松、勃拉姆斯、泰勒曼
)
“那个年代,汉堡还没有摇滚乐俱乐部。”披头士传记《Shout!》中这样记载,“有个与众不同的俱乐部老板名叫布鲁诺,此前是个露天游乐场演出主持人。他想到一个主意,引入摇滚乐队在不同的俱乐部演出。他们制定了一个公式,那就是大型的不中断演出,一小时接一小时,乐队要不停演奏以抓住流动的人群。”列侬的回忆是:“在利物浦,我们每次只需要演一个小时,于是我们只演奏我们最好的曲目,每次都是同样的歌。而在汉堡,我们每天要演8小时,这样我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演出方式。”后来曾经有人统计,自1960到1962年末,披头士共到访汉堡5次。第一次演出106次,每次5个小时以上;第二次演出92次;第三次演出48次,在台上待了172个小时;最后两次汉堡之行分别在1962年11月和12月,一共是90个小时的演出。加起来他们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演出了270晚,到1964年一鸣惊人时,他们的现场演出纪录将近1.2万小时,而今天的很多乐队整个职业生涯也没有演出过1.2万小时。
听到这个纪录,生活在上一个世纪、但住处也离绳索大街不远的勃拉姆斯肯定会有惺惺相惜的感觉。为维持家里生计,勃拉姆斯13岁起就在剧院帮助父亲演奏。为了多挣些钱,他还在酒吧担任钢琴师,在专做船员生意的酒店里为舞会弹伴奏。据记载:“他彻夜工作,酒馆的老板用酒刺激他,让他通宵达旦地弹琴。‘职业女郎’拉着他坐在她们的腿上,对他百般勾引……”

20世纪60年代的汉堡正处于它最艰难的年代。汉堡本是德国最主要的港口,也是当时的世界第三大港,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轰炸使这座城市化作一片废墟。披头士到达时,这座城市正以罪案泛滥、无法无天著称于全欧。列侬回忆中的“戴着马桶坐垫上台、拉屎撒尿”确实有可能在当时的汉堡出现,但这种自由的气氛在汉堡却并非60年代专属。如今的披头士纪念馆建在绳索大街与“自由大街”(Gro?e Freiheit)交叉处附近,自由大街的名称得自两三百年以前,其时这片区域与汉堡城区若即若离,因此允许天主教徒在此处奉行自己的信仰,而这种行为在新教遍地的汉堡城区是严格禁止的。假如说披头士的音乐代表了某种叛逆,则汉堡的音乐味道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就混杂着叛逆和仿佛与之矛盾的皈依。1897年,马勒专门从维也纳跑到汉堡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排开了身为犹太人的最后一层障碍,终于顺利得到盼望已久的维也纳国立歌剧院指挥的职位。门德尔松出身显赫的犹太家庭,但在小时候就由父亲带着在路德教会接受洗礼成为新教徒,这也是他姓氏后面德国式的“巴尔托迪”的来历。1830年,于新教有重要意义的“奥古斯堡信仰告白”(The Augsburg Confession)成文300周年纪念,门德尔松还为此专门创作了《宗教改革交响曲》。
后世研究者认为,门德尔松创作《宗教改革交响曲》的动机有二:一是公开表示他对新教的肯定,二是表示对马丁·路德的敬仰。在汉堡的圣米歇尔教堂的墙外,正矗立着一座马丁·路德的雕像。在教堂的入口处,墙上镶嵌着一块铭牌,上有马勒的头像,下面的文字说明马勒的挚友、指挥家彪罗(Hans Guido Freiherr von Bülow)1894年在此下葬,而他的葬礼给了马勒创作《第二交响曲》的灵感。教堂的地下墓室里是埃马努埃尔·巴赫的墓地。名流汇集之时,似乎缺席了有“汉堡之子”之称的勃拉姆斯,不过彪罗名字的出现也算代替了——正是在彪罗的努力下,1889年,贫民区出身的勃拉姆斯终于得到“汉堡荣誉市民”称号。
在2010年施坦威钢琴艺术节举办期间,汉堡市立美术馆(Hamburger Kunsthalle)正在举办名为“一切艺术都曾是当代艺术”的展览。展览将相近主题的当代作品与19世纪乃至16世纪古代名作并列展出,如此安排颇具有典型的汉堡式自由味道,恰似圣米歇尔教堂内外时空交错的名流汇集,也让人不由又记起勃拉姆斯的住处和披头士当年的蜗居不过几条马路之隔。混杂的结果之一是,名为“艺术”的东西在汉堡似乎更容易回归到它原本不加修饰的面目,正如施坦威那些袒露了内部结构的钢琴——被评论家装饰以各种玄幻的音乐在此一眼可以望见实际只是木头、毛毡与金属间的游戏。只是一切又做得如此细致精湛,倘若将此称为汉堡的音乐味道中的那点机油味,我想汉堡人也不会太反对。■ 莫扎特门德尔松味道汉堡艺术音乐作曲家巴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