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勺园图》
作者:曾焱(文 / 曾焱)
 ( 翁万戈私人收藏的吴彬《勺园祓禊图》(局部) )
( 翁万戈私人收藏的吴彬《勺园祓禊图》(局部) )
两幅《勺园图》的缘起
“我的高祖翁同龢,在他光绪十一年四月十二日(1875年5月25日)的日记上有记载:‘傍晚归,见吴彬画米万钟《勺园图》。’大概当日或其后不久,这图卷就入了他的收藏,一直到今日,历经五代,已过了125年,其中最后的61年,都随我在美国。”著名美籍华裔收藏家翁万戈先生向本刊回忆起吴彬绘《勺园祓禊图》和家族的结缘。
20世纪50年代,翁万戈拜识了燕京大学的洪业教授。洪业知道他藏有这件吴彬的杰作,1967年8月8日,特意赠送翁万戈一册自己的著作《勺园图录考》,为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1932年出版。从这本书中,翁万戈初次见到存世的另一幅《勺园图》——米万钟绘《勺园修禊图》的黑白照片,那是“旧藏天津陈氏,近归燕京大学”。仔细对比后,翁万戈认为,米氏应该是忠实地依照吴氏原画临摹了一遍,得出这结论的根据有两条:吴彬自题其画:“乙卯岁上巳日(1615年3月31日)写。”米万钟自题其画:“丁巳三月(1617年四五月间)写。”二者相隔两年多,而米氏图中一草一木、一人一物、一屋一桥都不离吴氏的原作。
勺园主人米万钟是明后期一代名士,“以诗文书画名天下”。又因酷爱搜集奇石,号友石、石隐。米万钟和吴彬相交至深,清初画家王崇简在吴彬的《勺园图》后作跋时记述:“吴文中昔馆于米友石先生家最久。为图勺园卷,极备。”园中正堂“勺海堂”,所挂匾额也是吴彬的篆书,可见他当年确实是园中常客。
翁万戈在美国守藏家传数十年,其间赏鉴研究吴氏《勺园图》。他从画中的几个细微处,体悟到了当年米万钟对吴彬此画的“爱之如命”:“勺园为米万钟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所建,意在仅取海淀一勺水。可是到了明熹宗(天启1621~1627)时,宦官魏忠贤掌权,迫害东林党人,至1625年明代进了政治最黑暗的一页时,米氏被劾削职。想在该年他为了保存吴彬的《勺园图》,把画首上右角的画家自题谨慎撕下来保存,并将画中标明建筑及景观的题名一一磨去(忽略了三处),以免匪人发现其为米氏勺园而毁其图,这真是爱之如命的行为。崇祯元年(1628),思宗登基,魏珰被除,米氏起为太仆少卿,吴彬自题得裱回原处,但图中小字就失去了。同年米氏去世,再过16年,明亡,勺园也变成‘一望荒烟白草,无复遗构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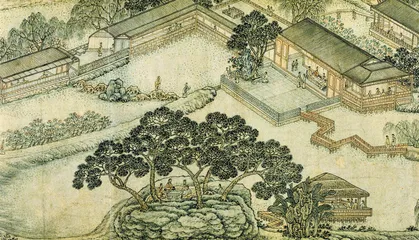
这样一幅“荒烟白草”的图景,为王崇简在跋中所述。他和勺园之间有着比同时代人更为亲近的关系:万历四十四年初(1616),王崇简15岁时曾亲见米万钟在园中宴饮。多年后王家又和米家结亲。翁万戈告诉本刊:“王崇简为米万钟之孙米汉雯的岳父,他曾游览园中,知道吴彬所画为实地描写,他从市场上购此卷,赠给其婿,亦即米万钟之孙。可惜那时他还有吴彬画的勺园大幅,而此图已好久不存世间了。”吴彬的《勺园图》得来也偶然,王崇简在跋中提及:“市儿偶以此卷求售,以数千钱易之。”
明代两大名家各写勺园,多年来,一幅画在北大找到归宿,另一幅隔海由翁家世藏。北大被认为是勺园故址所在,而翁万戈本人与燕京大学也颇有因缘。翁万戈1918年出生于常熟名门望族,高祖翁同龢为晚清名宦、两代帝师。恰好在他出生那一年,美国几个教会协议将各会所设学校合成“汇文大学”,旋即并入该年成立的燕京大学。1936年从汇文中学毕业后,他因成绩不错被保送燕京,同时也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因为上海离老家常熟近,便于去拜望过继的母亲,他没有入燕大。直至今日,年逾92岁的老先生仍对燕大心存厚意。“现在燕大已经并入了北京大学,所以我虽非校友,但也‘心向往之’!”翁万戈对本刊说,为尽保存中华文化遗产的一份责任,他决定将吴彬的《勺园图》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使它与米氏《勺园图》在近400年后重归一处,而且是在勺园故址上的建筑内珍藏。9月13日上午,老先生在女儿翁以思的陪同下,抱病专程从美国飞回北京,在捐赠仪式上,亲手将吴彬的《勺园图》递交到北大校长周其凤教授手中。

《勺园图》的研究价值
“其实《勺园图》不止这两幅,目前所知存世的应该有三幅。”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沈乃文告诉本刊,除了北大和翁家所藏,广州市博物馆里还有另一幅《米万钟写勺园图》,人物布局、画卷长度和这两幅都差不太多。“得翁先生无私捐赠,北大现在就有了两幅,另一幅也在国内,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北大图书馆以前也接受过捐赠,唯有翁先生这次捐画是分文不取,令人感佩。如果吴彬这幅画作拿去拍卖,肯定是个巨大的数字。”

沈乃文对本刊说,北大图书馆很少收藏书画,但于米万钟是例外。“北大图书馆最主要的收藏是线装古籍,有150万册,数量居世界前四。而书画很少,几乎没有。但北大所在的地方,在300多年前可以说就是米万钟的,因为所在地的关系,我们特别注重收藏米万钟的字画,共有六七件,首先是书法,还有他画的松、石。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这幅《勺园图》了。”沈乃文告诉本刊,米万钟在明末与董其昌并有“南董北米”之誉,不过现在认为他的书画成就远不及董其昌,但这个人很有风骨,先是力拒魏忠贤,抗清时又亲自拿刀守德胜门。米氏著述现在几无流传了,亲笔书画在国内外还存世近百幅,如南京博物院藏《灵石图》,重庆博物馆藏画石长卷,广州市美术馆藏行草长卷《夜过梅岭》,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古寺云山图》,美国私人藏《竹菊图》。北京故宫藏清宫旧物“青花出戟觚”,底部楷书款记“大明天启年米石隐制”,想是米万钟于江西按察使任上所制,应该是他留下的唯一瓷作。
几代学者研究《勺园图》,角度都不一样。沈乃文说:“要说到研究价值,第一条就是北京的地理。史载当年什刹海里桅杆遮云蔽日,这些在我们今天都不好想象了。北京历史地理变化最显著的就是水的变化,尤其是海淀这片。海淀一名的源起,不晚于元代,本义并非指某一地域,而是专指水面和湿地。但是现在的畅春园、海淀体育场、北大宿舍区,一马平川,既没有山也没有水。《勺园图》毕竟有实景,可为凭据,从画上我们看到,原来北大这块儿当年像沙家浜一样,都是水乡,周围广植白莲,还有成片的竹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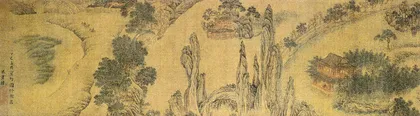 ( 北大图书馆收藏的米万钟《勺园修禊图》(局部) )
( 北大图书馆收藏的米万钟《勺园修禊图》(局部) )
沈乃文认为重视《勺园图》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从中了解明后期的社会生活。“明代中期以后,文人士大夫以及地方殷实人家,修建私家园林之风极盛。南方北方,竞相园居,召饮唱和,当时称为一派承平景象。这与其前的宋元和其后的清代相比,都是十分突出的。”沈乃文告诉本刊,米万钟的生活形态在同朝文人士大夫中并不见特殊,是当时境况的一个局部。米家也不止这一个园子,除勺园之外,据《燕都游览志》、《帝京景物略》等古籍记载,他在“长安之苑西”修有湛园,在距积水潭北岸的静业寺不远处建有漫园。三处都是京城名园。“后人从《韩熙载夜宴图》推想当时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意趣。《勺园图》也一样。比如从米氏《勺园图》上我们看到,勺园有门,但门是柴扉,而不是朱漆门或垂花门,这有他的品位和格调在里面。园里多种白莲而非红荷,如果没有图在,今人也很难想象。桥是曲折的,栏杆漆成红色,而清代皇家园林里都是汉白玉栏或绿色的木栏。”
勺园故址文化
 ( 收藏家翁万戈
)
( 收藏家翁万戈
)
在勺园研究中,使人感兴趣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勺园的原貌是什么样子?勺园的故址到底确定在哪里?时代隔得越久,求解的兴致越高。明末以后不乏关于勺园的著述,洪业在《勺园图录考》中即征引了明人著作31种、清人著作48种、外国人著作6种,考校的史料也有200多条。明末清初文人笔下的勺园大多偏重文学描摹,相比之下,孙国敉的《燕都游览志》被认为较实,他对百亩园宅里各个景观的位置及上面的题写都做了记述,其中几个著名的景观如风烟里、缨云桥、文水陂、定舫、勺海堂等,在吴氏和米氏的《勺园图》上也有绘画,可作对照。
“勺园当时的具体面貌是什么样,我们现在只能凭这几幅画来推想。不过古人画山水画,有些固定的套路手法,凭画卷景观推断事实景观,还是会有些差距。”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唐晓峰教授告诉本刊。他主要研究城市历史地理与地理学思想史,看勺园有自己的角度。他说:“关于勺园原貌的特点,或许可以这样说:勺园用水用得好,这在北方园林中比较难得。南方、北方水与房子的关系,习惯差别很大。南方人喜欢傍河,房子紧靠河边,而北方人通常会让房屋离河远一点,很少见到水上人家,这是因为北方的河流水势变化大,一会涨水,一会没水,房子不可能随着水势变化位置,所以只好以涨水为限,摆得远一点。勺园是利用泉水的稳定,设计了与水亲近的台榭,就有江南韵味了。勺园的第二个意义是它造园的时间较早,在明末建成,是北京西郊园林史上最早的园子之一。西郊园林的大发展是在清代。现在从北大西门进去以后往右拐,能看见小湖泊,那一带应该就是勺园旧址,水还在,但建筑全都没有了,现在是北大外国留学生的居住中心,就取名‘勺园’。记得勺园楼群建设之前,这里还有大片空地。说起来有意思,清朝的时候,这地方也曾用来接待来华的外国使团。”
勺园荒落也很迅速。沈乃文对本刊这样说到以后在园址上的几次变迁:“勺园在明末战乱中全毁,清初在园址上改建的园林,又于咸丰十年(1860)被侵入京师的英法联军在火烧圆明园之前,与海淀镇街市一起焚毁了。废园于宣统年间由清廷赐给贝子溥伦。1921年燕京大学购得此园之北的淑春园,建为校园。溥伦在去世前两年的1925年,也将园子售与燕大,与淑春园连成一片。当时园内北部是湿地,南部有两片淤塘,芦苇芜蔓。1952年北大迁到海淀,这里又成为北大校园的一部分。随着北大和周边地区的发展,道路沟河一再迁变,内外旧貌与旧界全都湮没了。”历史上,勺园和清华园东西相连,并称为明末京城两大私家园林,明末宰辅叶向高评说:“李园壮丽,米园曲折,米园不俗,李园不酸。”沈乃文说,清华园为武清侯李伟所建,当年洪业先生曾指出米万钟的第一位妻子李夫人“疑是武清侯李伟族人”,即明万历帝生母慈圣皇太后的族亲,如果是这样,两园隔路相望就不是偶然了。明亡后,清华园在康熙年间被圈禁为皇家园林,改建为畅春园。
唐晓峰告诉本刊:“勺园文化,很多年前就已经成为学者研究的领域。每有新的史料发现,学界都很重视。洪业先生是最早对勺园进行研究的学者。当年是他从市场上购得米万钟的《勺园修禊图》。后来我的老师侯仁之也研究勺园,正是研究勺园及其附近地区的历史,引发了侯先生的历史地理学兴趣。现在,北大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沈乃文是一个重要的勺园研究者。”唐晓峰告诉本刊,大约十几年前,有位来北大的美国教授对勺园文化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叫欧迪安(Diane Obenchain),当时就住在勺园五号楼北侧房间,窗外正对仿建的古式长廊,每天推窗可见。我介绍她认识侯仁之先生后,侯先生给她讲了很多勺园掌故,欧迪安于是对自己每天起居的这块地方着了迷。那时,她家刚在美国华盛顿附近买了新房,先生在美国装修,特意把后花园命名为‘勺园’。后来,欧迪安筹资复制了北大图书馆所藏的《勺园修禊图》,是请日本二玄社做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到北大演讲,校方即以一幅复制的《勺园修禊图》作为礼物相赠。”
“现在勺园已经成为北京古代园林文化的一个代表,也是北大人文气息的一个标志。燕京大学以及之后的北大校园,都因勺园而更有历史感。如果勺园遗址不在燕京大学校园里,而是在远一点的西郊什么地方,很可能也就被后人忽略了。这一次翁先生捐出自己珍藏的吴彬《勺园图》,又为这个地方增加了文化厚度。”唐晓峰说。■
捐赠的念头1967年就有了
——专访著名美籍华裔收藏家翁万戈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勺园在历史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名气?
翁万戈:勺园之享有盛名,除当时人认为“雅”之外,也因现在只有欣赏吴彬的画,领略一下其造园艺术。我个人曾研究过中国园林,苏州以及扬州等仍存的名园都身历其境,大致说来,我认为园林之美在于陆地之“径”之各种建筑,而水尤其重要。勺园之水,有船游之,有桥跨之,有树根点之,真是匠心独运,极其灵活。勺园并未经过重修,因为甲申1644年之变,勺园被毁,一片荒烟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你捐赠的吴彬《勺园祓禊图》,曾经过哪些人收藏?
翁万戈:关于这幅画的递藏故事,只能见于其跋中:先由米万钟之孙米汉雯的岳父王崇简从市上收购,送给汉雯,归入米家,其后不详。宋之绳为王崇简的同年,同为1643年进士,但我认为他题写的跋并不说是他收藏过,而是他为王崇简作跋。乾隆第五子(皇五子永琪)作有长跋,他曾收藏过,而其子绵亿也在乾隆甲辰十二月(1785年一二月间)写了一行字,此后便没有消息了,直到翁同龢在1855年收藏,一直留在我家至今。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决定将这幅画捐给北大?
翁万戈:捐赠的念头是我在1967年得到洪业老师《勺园图录考》时引起的,但要等到1979年我能够同老伴程华宝回到新中国才明晰。在80年代,我们曾专程到北大图书馆拜观米万钟的临本,同时走遍校园的每一角落,追寻勺园的遗迹。后来侯仁之老师访美时,曾光临寒舍莱溪居,纵谈勺园故事,并增强了我愿吴彬《勺园图》回家的信念。
三联生活周刊:据你所知,吴彬的画作目前存世大约有多少件?
翁万戈:吴彬画作,存世者当有数十幅。我见过的就不止十几幅。手头我有他的《十六应真》手卷的照片,很巧,其卷首的大字就是米万钟写的,画曾藏北京故宫,有乾隆御玺,见《秘殿珠林》。画极精,现不知在何处。吴彬山水也极奇特。■ 勺园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