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和《知青变形记》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苌苌)
 ( 韩东 )
( 韩东 )
到今年,韩东的文学创作生涯已经走过整整30年。40岁后,他的生活围绕写作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秩序。每天早餐后,他步行或坐车去工作室写作,甚至在大年初一也不休息。那是位于一栋居民楼里的老房子,韩东在那里读书,做笔记,打坐。打坐治好了他的颈椎病和失眠,每天写作两到三小时,在写作每部长篇小说之间,他会休息半年,为下一部小说构造框架,积累素材。一旦写作开始,他就进入自己称之为的“闭关”状态,写作初稿的最初几个月,他不接受采访,也几乎不和外界朋友交流。“在这个状态中,自己也会变得很脆弱。”他对本刊记者说。
“这基本是一种很磨人的心理状态,你不知道这部作品的容量,也听不到任何评价。写长篇不仅是体力考验,还有这种沉郁的心情,在写完前,可能一两年你都看不到任何价值的体现。”在近年适应了这种状态后,韩东觉得可以把写作时间拉得更长一点,书写得更薄一点,他也尝试不要让自己太拘囿于写作的孤岛。“我把写长篇看做是自己的主业,但进出其他门类的艺术、和其他艺术家交流,对我接下来的写作有很大帮助。你得走出去看看其他艺术家是怎么工作的,每次交流获得一些认同、一些新想法,然后再回来写我自己的。”
就像很多职业小说家一样,他们的生活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丰富多彩,反倒为了保护写作的气场比常人更为闭塞。“这几天我看足球,以前我只是看拳击。工作室的电视没有接天线,朋友给我个电话,我就跑到另外的地方看。我也上网聊过天,偷过菜,但意识到让我太沉迷就会掐掉。写作之外的事情真正能让我上瘾的很少。”韩东说。
韩东有很多朋友。在南京的年轻作家和文艺爱好者喜欢和他亲近。他对本刊记者说:“我们这代人,我见过的很多都是历经沧桑,他们沉浸于此,让我也了如指掌。我觉得那种状态其实并不很好,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新鲜的和好玩的事物,我喜欢和年轻人亲近,以前是比我小个五六岁,现在可能小20多岁,我入行较早,有些经验可以和他们分享,或者给他们做些推荐。但很多时候,我们很少谈艺术,对我这样一个没有单位的人来说,可能这就是我的单位了。朋友对我的意义像亲人又像同事,这就是我的社会关系,通过他们和社会过一种集体生活。”2006年韩东再婚,此前的19年他过的是某种形式上的集体生活。“生活不稳定,情感不稳定,那时我需要很多朋友。”韩东曾经形容南京就像一张腐朽的温床,从正面意义理解,在南京与朋友在一起,他可以尽可能少受时代变革影响,按照自己的步调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觉得基本的安全感是靠财富建立起来的,但对我来说,基本的安全感始终是你的身体状况。”
韩东生于1961年,17岁就读于山东大学哲学系,19岁开始发表诗歌。毕业后先后在西安、南京两地高校教书,1993年辞职成为职业作家。从20世纪90年代起,他开始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进入2000年后开始长篇小说创作,10年间,他写了4部长篇小说,其中3部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1969年8岁的韩东随父母下乡,直到1978年上大学。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扎根》更多是他对下放生活的回忆,《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则是写20世纪70年代县城少年的传奇,而《知青变形记》则脱离了他本人具体的经历,是一个杜撰的荒诞故事,讲的是一个没有回城的知识青年,如何阴差阳错、一步步变成地地道道的农民。在《代序》中,韩东提到为什么触碰知青生活这个并不新鲜的主题。他说,因为近年“大量文艺作品的塑造,历史真实已经烟消云散。戏说不仅是戏说,同时还固定了人们对这些历史时期的标准想象”。而对这些关于知青的标准想象,韩东是不满意的,或者感到有所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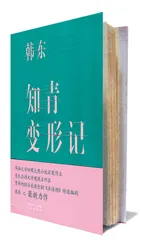 ( 作品《知青变形记》 )
( 作品《知青变形记》 )
知青罗晓飞为争取回城积极表现,要求饲养生产队唯一的一头耕牛,后耕牛因病趴窝,罗晓飞遭到公社人保组的非法审讯,被诬陷为“破坏春耕生产”而几近身陷囹圄。恰在此时,村里的兄弟俩打架,哥哥失手打死了弟弟,罗晓飞以冒名顶替的身份获得新生。故事由此展开,跨越10年,琐碎的生活和人情冷暖,最终罗晓飞选择和命运和解。但作者对事态的总结并非单一,小说里也包含了一个哲学命题:名字和身份的转变,就可以把一个人与以前的人生割裂,那么我们到底是谁?是否领教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可以对命运的践踏不以为意?
韩东视这部小说为他的转型之作,他说,因为从这部长篇创作始,他认真思考了与读者的关系,开始进入流程化职业写作阶段。“以前觉得小说只是在自我天地里的自由表达,有时会去追求极端。但小说离不开读的层面,只有通过充分的阅读才能成立,作家对此要负起责任。我们国家不管是体制内写作还是体制外写作,都是青春期才子式的,在写作前没有准备,写完后也不修改,依赖即兴发挥,出来一堆东西都是散文化的、天才式的。相对来说,电影、建筑等艺术则对作品的流程意识得比较明确,有创意,有方案,有论证,然后才是创作过程,要思考怎样达到预想的目的。现在写小说的挑战,就是你要能让小说自身的可能性和魅力说话——只要读者开始读,就能被吸引住,读完后也有所收获。”他说。
韩东的作品一直以来对荒谬情有独钟。笔法是现实的,但讲述一个非现实的故事,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讲清楚现实问题。采访中,他提到一个令他颇有感触的韩国电影《密阳》,一个女人的孩子被绑架撕票,在巨大的痛苦中她信了上帝,沉郁得以解脱。后来绑匪被捕,她去监狱里宽恕绑匪,而绑匪说:“我不用你宽恕,上帝已经宽恕我了。”她立刻就崩溃了,这之后她又变成一个反教人士。韩东说这种核心的转折点令他着迷。他在《知青变形记》中设置了一个核心,核心冲突是罗晓飞被诬告,在很短的时间,他要决定要么选择冒名顶替,要么身陷囹圄。这个创意成为他的发力点,他调动起所有的热情和精力,花了一年时间研究当时的史料、知青的回忆录,直到有了一切尽在掌握的状态。“反映现实,不可能不保持距离感,一直以来我就喜欢非现实的意蕴。小说不在于你讲什么,而是怎么讲,故事是不是当代也不重要,背景是‘文革’,但那种荒诞也可能发生在任何时代。”就像玛格丽特·杜拉斯在不同的年龄不停地回到中国情人的主题,持续经年,她的小说已经不是在讲西贡了。
韩东至今仍然保持自由职业作家的状态,决定组建家庭后,他承担起作为丈夫、一家之主的责任,但也不意味他要放弃小说家的责任。他说:“对我来说,将小说家作为职业没有问题,尽管对很多人来说不是这样。当职业作家不容易,你对好车好房有兴趣,那没有问题,现在人们生活越来越多元化,但你如果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就不要拿悲壮感来感动自己。写作不是不能生存,但你得专业。小说是一个专业,有一定规矩,从酝酿到构思到创作,有很专业的流程。我选择这种生活方式,里面有它无可比拟的自由和美好。给社会带来什么?一阵快意,一阵心领神会。”■ 文学小说韩东作家变形记知青变形记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