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莫里斯的游记
作者:薛巍
简·莫里斯
身为记者,莫里斯有幸见证了很多历史性事件。她在1953年第一个报道了珠穆朗玛峰首度被人类征服;1960年,她在报道联合国大会时目睹了赫鲁晓夫脱下鞋子拍打桌子以示抗议;1961年她在以色列旁听了对艾希曼的审判。她在哈瓦那采访过格瓦拉,30年后,在英国搭乘了一个T恤上印着格瓦拉头像的搭车者,她对这位搭车客说:“我敢打赌,在你搭过车的人中,我是唯一一个亲眼见过切·格瓦拉的。”
报社为莫里斯提供了观察各种事件的大看台,并容许她像对待随笔写作一样对待新闻快讯的写作。在珠穆朗玛峰上没有远程通信设备,为了将消息及时送回,她差点在下山时摔死。为了保证独家,用暗语发消息,如“雪况糟糕”等于“登顶成功”。
在对联合国大会的报道中,她不仅观察细致,对麦克米兰和赫鲁晓夫做了比较,还把握到了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及他们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哈罗德·麦克米伦留着油光可鉴的伊顿公学式的发型,缓慢、拘谨地走上讲坛,看上去沉着冷静又尊贵庄严,他发表了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绅士的演说。赫鲁晓夫则似乎处在最粗野的情绪中,摊手摊脚、面色愠怒地坐在座位上。但后来她发现,她模模糊糊地站在赫鲁晓夫一边,他的行为中有一种会被首相加以充分利用的农民式的诚实与幽默。而且,用鞋拍打桌子表示不赞成,不过是一种旧式的俄国风俗。
《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覆盖了20世纪的后半叶,从50年代到90年代,从“二战”初到千禧年终结。它反映了这个世界50年的进程,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变化:从24岁变成了74岁,从詹姆斯变成了简——1972年她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做了变性手术,她的文风也由此发生了变化,某些批评家说后来她的写作中有一种清晰可辨的解放感。
莫里斯最显著的文风特点是打比方,在对变性手术的记述中,她也发挥了这一本领。诊所里挂着厚厚、柔软的窗帘,弥漫着香水味,让她想起后宫,医生的太太就像一个婢妾。走下一道螺旋楼梯,来到私人区,“一切都是闪光和香奈儿,就像是从苏丹的宫殿走到了宦官生活区,当时我想,这是一个不坏的明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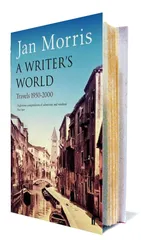 新书《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
新书《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
伊恩·布鲁玛在《纽约书评》上评论《名利场》专栏作家希钦斯的回忆录时说:“希钦斯对波兰、葡萄牙、阿根廷和其他地方英勇的报道有一个缺点,他好像在任何地方待得都不够久,也没见过不是英雄、名人和坏人的人。我们希望听到一个普通波兰人、阿根廷人或伊拉克人的声音。相反,我们只听到了亚当·米奇尼克、博尔赫斯、查拉比,他们都很有趣,但都是例外。我们想知道灰色地带,大部分人多样性的生活方式。”莫里斯的游记则没有这一缺点,在登上回家的航班时,她能回忆起圣彼得堡那位困惑的上校,开罗的学生,夏威夷的独木舟主人,幻灭的里雅斯特人。
周游了世界,莫里斯最喜欢哪个国家、哪个城市呢?肯定不是悉尼,她写悉尼的文章发表后,整整过了5年,从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给她寄去的义愤填膺的反击才渐渐平息。“悉尼的起源不体面,它的历史读起来不愉快,它的脾性很粗鄙,它的组织拉里邋遢,它的郊区丑陋,它的政治往往是欺诈,它那大肆鼓吹的艺术运动我怀疑一半是伪造的。”她认为加拿大是最好的国家,曼哈顿是一座永远不会令她失望的城市,“它有太多超现实之处,它的精神基础是逻辑和理性,但它的日常生活沾满了神经错乱之敏感性的元素与片段。其中一个片段是:一个友好、文雅的著名女演员,穿得很漂亮,搭乘出租车去第二大道参加一场演讲。司机问她去第二大道的什么地方,女演员镇定地说:‘别问我,他妈的你是出租车司机。’”
在全书的结语中,莫里斯写下了她对这半个世纪和她自己的一生的总结:“随着年岁日长,我比以往更清晰地认识到那个终极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没有并且永远不会有答案。多少个世纪以来,最真诚最聪慧的头脑用各种胡言乱语瞎扯过这个问题,从圣彼得教堂的大弥撒到施咒的巫医。照我看来,只需要一条戒律帮助我们处理事务:与人为善。它灵活到足以体谅自由意志和人性的脆弱,但在核心处又坚如磐石。”■ 莫里斯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