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博士的童话乌托邦
作者:陈赛(文 / 陈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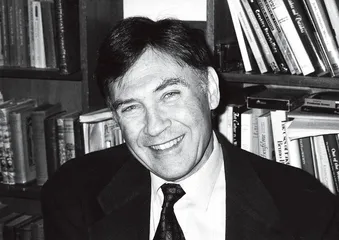 ( 杰克·泽普博士 )
( 杰克·泽普博士 )
《帕那索斯博士的奇幻秀》里有一个与魔鬼打赌的老头,失魂落魄地讲了1000多年的故事。他相信,一旦故事停止,宇宙也将终结。
73岁的杰克·泽普博士也是一个偏执的老头。他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德语教授,却跟童话打了一辈子交道。他相信,无论对儿童,还是大人来说,童话在今天仍然承载着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不仅是补偿,更是启示——真正的好童话一定与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世界对话,它们投射现实世界的真实与虚假,从不放弃幸福的希望。他告诉本刊记者:“好的文学提供希望,而好的童话提供极致的希望。我想这就是我追求的——极致的希望。”
没有谁指引他走进这个领域。从8岁开始,他就坐在图书馆的地板上,自己写故事,自己读给自己听。可能是现实世界太让人困扰,一个孩子天然地想要构想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他说,这就是童话的乌托邦本质。
年轻时,他是那种为了翻译几个童话,可以专门跑去学一门生僻语言的人。他热衷于从故纸堆中搜寻已经遗失多年的古老童话,破译这些童话中的符号与隐喻,从而揭示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想法、品位和价值,对他来说,是一件类似于侦探的工作,给他带来无穷的乐趣。他编撰关于童话人类学的百科全书,收录儿童们代代相传,到了这一代却即将消失的童谣、谜语、儿歌、咒语⋯⋯他向科学家的实验里寻求童话对人类进化意义的证据——因为与人类最基本的欲望与本能相关,童话已经深深植入人类的大脑,成为情绪记忆的一部分,帮助人类适应环境,处理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决定。
退休后,杰克博士放下学术上的研究,将更多心力放在了儿童身上。他认为,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故事的重要意义不下于爱和自由玩耍。婴儿从9个月起就开始学习语言和符号,他们在故事中发展思维,在故事中理解世界,理解人。
 ( 电影《帕那索斯博士的奇幻秀》剧照 )
( 电影《帕那索斯博士的奇幻秀》剧照 )
从90年代开始,他得到乔治·索罗斯的资助,在美国几个不同的城市主持了一系列讲故事的教学实验项目,受到美国教育部的嘉奖。他的实验面向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小学生,利用游戏、表演、画画等手段,教儿童自己如何变成叙事者,开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他选择的故事涵盖了不同的类型,包括传说、寓言、神话、童话、幽默故事等等。比如《小红帽》是一个关于强奸的故事,童话原意并不是警告小女孩小心陌生人,而是指责小红帽的自作自受,她的愚蠢和幼稚导致了自己的失贞。在向孩子们讲述时,杰克博士并没有对这个充满性别歧视的故事做任何的审查或净化,但在讲完原版故事后,他又选了另外一个不同视角的故事,一个现代化的、女性主义版本的故事,来挑战原版的小红帽。在新故事里,小女孩比大灰狼更聪明,并最终战胜了大灰狼。
 ( 宫崎骏作品 《千与千寻》剧照 )
( 宫崎骏作品 《千与千寻》剧照 )
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他从不强加自己的观点,而是与孩子们一起讨论这个故事,给他们一个开放性的情境,让他们按自己的构想重新设计剧情和结局。然后,他还会让孩子们用戏剧的形式把自己的故事表演出来,或者画出来。
“从这些实验里,我们了解儿童如何思考,如何辨别真假,如何对身边的素材做出反应,如何处理新的意想不到的问题。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孩子怎样用自己的语言和图画,在故事与自己之间建立关系,表达自己的个人需求和愿望。”
这样的实验项目在美国渐渐流行开来。比如一个叫克里斯汀的年轻女老师在旧金山的一所小学里开设了一节叫“作者剧场”的课程,专门让学生表演与流行文化有关的故事,故事的主角都来自流行的电影、电视、漫画书、视频游戏,比如《阿拉丁》、《蜘蛛侠》、《美女与野兽》、《星球大战》、《超人》、《街头霸王》等。她认为,既然这些商业文化产品已经在事实上成为美国儿童的主要精神食粮,那么作为老师,至少应该引导他们对这些内容进行判断和质疑,甚而进行有想象力的颠覆,而不是保持缄默。
在杰克博士看来,这些努力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商业流行文化对儿童和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比如迪斯尼。
他本人是迪斯尼的坚定的批评者。在他看来,作为当代世界最大的童话制造者,迪斯尼给儿童们制造的不是希望,而是幻象。“希望和幻象是两回事。迪斯尼的动画片与现代美国毫无关系,它给孩子们呈现的只是奇观,而奇观是具有幻觉性的,它并不能帮助他们理解世界,而是遮盖真相。”
但是,他欣赏宫崎骏,他说:“《千与千寻》是很好的童话,它没有以幸福婚姻为结局,小女孩经历了一场冒险,我们不知道她的未来将发生什么,但能感觉到希望。”
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孩子从小看迪斯尼电影长大,他们长大以后就很难认同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观念。
事实上,他最担心的现象正在发生:全世界的孩子变得越来越相似,标准化的文化创造标准化的儿童。到处是迪斯尼,到处是麦当劳,他们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东西,听一样的故事。这是商业化和全球化的悲哀。
与今天的儿童相比,杰克博士的童年不算糟糕。那时的美国没有战争,也没有经济危机,社会的暴力还不太严重。父母不必时刻担心孩子会被坏人拐骗。身为孩子,可以以一种比较自然的方式慢慢长大,无需思考,也不用太努力,大街小巷可以自由来去。父母组织孩子的生活,学校教育是免费的。人们没有手机,有什么话面对面地说。
在他看来,今天的儿童,至少美国儿童,生活在一种近乎残酷的高压之下。父母、学校和媒体都在催着他们快快长大。那些在自己的工作中承受过多压力挫折的家长,很容易把自己的焦虑转移到孩子身上,强迫他们从越来越小的年纪开始,就在学业与各种比赛中获得成功。他们教孩子要赢,要比别人聪明,要比别人强大,却不教他们做人的道理。竞争的压力使儿童之间彼此疏离,以自我为中心,导致了许多心理问题的产生。
“这是社会强加给孩子的压力。”杰克博士说,“这种压力背后隐藏着一个可怕的资本主义逻辑:父母在子女身上投资时间和金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他们能用一个好价钱把自己卖给这个社会。”
“欧洲社会好一点,他们有社会保障系统,如果没有工作,你至少还能活下去。但美国是一个非常野蛮的资本主义社会,遵循赤裸裸的剥削法则。媒体制造幻象,告诉你一切都很好,糟糕的教育制度、腐败的政客,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这些是可以接受的呢?”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对杰克博士的一生影响极大。“二战”流亡期间,布洛赫写过三卷《希望的原理》。他认为,对乌托邦的向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首要驱动力。只要还活着,我们就向往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能让人有尊严地活着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幸福,但一定要相信幸福是可能的。
在布洛赫看来,所有的艺术,无论高雅低俗,都包含了希望的图像和指向创造乌托邦的方法。他还特别提到了童话。童话里充满了小人物的冒险故事,比如杰克与豆子,主人公通过努力,通常得到外界,比如动物们的帮助,克服种种障碍,最终战胜邪恶的国王或巨人。这些故事都在告诉我们,悲惨的遭遇可以被改变,邪恶可以被战胜,被压迫的人是有希望的,而希望是掌握在与我们一样的小人物手中。
我们在杰克的故事里投射自己的梦想、欲望、野心和经验。他的冒险从最平常的地方开始,回归到日常生活。它不仅反映我们的挣扎,也揭示了重建生活模式和社会关系的可能性。■ 乌托邦杰克博士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