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是一个器件
作者:薛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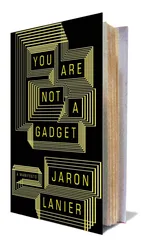 ( 杰伦·拉尼尔和他的作品《你不是一个器件》 )
( 杰伦·拉尼尔和他的作品《你不是一个器件》 )
群体智慧的限度
《时代》周刊评论说,李光耀有影响是因为他使新加坡的人均年收入从400美元增长至现在的近4万美元;乔布斯有影响是因为他开发了很多大受欢迎的产品;拉尼尔有影响是因为他出了一本书,从互联网革命的推动者变成了它的责难者。“49岁的拉尼尔是很多角色——作曲家、表演家、计算机科学家、哲学家——但他不是机器。他今年出版的《你不是一个器件》推动读者重新看待人类在社交网络世界互动的力量及其限度。
“在80年代,拉尼尔在虚拟现实方面的先驱性工作重新塑造了人们关于感应界面如何实现人类与电脑互动的概念。他在新书中提出,对网络的滥用会压制个人的声音。拉尼尔希望人们用21世纪的技术表达我们的本性,而不是消失在其中。”
《时代》百人榜的评选过程也肯定了拉尼尔的观点,他们的评选除了“网民投票”这一筛选依据,更重要的是“编辑选择”。
拉尼尔的论敌是群体智慧的拥护者。《纽约客》商业栏目的专职作者詹姆斯·索诺维尔基2005年出版了《群体的智慧》一书。1926年,门肯曾写下这样一句不朽的名言:“据我所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因低估群体智慧而蒙受损失。”索诺维尔基认为,门肯这个巴尔的摩的圣贤显然错了,“在一个大群体中,尽管有很多人知识匮乏,甚至目不识丁,但他们的群体智慧仍然会胜过那些少数精英”。虽然每个个体都不知道某个问题的答案,但答案其实已经包含在了群体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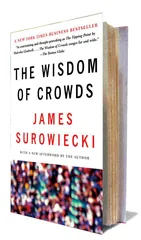 ( 詹姆斯·索诺维尔基和他的作品《群体的智慧》 )
( 詹姆斯·索诺维尔基和他的作品《群体的智慧》 )
他引证了《蜂群的智慧》一书的内容,该书作者托马斯·西里指出,一群蜜蜂可以搜寻距离蜂房6公里的范围。蜂群寻找食物时应用的是群体智慧,蜜蜂不是聚在一起讨论该前往什么方向去寻找食物,而是派出一些侦查蜂飞往不同的方向,相信总有一只侦查蜂会找到花蜜源。
拉尼尔说,群体智慧只有在选择很简单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他说:“拍卖可以决定一辆汽车的价格,因为答案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但如果同样的一群人试着去为市场设计一辆理想的汽车,没人会对结果感到满意。欣赏创造性的表达、反省,提出困难的问题,给出创造性的想法——不只是一个工具,这些都很困难。”
数字极权主义者认为智慧来自大众,而不是杰出的个人。这一思维的基础是混沌理论或复杂性理论,这一理论始于一个跟蚂蚁有关的问题:不会说话的蚂蚁之间的互动何以能产生一个复杂的群体?“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对研究交通拥堵等群体现象的人来说非常管用,但把从蚂蚁那儿引申出来的理论用于具有创造性的、能够表达的生命时就会带来问题。”
在整体主义者的模型中,算法在系统中的很多参与者之间制造连接,由此创造出知识,从这种无限的连接中会产生智能。创造者不再是人类,而是系统及其算法,从中产生一种有生命的、非人类的更高等的存在。有人相信,互联网不久将获得生命,“可怜的人类参与者成了为技术地主(谷歌、雅虎和拥有大量分析性资源的避险基金)干活的农奴,地主从自愿的劳工那儿获得利润。我们的作用只是不断地贡献我们的字节、文字片段和个人主页。我们成了计算机的外围设备”。
索诺维尔基承认,群体智慧的实现需要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比如群体中的个体要独立做出各自的判断,不受别人的影响。而在网络社会,不受别人的影响几乎不可能。
新的数字人道主义
拉尼尔的书的第一句话是:“现在是21世纪初,这意味着读到这些字的人大部分是非人——不动脑子机械行事的人或麻木的群氓,它们由不再作为个体行动的人组成。”
拉尼尔主要关心的是网络从业者对在线集体活动和群体智慧的信念。他认为,维基百科、美国偶像、谷歌和Facebook中包含的集体精神降低了个人声音的重要性和独特性,蜂群大脑将导致群氓的统治。“网络文化越来越像一个贫民窟。贫民窟比富人区有更多的广告。在贫民窟由群氓统治。”他的例证包括Facebook降低朋友的含义;很多投资公司和银行使用的基于网络的算法减少了关于金融和投资的聪明、分析性的思考。
拉尼尔提出,网络上最流行的东西,包括维基百科、Facebook和数码音乐,对人性异常有害,它们使年轻人降低对人能成为什么的期望。社交网络把人从复杂的东西缩减为各种类别,把用户交给蜂群心灵的意志。“最积极的Facebook用户要管理别人随随便便留下的评论,在网络上蒙受屈辱的Facebook一代没办法摆脱,因为只存在一个蜂群。”
网络偏爱群体而非个人,维基百科那样的群体作为受到表彰,哪怕它们去除了个性和视角。没有归属的信息因为被剥离了背景而被去除了人性。
网络用户不仅消费信息而且普遍地生产信息,这导致一些人认为,网络作为整体将获得生命,变成一个超人类的生物。根据这种信念做出的设计遮住了人的光彩。计算机不久将变得如此庞大和高速,人将变得过时。“微软的一位朋友曾经说,他们在为文字处理程序设计一些功能,它们知道用户想做什么。这些功能不是为了让你的工作变得更容易,而是在推广一种新的哲学:电脑正在进化成一种生命形式,它对人类的理解超过人类对自己的理解。”
“人们一直为了让机器显得聪明而贬低自己。在2008年股市崩溃前,银行家们认为聪明的算法可以计算信用风险,网络上充斥的用户生成的内容被认为将形成一个蜂群大脑,一种新的超级智能。”
拉尼尔认为,我们的心灵正在受到网络工具的奴役,这些工具正在训练我们以反人性的方式思考。他指出,大部分当今的网络工具都迫使我们进入异常有限的盒子。90年代第一代手工制作的网站虽然很简朴,但非常有创意,自由地表现自己,今天的网页非常华丽,但它们把人的个性缩减为一套要点。拉尼尔说:“我担心我们开始按照数字模型来设计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同情心和人性会被过滤掉。”拉尼尔关心的是,软件设计者会做出短视或受利益驱动的决定。我们也许日后会意识到这些工具限制了我们表达自我的能力,但那时为时已晚,因为那些设计已经定型,别的软件也是围绕着它们而设计的。
如克里夫·汤普森拉所说,尼尔对网络生活的批判指向的是网络造成的人们的虚假意识。他认为,人们受到软件的囚禁,他们已经变得异常愚蠢,意识不到他们的状况有多贫瘠,Facebook就是柏拉图描绘的洞穴的高科技翻版。软件确实会影响我们的行为,10年前劳伦斯·莱斯格就用“代码即法则”表达了这一意思。很多人注意到,Twitter和Facebook的不同设计会导致不同的行为。因为Twitter的大部分账户是公开的,谁都可以看到,而Facebook的账户默认的状态是隐藏的,所以社交网站的用户往往用Twitter来打造自己的职业声望,而把自己的生活照放在Facebook上。
克里夫·汤普森认为,拉尼尔过于悲观,“同样真实的是,用户不是那么容易被控制的”。实际上,技术的历史充满着这样的故事:人们以并非设计者的原意或设计者根本没想到的方式使用软件。短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12个按键的手机本来不是为了发送文字而设计的。用手机发短信非常不便,打出一个非常常见的字母需要按4次键。无线网络也不是为短信而设计的,运营商只搭建了一个很小的后台数据频道供人们打电话。所以当他们决定允许用这个频道发短信时,它每次只能传送160个字。但结果表明,消费者喜欢短信的便宜和方便,运营商也愿意利用这一新的收入来源。由于这种形式的字数限制,人们突然发现他们又开始在日常会话中使用古老的文字形式。
厌恶或害怕技术的人总是谴责技术革命导致个人或道德的腐化——书籍、报纸、广播,然后是电视,都曾招致类似的批评。拉尼尔是一个数字世界的业内人士,他希望软件工程师能采纳一种新的数字人道主义。“技术派把他们受到的批判归结为习惯性的道德批判都是胡扯,都是为了让非技术人员自愧不如。我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我发明的。我要说的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要发明一个新世界,然后拒绝相信它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做出的刚开始就是完美的,我们就是白痴。”■(文 / 薛巍) 不是一个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