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梦巴黎》和“后60年代”的世界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 《戏梦巴黎》电影剧照 )
( 《戏梦巴黎》电影剧照 )
《戏梦巴黎》近日由译文出版社重装出版。英国作家吉尔伯特·阿代尔的这部处女作最初出版于1988年。在文笔和结构上,阿代尔不算是一个很合格的小说家,但是他有故事,而且塑造的人物性格鲜明——生活在巴黎20世纪60年代末的文艺青年,对话也写得很独特,所以小说出版后,找他购买电影改编权的导演一直不断。
小说描写1968年,在巴黎进修法语的美国青年马修在电影资料馆结识了一对孪生兄妹——泰奥和伊莎贝尔,他们是一个桂冠诗人的孩子。伊莎贝尔从来只穿祖母留下的40年代款式的香奈儿时装,成为巴黎街头的一道风景。兄妹俩的父母去海滨度假,马修被邀请搬进他们家位于左岸知识分子气息浓厚的公寓,3个人过起了一种无论精神还是身体上都很乌托邦的生活,而窗外不时传来口号声。“红五月”以一种属于“乳臭未干”的青少年非常个人化的观察出现在小说背景中。
小说出版后,对于电影改编权,吉尔伯特·阿代尔一直不松口,直到有一天来找他的是意大利导演伯纳多·贝尔托鲁奇。贝尔托鲁奇邀请阿代尔做电影的编剧,2003年,他跟着导演和3位主要演员一起在巴黎经历了整个拍摄过程。由于对小说的初版感到不满意,每天傍晚从片场回来,他就开始改写原小说。“我吸收了电影中的一些想法,但小说和电影还是有很多不同,他们应该算是双胞胎,各有各的独立意识。”阿代尔对本刊记者说。经过作者改写的小说出版于2004年,从原名《神圣的纯真者》(The holy innocents)改成了和电影片名一致的《梦想家》(The dreamers),也就是这本将在中国面市的《戏梦巴黎》。
三联生活周刊:书名为什么改叫《梦想家》?
阿代尔:舍弃原书名的动力来自贝尔托鲁奇,他和我后来一样不喜欢它。在60年代,法国的年轻人被视为乳臭未干的小孩,既不性感也不勇敢,没人严肃地对待他们的观念和理想。只是从60年代以后,世界开始聆听年轻人的声音,现在的年轻人比60年代的有权力多了。在“红五月”运动发生前,我可以向你保证绝对不是这样,年轻人就好像在茧壳里,真的是没有人搭理他们,他们必须等待。像书中的3个主人公,他们天真,同时也很胆小,不愿涉足社会。他们在公寓里与世隔绝的生活在别人看来像一个梦,而参与革命的愿望,对他们来说也像是一个梦。
 ( 吉尔伯特·阿代尔 )
( 吉尔伯特·阿代尔 )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小说中尝试写3个年轻人最大可能的身体解放,然而相比小说,电影做了更保守的处理。是因为审查制度吗?
阿代尔:有一天,艾娃·格林(伊莎贝尔的主演)来见我。她说,我认为,伊莎贝尔应该是处女。我说不不不,剧本不是这样的。她说,剧本错了,我比你更了解伊莎贝尔,我认为,她这个时候应该是处女。我和伯纳多聊,他说,艾娃和这个角色相处了几个月,这可能使得她对角色理解更正确。原作是关于身体解放和思想解放的,原作中马修和泰奥也有性关系,但是两个演员都觉得这很不舒服,我们并不想强迫他们那样去演,因为这也是一种选择的自由,所以电影里只出现了一点暧昧的暗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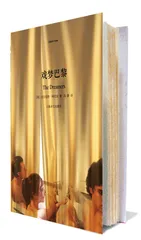 ( 他的作品《戏梦巴黎》 )
( 他的作品《戏梦巴黎》 )
三联生活周刊:父亲对当时发生的事情置若罔闻,他说“我只是个写诗的”。泰奥指责他父亲不在反对“越战”的请愿书上签字,说:“一份请愿就是一首诗。”这应该怎么理解?
阿代尔:1960年的巴黎基本是一个标语的年代。而当时那些标语,如我书中所列——“路面下是海滩”;“快跑,同志,旧世界就在你身后”;“社会是朵食人花”——本身就很有诗性,它给人带来语言节奏上的快感。父亲年轻时被认为是更有革命性些,但是他已经忘记了,甚至走到极端保守的一面。20世纪40年代他那样的知识分子是社会意见的积极参与者,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已显得迂腐。在他的儿子泰奥看来,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小说中涉及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知识分子是安德烈·马尔罗。他在20世纪30年代是左翼分子,他的小说《人类的境况》讲中国共产党的革命,30年代他去西班牙参加西班牙内战,“二战”期间,他领导几支游击队解放阿尔萨斯,是法国的英雄。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他作为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年轻人走上街头反对他。我希望小说让读者注意到人的这种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如何回望1968年呢?
阿代尔:1968年我22岁,在巴黎做了3个星期“毛主义者”。我们当时相信世界马上会改变,但它并没有改变。很多评论家说1968年的事就是一场嬉戏,没有冒生命危险就没有意义。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它成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始、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开始、保护地球和环境运动的开始,整个西方教育系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和贝尔托鲁奇聊,他认为此后几十年,我们一直生活在“后60年代”的世界,直到2001年9月11日。世界秩序发生变化,带给人们更多的是恐惧和希望的破灭。新元素不断出现,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但是,现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后60年代”的世界,因为60年代的影响并没有消退,比如它带来的个人解放。
三联生活周刊:一直很好奇,当年巴黎青年从哪里弄到“红宝书”呢?
阿代尔:有一个书店,我在书中提到过(注:圣塞弗兰大街的马斯佩罗书店)。我们去那里买毛主席语录和胸章。那书店一进门是3幅丝网肖像:毛泽东,格瓦拉和胡志明。《资本论》是当时年轻人的圣经,我们以为在那里可以找到世界为什么以及将要如何改变的答案。不过我们通常不在那里买书,而是消磨一天,看看各色志同道合的青年,或者说更像一个咖啡馆,我们拿走想看的书,不是偷,以后有钱就还回来,如果还能弄到钱的话。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作家总是对两男一女的情感主题着迷?而且这样的电影往往成为文艺经典?贝尔托鲁奇1976年拍的《1900》,还有你在小说里提到的戈达尔电影《法外之徒》,特吕弗的《儒尔与吉姆》也是讲这种三角关系的。
阿代尔:抛开个人的感受不谈,3个人的组合具有非常大的戏剧张力,在银幕上造成一种奇妙的视觉平衡。3人之间总是会产生一种微妙的、敏感的、总是在变化中的情感张力,这很吸引我。兄妹俩的关系牢不可破,就像泰奥说,他们是精神相连的连体婴儿。马修的加入一开始像只宠物,但这想法更多只是兄妹俩的一厢情愿。马修有思想就能产生影响,随着马修和伊莎贝尔关系的深化,泰奥和他们的关系必然也发生微妙变化。实际上你无法在3人中建立长久的平衡,他们有争吵,争宠,妒忌,不像两性关系,也许可以持续一辈子。你无法想象一个可以持续一辈子的三角关系,这个组合最终会破裂,因为人类很难消除的嫉妒心。谁说不妒忌,就是在装,这也给了作者很多发挥的空间。我现正在写的小说,是一对年轻的日本夫妇和两个美国人的故事,日本男人是银行家,他们都生活在金融危机后的伦敦。4个人就形成更为复杂的一种结构,这也是一个数学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影迷们一直有个争论,伊莎贝尔和泰奥到底是不是连体双胞胎?电影里他们的胳膊上有一个同样的伤疤。
阿代尔:泰奥说,他们是头脑相连,是没错的。胳膊上的伤疤更多像一个徽章,至少伯纳多这样想。不是说他们的身体从那里分开,而是一种隐喻,表明他们属于同一个团体的徽章,他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分享生活里的一切。我很喜欢这个设置。
三联生活周刊:读者也经常情不自禁去猜想,如果他们成年走入社会会是怎样?
阿代尔:后来我重写了小说的结尾,让它变得更丰富一些。以前的结尾,我没说主人公是谁,我们只听到他说话,他躺在旧金山的床上看电视,不停地换频道,电视里都是在讲中东问题的。他自述他曾经返回巴黎,返回到那套老公寓,但是兄妹俩已经不再住在那里。然后他换到一个台,正在演一部他曾经在巴黎看过的好莱坞老电影,然后他意识到,他人生中真正有意思的部分已经消逝不再了。伯纳多对这个结尾没感觉,他希望有一个更伟大的结尾。所以到了电影的结尾他们返回到街上,加入游行的人群,那是我们俩当年都不曾真正参与过的事情,有一种情结在里面。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的巴黎还吸引你么?
阿代尔:不论你什么时候到巴黎,人总是会说这么一句:“现在的巴黎,和20年前可大不一样啦。”20年前这么说,20年后也这么说,就好像无论你什么时候到巴黎都只是太晚,就好像威尼斯,人们老说威尼斯快完蛋了,都不知道说了多少年了。现在我在巴黎看到到处是麦当劳,那些同样的商店Zara、阿玛尼,你可能在上海、北京也一样看到。每每看到这些,就很遗憾老巴黎的一部分消失了。■(文 / 苌苌) 年代巴黎世界戏梦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