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之初鲣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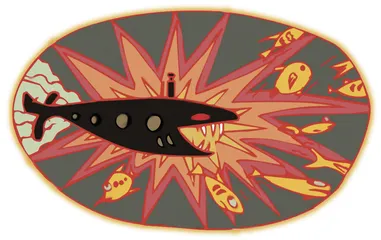
教母级美食作家费雪在她的名著《如何煮狼》中,有关鱼的一章,她用了首日本俳句做开篇:“嫩叶处处,山杜鹃啼唱,吾之初鲣!”可惜费雪撰写这本书时,正值战时,世界各大水域都是一片混乱,海鸥都没的东西吃,渔夫们也纷纷入伍,所以费雪在书中说:“所有那些晕头转向的鲱鱼、梭鱼,现时都得学会如何躲避深水炸弹,这件事光想想就让人伤心。而那位满腹渴望的小小日本人,在俳句结尾如此深情款款地描绘春日鲣鱼那第一口令人口角生津的美味,也同样令人难过啊。”
生长在和平年代就好得多,懂得吃鱼的人一般都不会错过鲣鱼这样的美味,但最近我发觉,其实吃鲣鱼的人变少了,甚至于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鲣鱼是何物。这真是辜负了当初那些日本美食家兼知识分子为鲣鱼们作的那一首首的俳句和歌谣。费雪引用的这一首,正是江户时代著名俳人、松尾芭蕉的拜把子兄弟山口素堂所撰写的关于鲣鱼的代表作。几乎每个日本人,听到这首俳句,都会流下贪恋初鲣的口水。而芭蕉的门生,室井其角也留下一首:“紫藤花开,掐指痴待,坐食初鲣日。”看看这两位,在如此迷人的春光中,不思女色,光想着吃鲣鱼,那是要何等的美味啊。而所谓的“初鲣”,便是一年中最早上市的鲣鱼。鲣鱼这种鱼类,通常太平洋随黑潮北上,抵达北海道南部时,则掉头再度折返南下,二三月份出现在九州的鲣鱼,途经高知县来到和歌山县海上时,身上还没有聚集脂肪,所以适合做成“鲣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木鱼或柴鱼。但这时的鲣鱼,生吃不够肥美,要等到其游到静冈县,绕过伊豆半岛,五月初来到神奈川的相模湾时,这才变得脂膏肥满,这时便会引得爱饕餮的江户人为了“初鲣”而一路狂奔。但在旧时,初鲣是高级无比的食物,不是凭着一腔追鱼的热情就能轻易吃到的。据古籍记载,1812年3月25日,日本桥鱼市场进了17条初鲣,将军家独占了6条,江户最高级的料亭买了3条,其余才被普通鱼贩瓜分,当时的价格是二两一分,相当于现代的27万日元,所以一般的庶民还要再耐心等等,吃不到“初初鲣”,等来比较早的第二、第三批鲣鱼也是好的。
鲣鱼的吃法大体上有生鱼片和“鲣节”两种。生鱼片里还分为高知县的“烤飞霜”和江户地区的传统生鱼片两种。“烤飞霜”也许可以翻译成“微炙”,做法是把鲣鱼生鱼片的外层连同外皮用猛火速速烤至泛白,但中间大部分保持生鲜,然后浸入醋水,蘸姜末和萝卜泥吃。鲣鱼是很特别的鱼种,跟山葵酱油不大合,一般都配合姜、蒜或萝卜泥等稍带辛辣气息的作料。在江户,传统生鱼片则是沾芥子泥味曾,味道也很特别。
而“鲣节”是更加具有传统色彩的鲣鱼吃法,很多人爱吃日本料理中的木鱼花,觉得轻舞飞扬的样子好看,跟冷豆腐、烤青椒或广岛烧之类的搭配味道也好,却不知道木鱼花便来自于鲣鱼。1704年,当时的四国土佐,即高知县,持续盛产鲣鱼,当地的渔夫便想出“干熏法”来处理过剩的鲣鱼。经过300年的技术改良,现在的制鲣节工艺已经变成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之一。制成一条优质的“本枯节”要经过复杂的生切、煮熟、拔刺、焙干、削除、长霉等环节,至少要消耗半年以上的时间。而制成的鲣节的重量只有原来那条鲣鱼的1/6,可谓凝聚了鲣鱼的完全精华。原来的日本家庭,很多都会买一整条的鲣节回家自己慢慢削着吃,但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家里藏着一条几十年的老鲣节从结婚吃到孙子出生”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少,为方便起见,很多家庭主妇都自己买小包装的“削节”来做自家料理。所谓“削节”,其实就是如今我国超市里都能常见到的柴鱼片、木鱼花,如果你对鲣节的品质不算很在乎,那削节既便宜又实用,毕竟,如果只是做些简单的家庭料理,削节是足够了。■(文 / 殳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