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纳托雷和他的电影《巴里亚》
作者:李东然(文 / 李东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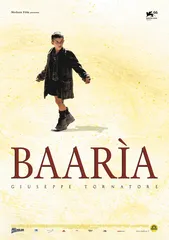 ( 《巴里亚》海报和剧照 )
( 《巴里亚》海报和剧照 )
威尼斯电影节把意大利本土电影作为开幕片的过往很少,《巴里亚》成为十分难得的“20年一遇”。不仅如此,这部耗资3000万美元的意大利巨制,也将参与2010年度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然而,导演托纳托雷(Giuseppe Tornatore)告诉本刊记者,《巴里亚》已经带给他作为意大利导演至高的满足,“在意大利的6000万人口中,迄今已经有1300万人走进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
与托纳托雷的绝大多数作品一样,故事还是开始在西西里的小镇上,几代人的故事在男主人公贝比诺的成长和老去中展开。旧时的小镇生活自然粗粝,“羊的过错”(羊吃了书)让贝比诺终其一生没能读完小学。可贝比诺想要改变世界,虽然理想总是如吉卜赛女人所预言的那样,是只破掉的鸡蛋,并且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时光也要在一日三餐和生儿育女中仓皇而过。但就像是孩子生来就乐于奔跑一样,因追逐而产生的生命愉悦本不需要结果。除了贝比诺,你也会记住一张张执拗的脸,托纳托雷毫不回避小镇生活的荒诞和狭隘,甚至不失时机地开着那些人的玩笑,会心笑过才发现,原始真挚的内心却如此富有力量。
对于意大利的观众,《巴里亚》有着超越电影本身的意义。“《巴里亚》是如同壁画一般,跨越了很长时间,是史诗性作品。它不但呈现了意大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之后经历过的种种历史命运,还可以看到意大利发生的那些政治变动,那些曾经的时代人物,包括法西斯、共产党、基督教民主党、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各种政治风潮交替出现,大小历史事件数不胜数。其中虽然只讲了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但故事背后的信息量巨大,最可贵的是导演把故事编排得错落有致,浑然天成,不纠结于事件本身,却把最深沉的情感倾注其中,这是伟大的民族的电影。”意大利资深的影评人、威尼斯电影节的选片负责人恩里克·马格莱利(Enrico Magrelli)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然而,在北京这为期4天的展映中,每一场《巴里亚》的放映,都会有观众站着看完了两个半小时的电影。“这部电影和《天堂电影院》有很多相互关联的地方,你能在电影里找到很多互动的元素。这两部电影就像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但《巴利亚》对我个人来说,是迄今最艰巨的一部作品,也是我所有电影中最个人化的作品。虽然这部电影的具体创作过程只有3年,但实际上我所考虑这部电影的时间甚至早于《天堂电影院》的拍摄,所以《巴里亚》也绝对不是《天堂电影院》中未达成心愿、没说尽的话语,而是这两部电影构成了完整的存在。《巴里亚》就像是一个人,而《天堂电影院》是人的肋骨,只不过《天堂电影院》对于曾经只有30多岁的我来说,是更加容易讲述和把握的,所以能更早地把它拍摄出来。”
托纳托雷坦言,《巴里亚》的开始也源于他那解不开的西西里魔咒,事实上,在漫长的构思过程中,他所关注,但始终无法逾越的,都是如何去阐述一个人的存在和他出生地之间的那种关联。“我的每一部电影都需要很长时间的构思,具体到《巴里亚》尤其是这样。实际上,我始终想去拍摄这样一部电影,这也许算是对‘西西里魔咒’的自我解读。很多年过去,最终我找到这样一种方法,那就是讲述这个小地方一个世纪的故事,随着年龄增长,你会更加看重那种历史性时间的积累,会更多地去在历史中找寻答案的所在。”

《巴里亚》和托纳托雷导演的其他作品一样,拒绝任何小说基础,从故事主线到细枝末节,靠的是用时间和耐心一点点打磨而来,托纳托雷告诉本刊记者:“我完全记不得这个故事诞生的起点在哪里,我总觉得所有故事都是本来就在我的头脑中一样,始终都有这么一个想法,之后就是在漫长的时间里,本能地去收集各种资料,充实它,打磨它。也不知道哪一天能拍出这种想法,甚至是需要外界的驱动才能办到,比如这部《巴里亚》中就有制片人投入的热情成为我的动力,我很感激他们。”
“整个故事的基础,这一个世纪的时光是飞逝而过的,虽然这个作品的故事本身是现实主义的,但是我讲故事的形式是充满想象的,我倾向于童话般的、幻想的、田园诗般的讲故事手法。”
 ( 导演托纳托雷
)
( 导演托纳托雷
)
托纳托雷没有太多的个人的故事,他也笑言因为把一切都拍进了电影,自己是个生活无趣的人。托纳托雷把自己的人生总结成简简单单的4个字——相信理想,“就像是《巴里亚》的结尾,压在陀螺中的那只苍蝇,最后也振翅高飞,对我来说,这只苍蝇负载着很多的含义,尤其是理想,是希望,生活再艰难,有理想的人永远有希望,对我来说,杯子永远是半满的,而不是半空的”。■
专访朱塞佩·托纳托雷
三联生活周刊:巴赞在自己的书中,曾给予了意大利现实主义以“真实美学”的高度评价。作为意大利导演,你怎么看待意大利电影中的现实主义特征,以及这个电影传统在今天的传承?
托纳托雷:意大利的现实主义由最初的纪实美学发展到今天,其实已经很难说清楚这个词的含义。像罗西里尼那样几乎完全书写现实的真实,是现实主义的一条脉络,当然有很多类似风格的导演,或者说继承者,比如德西卡、维斯康蒂。但是,你也可以说费里尼、安东尼奥尼也都是现实主义的,他们呈现的现实主义却又是截然不同。我坚信的是,现实主义确实是我们意大利电影的特征之一。
意大利电影的现实主义在新一代导演身上或多或少有一些传承,但是传承的程度并没有想象中充分,因为新一代导演受到好莱坞的叙事手法、欧洲其他国家的电影表现手段,以及网络、电视等现代传媒的影响,不会固守传统、按部就班地进行创作。其实,他们也理应创作得更加自由,不该受到所谓传统的束缚。
三联生活周刊:在中国艺术电影观众中,费里尼备受推崇,他的现实主义和你的新片《巴里亚》给人的感受非常相近,并且《巴里亚》里,甚至找得到费里尼电影的片段。
托纳托雷:如果你说这部电影带着费里尼电影的影子,我也欣然接受。毫无疑问,在我的电影生涯中,费里尼是教会我很多的意大利导演前辈。因此我本能地会把费里尼的片段放进这部对自己意义重大的电影中,这是对大师的问候,也是与影迷的秘语。大师的作品、风格对我而言的意义绝对不是用来戏仿,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让我爱上了电影,放飞和成就了梦想。但是费里尼不是唯一使我爱上电影的那个导演,让我爱上电影的导演很多很多,甚至不止是意大利的导演。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作品总是围绕着西西里故乡展开,出于对故乡的思念么?能不能解释这种情感?
托纳托雷:我把用电影表现西西里更多呈现为一种西西里情节,而不是思乡。我觉得我至今的作品中,带着纯粹思乡情感的电影只有一部,就是《天堂电影院》,其余电影都绝对不是思乡,是我对于故乡的情结,是我逃脱不开的魔咒,或者这是我个人的现实主义所在。
三联生活周刊:你并不是一位多产的导演,虽然《天堂电影院》的成功就已经让你收获了足以进入好莱坞工业体系的声誉,但是你始终在自己的国家拍片,并且坚持从编剧到剪辑全部独立完成的创作方式。在这个时代,你会不会担心自己坚守的传统作者电影的未来?
托纳托雷:向着好莱坞和商业片靠拢的趋势,已经不是近几年或者几十年出现的状况。实际上,纵观电影史发展过程,每一部电影的诞生过程,实际上都是一场导演和制片人之间的战斗。实际上,我觉得,真正可以去改写电影历史的还是电影本身的技术革命,近年来诞生的数字技术毫无疑问为电影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实际上我更倾向于认为数字技术会给电影带来的新格局,电影可以接近更多的人,人们可以相对容易地拍摄自己所喜爱的电影,这种情况会带给作品最大的自由度。我确实不是很关心它们是不是会把个人化的、作者化的传统电影方式毁掉,我不关心这个问题,我只拍自己喜欢的电影,只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拍电影,哪怕是机会越来越少也没有关系。只要有电影制片人愿意找我拍电影,给我钱拍电影,那我就按自己的方式做好了,如果真的有一天不能留给我这样拍电影的机会,我就换一个职业,或者拍自己的数字电影好了。■ 费里尼影视托雷巴里托纳天堂电影院电影剧情片法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