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的解剖
作者:薛巍(文 / 薛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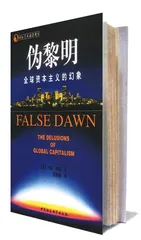
进步的幻想
格雷在书中推翻了认为我们已经到达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世俗自由主义的教条,指出了赌场资本主义的弱点和能源密集型经济增长的限度,之前,格雷从一个拥护撒切尔革命的人变成了全球化最凶狠的批评者。1984年他写了《哈耶克论自由》一书,赞颂这位自由市场的圣人,1998年他又写了《伪黎明》,讲述一些人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他从华盛顿右翼智库的常客变成了左翼媒体《卫报》和《新政治家》的作者。《稻草狗》一书表明格雷的又一次转向,这一次他转向了深层生态学。劳烦他的不再是自由市场或全球化,而是人类本身。“对自然界的破坏不是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西方文明或人类体制的任何缺陷,而是一种贪婪的灵长类动物成功地进化的结果。”但所有转变都只是表面现象。格雷始终如一地坚持他的悲观主义:我们对进步的信念是虚幻的,如同我们对人类独特性和掌握我们命运的能力的信念。
在1998年出版的《伪黎明》一书中,约翰·格雷预测,全球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会非常短命。全球化的鼓吹者没有看到,金融市场天生反复无常、容易发生周期性的震荡。格雷对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理想的批评更加思辨、深入地批判乌托邦或进步观念本身,他把所有的错误都追溯到启蒙。假定美国式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将扩展到全球,这是普遍文明的启蒙工程的最终版本。全球自由市场跟潘恩、密尔等启蒙思想家的共同点是,相信世界都将采取西方的体制。
新自由主义不只错在假定自由市场能够自我调节,面对来自东亚的不同经济模式,仍坚持认为唯一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适用于一切情形。格雷说,他一直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不是通用的。他一直对亚洲的模式很感兴趣,尤其是在新加坡和日本(他妻子是日本人)那里,市场嵌入体制和生活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的情形。
在《基地组织和现代意味着什么》一书中,格雷认为,当代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不是现代自由民主和反现代之间的冲突,他不认为现代化意味着解放和幸福。“新自由主义希望全球化将使世界遍布自由主义的共和国,通过和平和贸易相连,但历史充满战争、独裁和帝国。”格雷说,基地组织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组织,说它现代不仅是说它使用卫星电话、笔记本电脑和加密网站,而且把在媒体上发布图像作为核心战略。但这些都只是对技术的欣赏,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亲近,基地组织使用现代技术,追求却是反现代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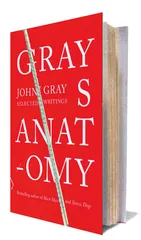
格雷说,即使基地组织一些前现代的特征,也使得该组织能够在现代条件下有效地运作。其非正式的银行系统遍布全球,且很难被追踪,拥有蜂窝状毒品卡特尔和扁平型公司网络,基地组织没有抗拒全球化,而是利用了全球化。
在拒斥了现代和反现代的认识方式之后,格雷认为,当今的全球性冲突本质上是人口增长,能源供应减少和气候变化,种族和宗教仇恨,很多政府的解体或腐败。格雷拒斥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是因为他认为,本质上人类之间有差异。格雷批评自由主义者没有看到各种文化之间基本的、不可改变的差别,他跟亨廷顿一样认为,各种文明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他说:“我们能不能接受人类拥有分歧和互相冲突的价值,学会适应这种事实?”格雷正确地认为,世界上大部分人不想采纳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但他走得太远,把这变成了对普遍主义的反驳,人类虽然有着地理、文化和宗教上的差别,但有着很多共同的价值观。
 ( 约翰·格雷认为,地球人口越来越多,只有科技才能拯救人类 )
( 约翰·格雷认为,地球人口越来越多,只有科技才能拯救人类 )
格雷知道,他的分析中最不能令人接受的是对社会向善论的批判,社会向善论认为,道德和政治上的变化能像科学上的进步一样不可逆转。过去几百年间,人类的能力和知识取得了显著增长,但不能以为,因为知识增长了,人类就不会那么容易变得怯懦、残忍。奴隶制在19世纪被取消,但现在仍有数百万人被奴役,不仅道德和政治上的进步是虚构的,而且试图使世界变得更好只会导致屠杀和人类精神的腐败。
格雷反对进步观念的问题在于,除非人们相信能够改变世界,否则很难知道奴隶制是怎样被取消的,或虐囚是否是非法的。确实,今天仍有人被奴役和殴打,但我们对奴隶制的憎恨和对美国虐囚行为的谴责,本身就是道德进步的表现。盲目地接受乌托邦观念会败坏人心,但盲目地拒斥乌托邦理想也一样会败坏人心。
 ( 约翰·格雷(上图)与他的作品《格雷的解剖》和《伪黎明》 )
( 约翰·格雷(上图)与他的作品《格雷的解剖》和《伪黎明》 )
他认为,我们和动物之间没多大区别,但他自己的道德感和对各种暴行的强烈谴责违背了这种观点。如伊格尔顿所说:“格雷可以强烈地批评屠杀,但我们还没遇到能这样做的一只长颈鹿。”意思是,格雷说得很聪明,但有点不着边际。首先,即使长颈鹿能够说话,它们要谴责的也是人类的行为,或狮子的行为,而不是长颈鹿的行为。其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动物,至少是高等动物,确实有道德感。
反讽自由主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虚构的解构》一文中,格雷戏仿马克思主义研究语言学的方法,虚构了维特根斯特访问苏联,以及他与一位匈牙利学者的关系,这位学者把奴隶劳动者的咕哝声理想化为无产阶级的原初语言。更让人愉快的是,他以自由主义的方式为虐囚辩护,取笑自由主义。
2003年2月,就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几周前,格雷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一个温和的建议:关于在自由民主国家防止酷刑被滥用及认识到它们对公众的好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对斯威夫特的模仿。1729年,面对爱尔兰普遍的贫困,有人建议准许法国来募兵,有人建议移民到澳大利亚为仆,愤怒的斯威夫特则以反语建议把儿童养肥,作为富贵人家的美味佳肴。格雷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多人没有看出这是一篇讽刺之作,要么是《新政治家》的读者没有幽默感,要么是他们不愿意认为这是讽刺。
他写道:“将虐囚从地下室带到光天化日之下,需要对法律加以现代化,但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们需要革新我们对人权的认识。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援引当代自由主义哲学的最先进的思考——罗尔斯的《正义论》。该书的核心特征是,认为基本的自由不会冲突。对霍布斯和密尔等欧洲思想家来说,一种自由会和另一种自由冲突,甚至一个人的一种自由也会跟别人的这种自由冲突。言论自由跟不受诽谤的自由冲突,一个人的结社自由(比如只接受白人的俱乐部)是对另一个的歧视。霍布斯和密尔认为,这些是我们无法彻底解决的冲突,我们最多能达成妥协,使各种主张保持平衡。
“美国的自由主义哲学拒绝这种令人厌烦、没有指望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的所有自由属于一个单一、统一的体系。当它们被恰当地指定出来时,即正确地加以定义使之不会互相冲突,人权就不会冲突。因而,当言论自由跟不受诽谤的自由冲突时,后者就不是真正的自由。这种观点跟虐囚的关系非常明显——我们不应该认为,恐怖分子遭到虐待是违反了人权。罗尔斯等人表明,基本的自由必须形成一个融洽的整体,因而一旦采取了合法的程序,虐待恐怖分子就不会违反人权。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恐怖分子有权被虐待,这显示了自由社会相对其他社会的道德优越性。别的社会通过把恐怖分子交给不受法律约束、不负责任的权力,降低了他们的身份。在新世界,虽然恐怖分子通过推行恐怖主义而自降身价,但他们也会在法律过程中保持全部的尊严,哪怕被虐待。我们可以期望有一天人人都拥有这种权利。……忘记受审者的需要是错误的,他们将需要经常做心理咨询以克服受到的创伤,必须使他们把自己看成为了进步事业而献身的人。”
从密尔的角度正面反对虐囚的论证可以是:不允许虐囚可能间接侵害到社会其他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允许虐囚则直接侵害了当事人的基本权利,直接侵害的恶果大于间接侵害的恶果。犯罪嫌疑人对他人权利的侵害是个人行为,国家机关对犯人的拷打是国家行为,而国家的行为能力远远大于个人的行为能力。■ 政治解剖格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