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音乐的苏格拉底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寇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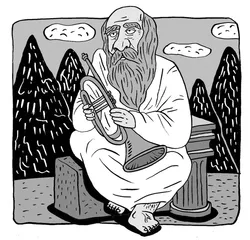
尼采一辈子都是个愤青,被他诋毁过的人和事一抓一大把。比如他对教养的“定义”:所谓教养,就“在于不让人看出自己多么卑鄙、下作,不让人看到自己在竞争中多么如狼似虎,在聚敛中多么贪得无厌,在享乐中又是多么自私和无耻”。拐弯抹角,把有教养的和没教养的全骂了。
被尼采骂得最著名的大人物,怕是苏格拉底了,他指斥其为“魔鬼”。尼采认为,苏格拉底应对希腊悲剧的消亡负主要责任。在尼采看来,希腊悲剧是顶尖的艺术消遣,当俄狄浦斯在神话里受苦,苦命人尼采也感同身受,其被震撼的程度,不亚于家庭主妇看韩剧。不过浅薄如我辈,只会哭得稀里哗啦,哭过即忘;深刻如尼采,悲痛过后,还会化悲痛为美学。我想这句台词正合他的胃口:“智慧之矛调转矛头刺向智者,智慧是对自然的犯罪。”这话慰藉尼采的悲苦人生,也恭维了他的智商。
希腊悲剧消亡了,尼采痛心疾首,经过紧锣密鼓的搜捕,他挖出元凶: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他写了有史以来最让法官头疼的诉状:《悲剧的诞生》,条分缕析苏格拉底的罪责。苏格拉底是个下里巴人的老夫子,不懂艺术,没音乐细胞,不是盘腿坐在炕头跟学生讲道理,就是到广场拦住行人讲道理。讲着,讲着,苏格拉底这支长了一对肿泡眼的消防栓,灭了希腊人的激情,逐渐便没人去讨论俄狄浦斯的恋母情结了。
为扳倒苏格拉底,尼采做了两件事。一是离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师生关系,他说柏拉图本来和他一样是个挺有艺术修养的热血青年,不幸遇到苏格拉底这个老古董。柏拉图为讨师傅欢心,硬生生压制自己的天赋,写作《对话录》时,艰难地在诗歌与辩证哲学中寻找平衡,却以诗歌让位于逻辑告终。
第二招,是再讲一遍“苏格拉底最后的梦”的故事。苏格拉底赴死前,在监狱常做一个梦,梦里有个声音劝他改行:“苏格拉底,搞音乐吧!”这个声音反复出现,扰得他不得安宁,或许蹲大狱确实无聊,又没人辩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苏格拉底有些松动了。他尝试做音乐,最后还写了“阿波罗颂歌和几首小诗”。是不是《悲剧的诞生》中的杜撰,也未可知。就算尼采给了自己一片阿司匹林吧。
不喜欢讲道理的尼采,其生命结束的方式也不着调。1889年,尼采在街头抱住一匹马,大呼:“我的兄弟!”就此崩溃。在随即出现的幻象里,他认为自己是酒神、耶稣、拿破仑、恺撒……他是否认为自己是“魔鬼”苏格拉底?并非没这个可能,他口出狂言“上帝死了”,但也认为自己是耶稣。这位不幸的“愤青”哲学家,生命中最后11年,无知无觉,不讲道理,也不讲艺术,倒落得清净。■ 苏格拉底艺术音乐尼采哲学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