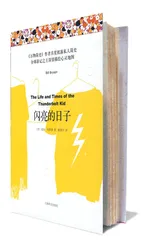布莱森的“美国派清口”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苌苌)
 ( 比尔·布莱森(左)和他的作品《闪亮的日子》(中)与《“小不列颠”札记》 )
( 比尔·布莱森(左)和他的作品《闪亮的日子》(中)与《“小不列颠”札记》 )
读比尔·布莱森的书经常令人捧腹,他的幽默很明显继承了两种风格:英国式的板着脸孔说笑话,高雅地挖苦别人;美国人的极尽夸张之能事的幽默方式。这和他早年生活阅历有关。1951年,比尔·布莱森生于美国爱荷华州的得梅因小城,这也是本书的落脚点。大学毕业后,他去欧洲游学,曾经徒步从挪威走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后来在英国定居娶妻生子,根据《“小不列颠”札记》中讲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作为左撇子,在这个开车靠左行驶的国度倍感适应。那些年他做记者、编辑主任、自由撰稿人,直到1996年,为了让他的4个孩子感受不同的文化环境,或者如他在书中讲的,当听说当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测验表明,370多万美国人都认定自己曾遭外星人劫持,他大呼一声“祖国需要我”,便携全家返回美国安居。此时,他已经被誉为是世上最风趣的旅游文学作家。刚翻译出版的《“小不列颠”札记》,是他在要离开英国那年写的,他形容为就像是长跑比赛的冠军到达终点后,向观众致敬跑的那一圈。之后在《人在故乡为异客》中,他记录了刚返回美国时的感受。而令他获得最大商业成功的则是《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译者简单翻译成了《万物简史》,与肯·威尔伯讲灵修的《A Brief History of Everthing》中译本重名),这本从宇宙大爆炸讲到物种起源的科普读物,因为受到奥普拉的青睐而常年停留在畅销书榜单上。
《闪亮的日子》之所以有趣,可能因为比尔·布莱森的回忆也唤醒了我们对上世纪50年代以及80年代的集体记忆。他精读那时候的出版物,只看到纯粹乐观和失望的奇怪混合。美国的50年代竟也如此“跃进”:政府有人曾认真实验并考虑用火箭投递邮件,或者把氢弹用于民事工程的建设。在50年代,美国的报纸正是用这样的信息鼓舞人民。城中时不时进行“原子时代的空袭演练”,理发师领着他们刚理成阴阳头的顾客涌向防空洞。“我们不仅擅长制造真正的巨型爆炸,而且还擅长制造我们解决能力范围之外的后果。”布莱森写道,在比基尼岛上的试验,使得邻近岛上温顺的土著居民得了永久性耳聋,更别提辐射尘埃全部朝着与专家预料相反的方向飘移。此外,还有1000个核弹头在美国本土做爆炸试验,空气里都是原子的味道,1958年美国小孩身体里携带的锶90是前一年的10倍,而他们没有得到过任何政府公告,没有人肯承认这些惨败。看上去,没有荒唐,只有更荒唐。
即便是生活在战后美国GDP在10年内上升了40%的年代——从1950年的3500亿美元到10年后的5000亿美元——在大萧条时期出生的布莱森的父母,也无法克服根深蒂固的贫穷记忆。他的妈妈厨艺不精,喜欢搜集废弃的塑料包装盒,他的父亲是个优秀的体育专栏作者,专门跑全国各地去看职业棒球的训练和比赛。有一年,父亲买了一辆寒酸无比的车,带着全家穿越美国中部去迪斯尼乐园,这构成布莱森童年最快乐的记忆。新式家用电器轮番登场,每个家庭都很容易买得起。布莱森记述了刚有电视机的时候,20多个小孩挤在第一个有电视的人家的窗外看电视。他哥哥看到一个“只花65美分就可以看彩色电视”的广告,而邮购来的一块彩色透明的塑料薄片,使用说明要求他们把它贴在电视屏幕上。无独有偶,相信很多人会记得这项“技术”在80年代初的中国也有应用。“在50年代没有伤感的余地。”他写道,在文明过度发展之前,那是一段短暂的无忧无虑的时光:小汽车尚未有安全带和气囊;电影院都是很热闹的大礼堂,而不像现在隔成一个个小厅;香烟随便抽,无论在电影院还是在飞机上;食物都是好的,糖给我们能量,红肉让我们强壮,冰激凌令我们的骨头结实,而咖啡令我们清醒且高效。
比尔·布莱森的书在中国出版,陆谷孙写了总序,七八年前,他就一直向国内的翻译出版界推介比尔·布莱森的书。陆谷孙告诉本刊记者,比尔·布莱森是当今英语世界非常多产且又“最能逗乐”的游记作家之一。作为《英汉大词典》的主编,陆谷孙自然很看重布莱森对词语的把握。最初引起他注意的是比尔·布莱森的《母语》和《美国制造》,“没有经院讲章吓人的架势,而是轶事趣闻迭出,清晰又有洞见”。还有他的《烦难字解》,充分体现了作者善于解难词。陆谷孙认为,布莱森突出于共性之外的特点,应该是他强烈的环保意识。在《林中远足》中,他就对在阿巴拉契山道上,美国国家园林服务局听任林木大片被伐提出严厉抨击,也针对在美国没有汽车就无法出门的生活现实做了辛辣讽刺。布莱森的写作表面上有英式幽默的讥诮、促狭、戏谑,但背后有一个宽厚的灵魂。他写作上含有一种民主意识,不仅仅体现在文笔上。他的作品老少咸宜,还有就是他在书中努力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局面,团结犹太人、有色人种和同性恋。只有第七章是政治化的,读者会被他搜集的一条新闻吓到——仅仅不过是50年前,在阿拉巴马州,一个黑人因为抢劫1.95美元而被判处死刑。布莱森对当时肆虐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大大嘲弄了一番。不过,这样的内容仅限于一个章节,因为书中更多透过一个10岁男孩的眼睛观察世界,布莱森津津乐道,在他那个年龄的世界里,有结痂伤疤的孩子、会流鼻血的孩子如何受到崇拜。布莱森的书没有特别的深度,像一个浮光掠影的万花筒,但他提炼素材的能力和全景式的记忆力令这本书保持轻重相宜,也好在他没有把这本回忆录变成一味喟叹旧时光的多愁善感的思乡之作。在私人记忆之间,他对当时媒体报道的社会怪现状的引述,阻止了读者坠入怀旧的怅惘中。
《闪亮的日子》原名叫《“霹雳小子”的生活与时光》。“霹雳小子”来自比尔·布莱森从家中旧阁楼上找出的一件前面带有闪电标志的旧套头衫,在童年的游戏中可以赋予他“超人”的力量。在回忆到不愉快的局面时,这位作者都让“霹雳小子”跳将出来,让坏蛋人间蒸发,令人莞尔。战后“婴儿潮”的一代,吃着美国流行文化的奶长大,童年的比尔·布莱森是个超级平庸的小孩,一点也看不出来,日后的消费文化可以把他造就为一个超级畅销书作家。那时的生活风平浪静,尽管很多人相信5年内还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并不妨碍人们整装待发迎来一个物质需求将被极大满足的世界。“那时候每个地方都不一样,那就是生活在一个还没形成全球性连锁店的世界里的福分。”布莱森写道。结尾泛上来的愁绪引起我们的同感:“世界就是这样,拥有的被抛弃,生活还在继续。我常常想,我们没有把50年代那些令我们与众不同、别具一格、引人注目的东西保存下来,多么可惜。想想看,如果那些老建筑保存下来,现在会是多么不可思议。想想吧,一个与其他城市完全不同的城市,那曾是多么精彩的世界,恐怕我们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