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哲学的兴起
作者:薛巍 ( 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
)
( 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
)
从思想实验到现场实验
《哲学家杂志》说:“哲学研究的成本很低。从大学财务主管的角度,神经科学系需要一台昂贵的大脑扫描仪,化学系需要一箱箱的试管,考古学系需要一个路虎车队,相比之下,研究哲学只需要去一趟宜家,买一只扶手椅。哲学家不需要做实验,他们的论证不是从科学发现推论出来的,而是纯粹先天的。”
2007年12月9日,《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的文章《新新哲学》,他写道:“近来兴起了一个名为实验哲学的运动,大胆挑战职业哲学家对他们自己的定义。哲学家们不仅不习惯搜集数据,很多人还把他们自己定义为不愿意搜集数据的人。我们的领地是纯粹思考的天空。生物系的同事们有基因扩增仪要运行,有载玻片要染色,政治科学家有人口统计数据要分析,心理学家有他们的老鼠和迷宫。我们哲学家不观察,不做实验,不测量,也不计数。我们反思。我们只喜欢思想实验,但关键词是思想。但现在一些哲学家相信,走出去搜集关于人们的真实想法和对思想实验的回答有助于解决传统的哲学问题。”着火的扶手椅已经成了实验哲学的象征,在网上可以买到印有着火的扶手椅的T恤衫,YouTube上有一个烧掉扶手椅的视频,名为“实验哲学颂歌”。
其实历史上哲学家跟科学家曾经并无罅隙,哲学家总是非常了解科学研究、历史和心理学。20世纪之前大部分著名哲学家都综合了经验和观念研究。一些人是征引别人的研究,笛卡儿和洛克则是亲自做实验,那时科学还没有完全从哲学中分离出去。休谟除了抽象的推理之外,也运用心理学和历史观察,他的《人性论》的副标题就是“一个将实验推理方法引入道德问题的尝试”。对今天的很多哲学家来说,实验哲学这一概念却很刺耳,概念分析在过去100年间一直主导着英美哲学。他们不直接研究世界,而研究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实验哲学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哲学家设计问卷,了解人们的直觉,走到大街上去发放问卷。第二种使用新的大脑扫描技术,哲学家们跟神经学家一道,寻找人们面对哲学问题时神经活动的模式。第三种是开展现场实验,观察人们在特定的情况下的行为,通常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三种实验的目的都是质疑哲学家们已经使用了2400多年的方法,检查哲学家通过内省得出的关于人们会说什么和相信什么的假定。传统的哲学论断,“我们有这样强烈的直觉”或者“我们都赞同”现在需要接受证据的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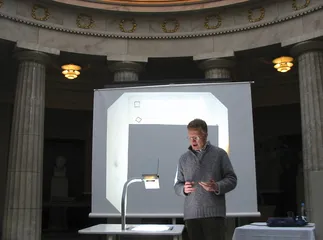 ( 牛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蒂姆斯·威廉姆森曾经在亚里士多德学会上说:“如果说有什么是能在扶手椅上得到的,那就是哲学。” )
( 牛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蒂姆斯·威廉姆森曾经在亚里士多德学会上说:“如果说有什么是能在扶手椅上得到的,那就是哲学。” )
在现场实验之前,哲学家们使用的是思想实验。这些思想实验往往从真理的案例中加以抽象,揭示出相关的道德推理。最著名的伦理学思想实验是“有轨电车难题”。你站在铁道边,看到一列电车行驶过来,刹车失灵,列车失控了,在铁道上站着5个人,他们不知自己身处险境。幸运的是,列车正驶向一个有岔道的汇合点,扳一下道岔就能使这5个人得救。这是好消息,但糟糕的是站在另一条铁轨上的一个人会被轧死。但你还是会选择扳动道岔,因为通过改变列车的行驶方向,只会死去1个人而不是5个人。
这是有轨电车难题的一个版本,现在改变一下场景。这次你是站在桥上,看到列车开过来,有5个人站在铁道上。有一个胖子站在桥边,如果你把他推下去,他会挡住列车。如果这么做,5个人得救,胖子被轧死。你该不该把他推下去?大多数人都觉得不该这么做。但从结果上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两种情况下都是轧死1个人,救下5个人。
对功利主义者来说,用1个人的生命换取5个人的生命是划算的,所以是道德的。但对康德主义者来说,人是目的,永远不能只把人当做工具,所以牺牲胖子是不对的。“这些哲学观点是否能给我们的直觉提供辩护仍然没有定论,有趣的是实验哲学家对于这一论争的处理方法。过去哲学家们假定他们的直觉跟普通人的直觉是一致的,但二者是否一致,现在很容易查验。”BBC做了一个网上调查,有6.5万人参与了这一调查。近4/5的人认为在第一种情况下应该扳道岔,只有1/4的人认为应该把胖子推下桥。但是,“没人注意到有一个链接说近1/4的英国人是胖子”。
谁害怕实验哲学?
《展望》上的文章列举了学界反对实验哲学的声音,也指出了其合理的一面。使用先进的神经观察技术解决哲学问题看起来像是重大突破,但多年来使用大脑扫描研究中风和癫痫的哲学家和医学家雷蒙德·塔利斯没这么确定。他认为大脑扫描的准确性和相关性被高估了。扫描技术在确定大脑的物理损伤方面比较准确,但当用于确定特定的思考过程发生的区域时则比较粗糙。伦敦国王学院的科学哲学教授戴维·帕皮诺说,想知道心灵、自由意志、道德价值和知识的本质,哲学家应该偶尔离开扶手椅,关注相关的发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去大街上发放问卷,他们不会从普通人那里问到什么的。
但也不能轻易否定哲学实验的意义。阿皮亚去年出版了《伦理学实验》一书,他在书中引述了一些实验,说明情境对我们的行为有多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式的美德伦理学家强调在各种情境下道德品质的一致性:一个诚实的人即使面对诱惑时也会是诚实的,一个有同情心的人在各种情况下都会是有同情心的。真是这样吗?实验表明,并非如此。在一个香气四溢的面包店外找人换零钱,就比在一个五金店外面找人换零钱的成功率更高;在电话亭里捡到硬币的人比没捡到硬币的人更愿意帮助别人捡起散落在地上的文件。
“情境对我们的行为的影响超过我们的想象。也许我们不应该像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所指示的那样,注重美德的培养,而应该让人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不相干的因素是多么容易决定我们的行为。”如阿皮亚所说:“你是否更希望人们乐于助人?结果表明,让他们遇到开心的事情比用心培养他们的美德更管用。”
如果情境对我们的影响大于我们所说的做那些事情的理由,我们事后只是用那些理由对我们的行为加以理性化,那就需要对理性主义的假定做出修订。实验哲学的这一结论让我们更加接近尼采的观点:我们以为的理性的想法只不过是对我们的内在欲望的改头换面,把它们伪装成逻辑推理的结果。
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康德的义务论,都是一个建立在一些预设基础上的论证体系。实验哲学改变了哲学的基本模样。网络杂志Slate专栏上的一篇文章说:“虽然哲学家们努力根据从世界各地的实验得出的回答提出新理论,但哲学永远也不会重获其确定性的程度。实验哲学最具革命性、最让一些人感到恐慌的是,一旦哲学朝经验科学的方法及其不可降低的不确定性开放,哲学的信条将不再是信仰的条款。哲学将不再是你相信的东西,它变成了你可以加以检验,并期盼将来加以改变的东西。”■ 兴起哲学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