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詹姆斯·伍德与时代精神
作者:薛巍(文 / 薛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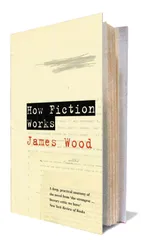 ( 《小说的原理》 )
( 《小说的原理》 )
詹姆斯·伍德神话
耶鲁大学的威廉·德雷西维茨日前在《国家》杂志上撰文说:“美国人生活中的一道铁律裁定,思想领域在集体意识中只有一位代表。就像可怜人的诺亚方舟一样,我们每一样只能带走一个。一位物理学家:斯蒂芬·金;一位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一位激进社会批评家:诺姆·乔姆斯基。在她去世前,我们有一位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仅此一位(现在我们把知识分子这个范畴一股脑摒弃了)。我们是伟大的指定者,习惯于排除对审慎的需要。我们不想权衡一种东西的利弊——衡量优点,回顾历史,进入辩论。我们只想找出一个人——明星文化的逻辑。近来文学评论的代表人物成了詹姆斯·伍德。伍德一直被认为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优秀的评论家,不只是最优秀的,还是唯一的、最后一位。”
造就伍德这一神话的一个因素是,“现代意识中与物质文明进步的信念相应的,认为文化在衰落”,所以要以伍德为基础,复兴文学批评乃至文学。伍德让人想起上世纪中期美国文学评论的辉煌年代,爱德蒙·威尔逊、特里林、卡赞和欧文·豪的年代。
2007年,伍德离开《新共和》,到了《纽约客》。伍德说,他此举是为扩大文学的影响,《新共和》的发行量只有6万册,《纽约客》的发行量是110万册。他妻子也是一位小说家,《皇帝的孩子》的作者克莱尔·梅苏德。今年伍德出版了《小说的原理》一书,此书很大程度是他自2003年起在哈佛大学授课的一个成果。
德雷西维茨首先肯定了伍德的才华:伍德学识渊博,他不仅读了所有的小说,还读了所有的信件、宣言,引用时就像他昨天刚刚看过。他读了文论、理论、美学和神学,他认为文学即真理。在娱乐的语言已经取代了文学中有道德上的严肃性的语言的时代,文学杂志《n+1》宣称,文学只是一门艺术,跟葡萄酒鉴赏一样,不值得在大学里教授。而伍德对文学超越性的忠诚和把批评当做天职是他最大的优点,他的结论是,美国评论如果追随他,只会步入一片荒漠。
 ( 詹姆斯·伍德 )
( 詹姆斯·伍德 )
伍德研究小说家如何让我们相信我们知道不真实的东西,如何创造可信的形象,小说语言如何既是文学的又是现实的。伍德最关心小说家讲述世界真理的方式,他们如何写出准确窥见事物存在方式的作品,“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最深的动机和首要局限”。伍德的理想作者是契诃夫、托马斯·曼这类人,他们创作的人物形象好像能够打破作者的原意,感到自己是真实的,因此也让读者感到他们是真实的。对伍德来说,作者最重要的才能是济慈所说的消极感受力——能够接受相异的存在方式、信仰和价值观,能够停留在不肯定、神秘感、怀疑中,而不是令人生厌地追求事实和真理。
一位推崇真实性的评论家很自然地喜欢现实主义作品。他的检验标准是奥斯丁、托尔斯泰、亨利·詹姆斯、契诃夫、曼、贝娄、奈保尔。对超现实主义作家——实验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魔幻现实主义者,拉什迪、德里罗、扎德·史密斯,他是持批评态度的。当他谈论乔伊斯或吴尔夫时,他让他们看上去像是现实主义者,避免任何实验或现代主义的成分。他承认库切作品的力量,以比喻和寓言为基础,但是他没有研究它们的力量,而是选择了库切最现实主义、最不具代表性的一部小说《耻》。
《纽约》杂志的书评人萨姆·安德森说,虽然伍德的《小说的原理》讨论了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比如虚构和真实的关系,但它没有逐章深入分析,而是设了123个围绕人物、对话等主题的小节。这些小节的篇幅从数行到数页不等,不停地从一部小说跳到另一部小说,从一件轶事说到另一件轶事,这种形式分散了应有的论证效力。
伍德声称他的《小说的原理》是对罗兰·巴特的批驳,他努力维护小说和真实之间的联系,驳斥罗兰·巴特这类评论家。巴特宣称作者之死,认为现实主义是一套人工的符号系统。伍德则坚持认为,小说既是人工的,又是逼真的,同时保持这两种可能性并不难。但任何一本248页的书都说不清“小说的原理”,这本书的优点是呈现了伍德作为一个文学人物的复杂性。他以前高高在上,现在变得亲切了。他跟读者分享他给女儿读波特小姐写的故事,把福楼拜的一句话翻译成嘻哈风格,几乎每天都会想到索尔·贝娄对一支雪茄的描写。
文学评论的转变
11月6日,《每日电讯报》报道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说,应该像看待科研报告那样,认真对待小说和诗歌。小说家再现和传播关于国际发展的现实,“讲故事是人类最古老的获取信息和表现现实的方法,以前故事像今天的科学研究一样权威。小说往往关心发展问题的基本主题,像不同的人相遇带来的前景和危险,受压制者生活中的勇气、绝望、幽默和被剥夺”。
德雷西维茨指出,除了对神学的专注外,伍德对小说的意义不感兴趣。他的批评在最宏观的层面和最细微的层面之间穿梭——小说技艺在小说史的发展过程和作者的风格特点。在这两方面他很出色,但他忽视了两者之间的东西。他忽视了小说形式的中间层面——叙述结构、性格模式、统一各时刻的图像和象征,他还忽视了小说家用这些方法传递的意义。伍德可以告诉我们福楼拜的叙述或贝娄的风格,但他对这些作家就人世间所说的不太好奇——人世间的烦恼、忧伤或死亡,他宁愿花时间品味某一句话或满足他的理论兴趣。
伍德跟威尔逊、特里林、卡赞和欧文·豪之间有一道鸿沟。威尔逊等纽约评论家之所以杰出、重要,不是因为他们有伟大的学识、思想或表达能力、对文学感情和文学形式的感受力,而是因为他们关心文学之外的东西。威尔逊论述过政治、流行文化、社会主义者派别、美国本土部落等各种论题,警告过将书籍和其他人类活动分离开来的代价。特里林的批评方法是将论题放在道德想象的历史中加以考虑,卡赞致力于阐明美国经验的本质。纽约评论家之所以对文学感兴趣,是因为他们对政治、文化、道德生活和社会生活感兴趣,他们把文学放在他们的研究活动的中心,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文学不仅能再现生活,而且能批判生活,思考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哪里跟我们应该在哪里的关系。
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中说,文学批评在民主社会的高级文化中地位愈来愈显著,它已逐渐、半自觉地取得过去曾经先后被宗教、科学和哲学所占有的文化角色。“文学批评”一词,在20世纪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延伸扩大。起初,文学批评是指对戏剧、诗和小说的比较和评价,然后,它扩充到涵盖过去的批评,如德莱登、雪莱、阿诺德、艾略特等人的散文。随后,它相当迅速地扩大,扩及神学、哲学、社会理论、改革派的政治纲领,以及革命宣言。
“文学批评家是道德顾问,不是因为他们具有取得道德真理的独特门路,而是因为他们见过世面,人生经验丰富。他们阅读较多的书籍,所以较不容易陷入任何一本书籍的语汇中而无法自拔。我们希望有个批评家能将这些人的书摆在一起,来扩大经典范围,给我们一套极丰富而多样的典籍。”
罗蒂列举的典范是马修·阿诺德、沃尔特·佩特、利维斯、艾略特、爱德蒙·威尔逊、特里林、柯默德、布鲁姆等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是解释书本的真实意义,也不是评估所谓的文学价值。反之,他们花时间把书本放入其他书本的脉络中,把人物放入其他人物的脉络中,加以定位。
相比之下,伍德的审美趣味非常狭窄。这也不能怪他,他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产物。“现在没人像以前的纽约评论家那样做,真正的问题是原因何在。首先,这跟文化雄心整体上的丧失有关,再也没有人立志成为下一个乔伊斯或普鲁斯特,重建世界的现代主义者的冲动让位给了后现代的衰弱感,英雄主义的评论已经不再可信。与此相关的是所谓的文化转向,放弃过去几十年间激进批判的政治维度,只重视社会意义——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和媒体的文化评论的领域。政治和文化不再相互联系,或者说对它们的评论不再有联系,因此我们不再拥有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文学小说伍德时代精神詹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