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舞台上的道具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李华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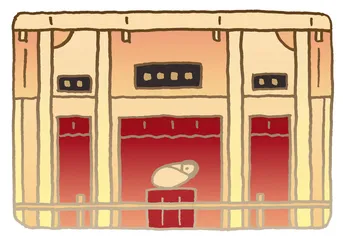
我对过去的那个老山东剧院是充满感情的。绿色琉璃的瓦,以及它宫廷式样的造型,给人的感觉是有些古朴味道的。它给人们真正的记忆,是一些戏剧大师,曾经在这里获得满堂彩。凡来山东的名角,都会在这里演出。记得七八岁时,京剧大师梅兰芳来济南演出,父亲就让我去排队,不过我人小,在那里只是跟着父亲一起排队。
这届京剧节开幕后,我就又来到山东剧院为父亲买了天津青年京剧团演的现代历史剧《郑和下西洋》,票不能仅买一张,就买了两张,让母亲和父亲一起去。父亲说,买80元一张的票就行,因为现在一袋子大米才80元,两张票就是两袋子大米呀。我说,大米什么时候都能买,可是这届京剧节如果不是在济南举办,可是轻易看不到的呀。母亲原来就在山东剧院工作,平生头一次看如此贵的演出,还是有些心疼,连连说,我过去看戏可是从来不花钱的。我说,去看看吧,现在的剧院不是当年了,看看现在的新编历史剧是什么样子,现在的舞美、布景、造型可是当年无法与之相比的。
在济南看戏,最好的剧场是山东剧院,站在最后一排,也能清楚听到台上的道白、唱腔。所谓审美的感觉,似乎就是在这里完成的。那时候,母亲在这里工作,父亲喜爱京剧,我便有了不少在这里“看戏”的经历。不过那是家人抱着我,我并不知道自己看过多少出戏。听母亲说,父亲抱着我在山东剧院看戏,有时戏中需要一个正在襁褓中的孩子,便时不时被抱上去,在那些剧中的情节中被借用一会儿。不过这样的印象我是一点也没有的。因为那时候,我挺乖,不认生,谁抱都行。
不过,当年,母亲说,在这里干,太累,因为五六十年代,山东剧院的演出任务太多,看戏倒是方便了,可是每天都要很晚才回来,这样照顾孩子就成了问题,所以我才有了到剧场上去,被当做道具的经历。
京剧的熏陶,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上新街小学的南边,就是过去的山东省京剧团,每每在早上,来到学校时,那边的演员就在那儿开始吊嗓子。而且我的一些同学,就在徐家花园的京剧团宿舍里住,而那时候的方荣祥先生,就经常在学校大门口或是街上走过,这些演员也是匆匆来匆匆去。有时到我们班那位姓宋的同学家里(他家就在京剧团宿舍),也时常见到那些演员聚在一起,有委婉低回的咿咿呀呀,或是激昂昂的黑头唱腔,那番豪情真的是可以拗折了流云的气魄。
说来也巧,当年和妻子在结婚前看到的唯一一出京剧,大概是《玉堂春》,记不得是哪个剧团演的,只是觉得当时票价太贵,太不值得花费这么多钱来看一场戏。可是一旦进入戏中情节,就会感到,看戏的确比听戏多了些直观的感受。那是在1982年左右,是在现在的北洋大戏院看的,时间已经过去了26年。那时,这就是恋爱的最正统方式。就在山东剧院的临街围子河边,其实就是谈恋爱的去处,而有点情调的才是舍得花钱到剧场看场戏的。
不过,那出《玉堂春》现在想来倒是可以作为谈恋爱人必看剧目的。后来到了电台工作,经常接触到一些剧目什么的,我对《玉堂春》情有独钟。这里面的缘由自然我不会说什么,可是,那个苏三的命运,以及后来对苏三命运不胜唏嘘的感叹,似乎是对人一世情怀的裨益。
对于什么青衣、老旦、小生什么的,可是从小就知道的。尤其是我的一位亲戚就是唱京剧的,她好像就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记得最出色的就是演丫鬟,而且往往是那种插科打诨的角色。只是感到好笑,这么大年纪,硬是演一个天真的少女,为那些小姐、公子通风报信,也不见有什么大段唱腔,而只是装傻卖呆做一个使唤丫头。可是她确实一身的戏,有时你会在生活中分不清她是在演戏还是一番真情,因此,我自小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触,人一旦演了戏,可就是真真假假的难以分辨了。原来以为这丫鬟不是什么角儿,后来才知道,她是红娘呀,而红娘,在《西厢记》里可是不可缺少的角色,按现在的话说,可是“莫让风流误了佳期”中最重要的戏份儿,而她的性格也是挺适合演这个角色的。
也许是曾在襁褓之中的经历,注定了我有些艺术情结,尽管已然半生经历,一事无成,但是想来唯有那浸入骨髓的琴声、鼓声、锣声,以及那些开场程式化最传统的过门,无时不萦绕在耳畔。当年我那位同学的父亲,就是一位锣鼓大师,而那锣鼓就用在开场、换场、上下场、走路、入座等的讲究,想想看,在这些讲究里,其实就是人生百态在舞台上表演所需,人生如戏真贴切。
小时候,我看戏当然也是没有“买票”的机会的,最愿意去的地方,最佳位置是在二楼中间前排,那个打字幕的地方,而看着字幕来回地换,加上台上的京腔京韵,不光是认了不少字,而且绝对字正腔圆。这样的机会,现在却是难得一寻了。■ 玉堂春父亲京剧道具京剧演出舞台戏剧爱情电影智利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