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极殿前献演《洛神赋》
作者:李晶晶(文 / 李晶晶)
 ( 《洛神赋》舞剧融合了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南管音乐和梨园戏的程式化表演
《洛神赋》(局部)
卢卡斯·汉伯 )
( 《洛神赋》舞剧融合了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南管音乐和梨园戏的程式化表演
《洛神赋》(局部)
卢卡斯·汉伯 )
幕起
……翻过伊厥山,越过轩辕山,经过通谷,登上了景山。这时已是夕阳西下,车马疲乏。于是在铺满香草的河岸边停下,让马儿自在地在芝草田里吃草歇息。我在树林中安然地走着,欣赏眼前洛水之滨的美景。忽然间,心神一撼,思绪飘到了远方。猛一抬头,只见一幅奇异景象:一位美貌的女子正在山崖之旁……
惊艳
看那洛水粼粼,石岩崖畔,金色毫芒;再看那绫罗飘逸的佳人,原是宓妃显灵。婉转唱腔,凄切的琵琶声中,曹植与甄宓执手相望……
《洛神赋》原名《感甄赋》,是三国时代曹植著名的赋篇。后代文人认为,他是借歌咏洛神宓妃之美,以表暗恋其兄嫂甄妃之情。由于此赋笔调绚烂典丽、风靡后代,不少文人雅士,或书此赋或绘此情此景。台湾汉唐乐府依据北京故宫所藏顾恺之《洛神赋图》宋人摹本(北宋本一,南宋本二),以南音乐舞的形式将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呈现在今人眼前。

故宫皇极殿前,主体舞台采用太极八卦的“阴阳鱼”设计,整个舞台和观众席的呼应,又簇成一朵盛开的莲花。一改过去舞台和观众之间单调的对应关系,把观众纳入演出的一部分。此外,巧妙利用新媒体艺术,营造出洛水细流、层层涟漪,以及“抽刀断水”的画面,一派如梦似幻、神光离合的天上人间景象。
这部《洛神赋》舞剧融合了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南管音乐和梨园戏的程式化表演。对于南音和梨园戏,知道的人可能并不多。令人难以思议的是,汉唐乐府的创始人及艺术总监陈美娥却将这部南音舞剧的首演放在法国,导演是法兰西歌剧院的新锐歌剧导演、德国人卢卡斯·汉伯(Lukas Hemleb)。在指导《洛神赋》之前,卢卡斯从未到过中国,对中文更是一窍不通。
 (
《洛神赋》(局部)
)
(
《洛神赋》(局部)
)
“汉唐乐府99%的计划我都有把握,我非常自信。”对于和这位西方导演的合作,陈美娥告诉本刊记者,她一点都不担心。
那是2000年,陈美娥带领的汉唐乐府南音社团和法国小艇歌剧院,合作了一部带有巴洛克风格的舞剧《梨园幽梦》。演出的成功,让当时的布赫居文化之家(Maison de la Culture de Bourges)的主任、同时也是《梨园幽梦》的音乐总监吉尔伯(Gilbert Fillinger)大为满意,他希望双方能有更深入的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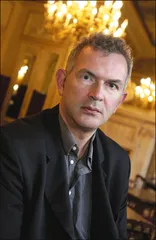 ( 卢卡斯·汉伯 )
( 卢卡斯·汉伯 )
“大约2003年,我和哥哥来到法国,再次和吉尔伯先生见面,商量第二次合作的事情。当时的构想是仿照《梨园幽梦》的形式,采用法国演员和梨园舞者、巴洛克音乐与南音并置演出。所以吉尔伯推荐了法兰西歌剧院的歌剧导演卢卡斯·汉伯,希望能借着他在音乐与戏剧方面的专长,执导这部糅合中西音乐的舞剧。”
卢卡斯本人是学戏剧出身,对音乐也有很深的研究。他执导过法国剧作家菲利普·埃尔桑(Philippe Hersant)的歌剧《卡佩家族的城堡》、莫扎特的《魔笛》、威尔第《命运之力》等,以严苛的标准、坚持不同流俗的选择以及建立文字与音乐间的特殊连结而著名。

此前卢卡斯也曾耳闻汉唐乐府,但要亲自来执掌这么一部“非常中国”的舞剧,必须要对中国文化有深入了解。于是卢卡斯请来老师教授中文,了解南管音乐。“对于我来说,当时各种领域的中国文化和体验可谓是翩然而至:书法、水墨画、茶艺、茶道,还有像是太极拳这种与身体直接相关的艺术。”卢卡斯告诉本刊记者。
在卢卡斯学习中文的时候,陈美娥回到台湾,开始了《洛神赋》的编剧、编舞、编曲的工作。半年后,卢卡斯来到台湾参加编排工作。为了让卢卡斯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人文,陈美娥带他到了北京,看了所有明清时期的皇家建筑;到了泉州,南音的最早的发源地;参观了在武汉出土的曾乙候编钟;最后还去了武当山。“这是为了让他感受一下‘仙气’,因为《洛神赋》是神仙故事嘛。”陈美娥笑着对本刊记者说。
这番游历之后,卢卡斯开始说服吉尔伯和陈美娥舍弃之前的想法,只表演纯粹的南音乐舞。“对于这种古老的南音艺术,我们不应该添加任何多余的元素。它具有一种无法穿透的单纯,那是宛若入会仪式一般的境界。”如此一来,原本中、法各10名演员参加的《洛神赋》,变成由汉唐乐府独立演出,舍弃巴洛克音乐,摒弃所有西方元素。卢卡斯这位西方导演,反而成为乌龙茶里的一滴干邑酒。
“南管乐舞剧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艺术,有别于其他各种流派的中国戏曲。没有震天作响的鼓声或是特技般的动作,也没有长长的胡须与幻妙的装扮。相比较之下,南管乐舞剧的形式要显得含蓄多了,几乎是极简的。它所参照的既不是野兽的传奇故事,也不是战士的史诗颂歌,而是古典、深沉的诗歌。南管音乐拨弹琴弦、吹奏洞箫时,有一种掐金捻银般编织出细腻的质感。”卢卡斯说。
但在艺术上,卢卡斯展现出一种并非完整、严肃的“音乐”,他让一些不合规则的声响成为可以尝试表达的对象,潺潺的水声、碰撞声,以及二弦以情使不以律使的演奏,都是以往汉唐乐府不曾有的元素。
溯源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和南音打一辈子交道。现在说来可能谁都不相信,我第一次听到南音的感受就是,噢,天哪!真是太难听了!我绝不要听第二次。”19岁那年在电台工作的陈美娥,连着好几天收到听众来信,希望她能给大家唱唱南音。“南音是什么?我根本都不知道。向好多人打听才晓得那是一种古老的乐音。”
陈美娥按照朋友的指点,找到一家南音社团。“这是一个有着200多年历史的老社团,里面都是八十来岁的老太太。我第一次找到那儿时,有点被吓到了。音乐不好听,一句歌词老半天唱不完。每个演奏者都那么老,我才十几岁,怎么学、怎么唱啊。”有一位老太太似乎看出了陈美娥的心思,说服她第二天再来,听听老师们唱的。盛情难却,第二天陈美娥如约而来。“真是没想到,同一个曲牌、同一个歌唱的方法,可是由不同的人唱出来,是那么委婉、动听。”就这样,曾下定决心绝不听第二次南音的陈美娥,开始跟随南管名家之后吴素霞学习南音大曲与琵琶弹奏。
“那时候没有人能告诉我南音的历史,只知道它很古老。可究竟有多古老,没人知道。为什么南音的乐器会跟其他民乐使用得不一样,也没有人能解释。所以我觉得研究南音这个事情很重要。我跟哥哥商量,我要辞职,去做南音的调查,但你得养我。他说你究竟想干嘛?没人听的音乐,你却当个宝贝。”哥哥最终是没能拗过妹妹,开始了20多年资助陈美娥学习南音、包括后来创立汉唐乐府。
陈美娥除了和老师学习南音外,其他时间都在东南亚地区探访有关南音历史的线索。“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有很多华人,他们大部分都是闽南、福建人,所以在东南亚都有南音社团。这些侨民当年漂洋过海离开自己的家乡时,都会带上3样东西,族谱、乐谱(南音乐谱),还有就是演奏南音时用的琵琶。所以这时我觉得不再是音乐这么简单的事了。”
1981年,在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的汉学家希珀博士(Dr.Kristofer Schipper)的引见下,陈美娥及乐团成员一行9人远赴欧洲各国演出。“我们做成了一场最长的音乐会,从晚上22点到清晨6点,8个小时没有中断,法国国家电台现场直播。”
演出虽然成功,但在陈美娥看来,自己所属的乐团过于保守、业余,不能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必须不断创新,改变表演形式,才能让南音有出路。但是这种想法与一向把南管当作生活休闲的乐团前辈们的习惯大相径庭,得不到认同的陈美娥离开了乐团。“我到台北,在大学的音乐系里招募学生。虽然他们学的不是南音,可是他们都受过长期的音乐训练,对音乐的理解能力比较强。我带着这些学生,进行了长达10年的海外学术之旅。”直到1993年陈美娥才成立了自己的南管团体——汉唐乐府。
“经历了10年,我觉得南音的基础已经稳定了,我也把南音的64套词谱大曲全部整理、录制下来了。我把梨园戏跟南音的大曲结合,形成现在我们看到的南音风格。它们都是最传统的东西,我没有增加一点其他的乐种或戏种在里面,传统加传统等于前卫,它形成了一个令人惊艳的民族风格,所以在西方各个国家,不管是行家还是外行,都对我们南音很赞叹的。”
收颜
“汉唐乐府从诞生那天开始,就注定了走国际路线,所以我说它打的是‘国际牌’。”乐团建立初期并不顺利,演出机会不多,树敌却不少。在关于南管起源时期的问题上,陈美娥与希珀博士产生了不同的结论,最终导致不欢而散;在推崇南管是中国音乐之祖时又与当时音乐权威意见相悖;当她把把梨园乐舞带上舞台,宣称这是一种古代舞蹈时,又无意间和学院派的理论相抵触。
于是陈美娥只好带着汉唐乐府走上了一条西行之路。“西方人特别容易理解汉唐乐舞的古典美。从最早做学术交流的时候,我带去的并非现在所看到的舞剧,当时就是古典大曲的演奏。一场音乐会通常是一两首大曲就结束了,但他们却能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会惊叹中国有这样的古典音乐!他们是真的感动,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震撼,这在他们的教育里是没有的。汉唐乐府在欧美可谓是如鱼得水。所以我说,汉唐乐府是‘挟洋自重’。”
欧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将近600年来,在文化观念和价值观上没有断层和大的变动。所以“二战”结束以后,当他们和平安定下来的时候,他们恢复得相当快。欧洲可以说是坐享文化财,他们已经形成了一条艺术产业,他们将这个产业称之为“无烟囱工业”。
“我一直说中国怎么可以没有保存超过千年的礼乐呢,中国怎么能把那些曾经失落、甚至已经遗忘的古典文化和思想重新复兴起来呢?”在陈美娥看来,应该用唯美的方式来吸引更多人关注南音,让他们先从欣赏南音开始,再导入学术。于是汉唐乐府1995年首度上演南音乐舞《艳歌行》的时候,就是在既成的传统架构中注入现代剧场元素。
“今天,我把汉唐乐府带到故宫,将《洛神赋》用一种最高端的科技形式来表现,这是在2003年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新媒体艺术、卢卡斯的合作,这都只是为了让传统转化成当代的,让古典变成前卫的衔接点。但我想呈现在所有观众眼前的,依然还是中国的传统,依然还是中国的古典。汉唐乐府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她的下一步不再是为表演而表演,一个新的转型的时机已经来了。”■
梨园歌舞戏
梨园戏源自唐朝“梨园教坊”之歌舞戏。玄宗时酷爱九代遗音传统“清乐”(隋、唐国乐九部伎之首),自作新曲名曰“道调法曲”,亲自教习乐伎于宫苑梨园,故“清乐法曲”部之歌舞人名曰“皇帝梨园弟子”。梨园歌舞分有“女弟子队舞”与男孩的“小儿队舞”,所用乐曲以横笛定调,音调高出“清乐”本调二律,高亢亮丽,利于儿童细稚嗓音;“清乐法曲”则是洞箫定调高,温婉悠扬,适宜成熟之韵情表达,其遗制犹存于今之南管音乐与梨园戏曲规范中。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南侵,汴京(今开封)沦陷,北宋覆亡而迁都临安(今杭州),建立南宋。赵宋皇族南外宗正司也自临安迁往泉州。遗臣、遗民们纷纷南移,一时泉州成为南宋的陪都。以南音为基础,以带浓重的中州洛下正音的泉南腔为唱词吐音,并加以故事化了的梨园戏,此时应运而生。
清朝年间,泉州梨园戏班经常往来闽、台地区演出;日据时期,艺人仿习梨园科步扮演,增入锣鼓、武打场面,或新编剧本改良演出而蔚成时尚。因其使用曲牌均采自南管音乐,故俗称“南管戏”或“高甲戏”,因而取代“梨园戏”原名传谓至今。梨园戏的表演优雅细腻,有一套极其独特、严谨的基本程序,称为“十八步科母”,对手、眼、身、步等每个动作都有严格的规定,如“举手到目眉,分手到肚脐,拱手到下颏”等。此外,各行当都各有特殊的科步身段,如官生与末行的“十八罗汉科”,净与官生的“马鞭科”,老生的须功,生、旦的扇法及眼法,也各有成套的程序。
上世纪70年代,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权威龙彼得教授发现嘉靖年间南戏版本《重刊潮、泉五色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即现存梨园戏《陈三五娘》剧本),梨园戏于中国戏剧史之地位擢升为现存最古老剧种。
南管古乐
南管即福建“南音”,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据考,东晋五胡乱华,北方中原民族大举南迁避祸,中原文化因而传入福建闽南泉州一带;及至唐末经王审知兄弟的推行,并吸收唐代大曲部分精华,与当地音乐结合,逐渐形成“南管”乐曲。
宋王室为避金人南迁,因泉州是最早的对外港口,商船云集,文化兴盛,民间娱乐场所应运而兴,一般艺人及爱好南音之士遂竞相创作新词,使南音的内容更加充实。元人统治时期,推行元语谓之“国语”,唯独泉州因地理经济优势,不改其俗,固守汉语,得以保存在中原失传的音乐、舞蹈、戏剧、民俗等文化艺术。
南音演奏演唱形式为右琵琶、三弦,左洞箫、二弦,执拍板者居中而歌,这与汉代“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相和歌表现形式一脉相承。其工尺谱记法自成体系,是古代音乐记写形制的遗存。横抱演奏的曲颈琵琶、十目九节的洞箫、二弦、三弦击拍板等,也都因袭古乐器遗制。南音曲目有器乐曲和声乐曲2000余首,蕴含了晋清商乐、唐大曲、法曲、燕乐和佛教音乐及宋元明以来的词曲音乐、戏曲音乐等内容。南音以标准泉州方言古语演唱,读音保留了中原古汉语音韵,演唱时讲究咬字吐词、归韵收音。
南音随闽南裔族移民流布海外,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及中国港台地区,凡有闽南人的地方即有南管古乐。 汉唐乐府皇极殿艺术音乐洛神赋卢卡斯文化南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