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 爷(496)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张家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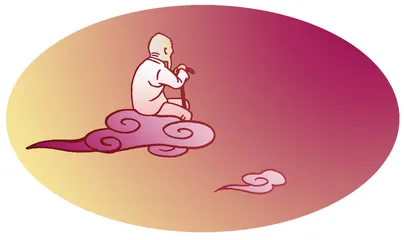
有时做梦会梦见姥爷。他去了有十几年了吧。
有人说姥爷是广西人,有人说是山西的,还有人说他是湖南人,因为姥爷身世很复杂,姥爷他爸是从广东广西一带到山西做官的,姥爷出生在山西,说的却是一口南方话,乍一听像湖南话,仔细一听,又不像。因为从小听姥爷说话,所以我现在对各种难懂方言的听力强于一般人。还因为姥爷一辈子非但没说过普通话,连他出生地临汾的方言也一句不会,我们几个孙辈的人经常问姥姥,姥爷到底是哪儿人呀?姥姥说,八成是外星人吧。
姥爷大学学历,在新中国成立前上过商业专科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商学院经济学院之类的,新中国成立前好歹也在某个商行做过小职员。但他上班没几天就生了病,据说还是那种十天半月好不了的慢性病,姥姥说他其实就是不想工作,和谁都处不好关系。现在想想,估计姥爷那时得的很可能是抑郁症。后来,毛主席解放了全中国,姥爷怀着对新社会种种不看好的想法,就彻底回家做了“宅男”——以后的四五十年里再也没有上过一天班。好在姥姥是个女强人加新女性,知书达理,竟然还上过高中,养活全家的重任就自然地落在了她柔弱又坚强的肩上。
在别人眼里,姥爷是个古人,或者说是个怪人。他的衣着是解放前乡村贫民穿的那种粗布带纽襻的中式立领对襟衫,冬秋是黑色和蓝色,春夏是米色和白色,扣子永远系得一个不落,走在街上,你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某个剧组跑出来的演民国戏的群众演员,仔细一看,神态和做派又真像是地地道道的清末乡绅,稳重而略显木讷。新社会的快节奏和飞速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让他觉得极不适应,好在在家除了读书看报听广播,还可以听听邻居们谈谈天,甚至小孩子也会带来些新鲜事物,他便再也没有出门的必要性了。
我目睹的姥爷这一生中的两次出门,一次是在1982年,我们家从西单四合院搬到新街口的四合院,还有一次是我上大学那年,从四合院搬到了东城的居民楼里。那两次经历对姥爷来说是痛苦而又惊心动魄的。第一次,姥爷出门后就紧紧抓着弱小的我的手,在此之前,他已经几十年没有出过门了。当时北京的公交车很挤,沿着赵登禹路走的7路公交车又尤其的挤,上车后,我和姥爷就被挤散了。姥爷离开我,不知道要在哪儿下车,就紧贴在车门口,7路车凶悍的女售票员揪着姥爷的衣服让他给下车的人让开通道,姥爷被她粗俗的举止吓得直哆嗦,手却紧紧地把住车门,嘴里一直念着:这样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呢?几乎快到下车时我使出了浑身的劲儿从中门挤到了前门姥爷身边,拉着姥爷的手,几乎拽着将姥爷拉下了车,姥爷的头碰到了车门上,被磕肿了一大块,身后售票员还骂着:外地人,真不懂北京的规矩。我紧紧地拉着姥爷的手,眼泪扑嗒嗒地掉了下来。那年我12岁,也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的悲哀,为没能保护好姥爷。
搬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姥爷都闷闷不乐的,晚上看书看到深夜,上午就一直躺在床上,到午饭时才起。我知道生活中的任何一种改变,对他来说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让爸妈给姥爷订了本《大众电影》,那是当时中国图片最多、最好看的杂志,那时我就知道,美女是有疗伤作用的。我问姥爷陈冲好看还是刘晓庆好看,姥爷觉得刘晓庆更美。后来,他又迷上了林芳兵。
第二次搬家后,我就上大学了,姥爷有了单独的房间放自己成堆的旧书。每个周末,我回家后,就坐在他的房间和他聊上几句,姥爷就会问我,钱够用吧?然后,从书架最里面抽出一本旧书,把夹在里面的钱一张不落地塞在我手里,那是我妈给他的零用钱。他说,以前他还买书,但现在书已经放不下了,钱也就没什么用处了。
所有的人当中,姥爷最爱我,超过了刘晓庆和林芳兵。我却没什么可回报他的。他走的那年,冬天很冷,他总是不停地咳嗽。有一天,我下班回来,习惯性地先去推他的门,见他躺在床上,不停地喘着粗气,妈说大夫来过了,是重感冒。那晚上我坐在姥爷床边握着他的手,姥爷说不出话来,眼睛一会儿睁开一会儿闭上,看我还在不在他身边。那天凌晨他离开的时候,我睡着了。姥爷以最安静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告别了我。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愿意想起姥爷,这个道道地地的世界的旁观者,他让我很小就觉得人生可以是对社会无用又无害的,可以一边逃避现实一边观赏现实,同时让我觉得人生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而说到底却是无能为力的。
在梦里,姥爷还是那么面容慈善,和气安详。姥爷要是活到现在,就再也不用挤公共汽车了,我会开着车带他去每一个他想看的地方,让他隔着玻璃窗,不受打扰地欣赏这个世界,没人再能伤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