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写作带我走出迷雾重重的河流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
迟子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64年出生于中国的北极村漠河,童年在黑龙江畔度过,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院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
)
(
迟子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64年出生于中国的北极村漠河,童年在黑龙江畔度过,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院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迟子建的中篇小说集,共5卷本。从早期的代表作《北极村童话》,到今年初刚发表的《草原》,由作家本人自选的25个中篇,是她在20多年中创作的精华,全面呈现了这位大兴安岭山水哺育的女作家的创作历程。迟子建1983年开始写作,3次获得鲁迅文学奖。这一切成就,也许是因为她发自内心的对故乡执著的描写,诗意盎然,淳朴却不显做作。她的笔从没有离开过东北,最近一次得奖的是她的中篇《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篇小说亦是她创作生涯上的一个转折点。第一句她写道:“我想把脸上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悲伤。”生活发生变故后,迟子建遁入到写作的虚拟世界中,以己度人,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从自己的悲伤推及到普世的悲伤,寻觅悲剧背后的原因。她的文字有一股坚实的穿透力,穿透现实生活,直抵命运的本质。小说中的妻子为排解苦闷出门旅行,意外地来到一个矿区,看到底层生活中的凄苦,而作家的思考最终带着读者穿越了痛苦的表象。
三联生活周刊:王安忆说你的“意境特别美好,好像直接从自然里走出来”,你是如何获得这种叙述方式的?
迟子建:我想一个作家的情感是质朴的,他的写作才会呈现质朴的风貌。不是因为你写了泥土,你就质朴了;也不会因为你写了旧上海,你就不是质朴的。说到底,一个作家的气质,决定了他作品的气质。
三联生活周刊:你每天都什么时间写作?写多少字?
迟子建:20多岁的时候,我一夜可以写一篇万把字的小说。那时写得快,除了因为年轻、精力充沛外,可能与初学写作也有关系,心中洋溢着激情,总想着去表达,去倾诉,所以写得快。我要感谢《伪满洲国》的写作,是它让我放慢了写作的节奏。这套上、下两卷近70万字的作品,我写了两年左右。我已经发表了500多万字的作品,出版了40多部书,产量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之所以在写得慢的同时,还能出这些作品,在于我持之以恒。如今我写一个中篇,要用两个月的时间,短篇差不多要一个月。长篇呢,《额尔古纳河右岸》算是个例外,20万字,两个多月就完成了。一般说,我上午10点左右开始写作,到下午三四点种就收工了。每天最多写2000字,晚上基本是在读书。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多年,有没有过写作上的倦怠感?
迟子建:我从1983年开始,已经有20多年了。对于写作,我是始终如一地热爱,所以没有倦怠感。当然,身体疲惫时,我是不会动笔的。有时候,回到故乡,我也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不写作,享受大自然,在青山绿水中徜徉,感受美!还有,我是个足球迷,世界杯和欧洲杯期间,我会停下笔来看球。像这次欧洲杯,开幕以来,我差不多每场都看,这期间当然就不会写作。明晨决赛,德国对阵西班牙,我希望西班牙胜!西班牙足球比德国足球更艺术。而足球场上,失意的往往是艺术足球。文坛其实也是如此,所以好作家都是耐得住寂寞的人。欧洲杯结束,我还要“歇伏”,我这人一到暑天思维就会迟钝,一般说,冬天是我写作的黄金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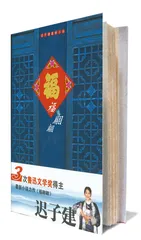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20多年过去,写作给你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得失?
迟子建:生活和写作,是两码事。我曾说过,作家比别人要幸运的一点,是过着“双重生活”。我以写小说为主,小说在我眼里是虚构的艺术,一个作家要想锻炼自己的想象力,就到小说里来吧。在我看,小说家过着两种日子,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精神的。小说家用一支笔,明显比别人多活了一生一世,赚了!当生活遭遇变故时,写作会充当领航人的角色,引你走出迷雾重重的河流,让你看到彼岸的曙光。从这点说,写作给我的生活带来的是“得”,我应该感谢它。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你在黑龙江一个县城里有一所房子,有时候会过去住,是不是写作生活把你变成了一个隐士?
迟子建:真正的隐士,是不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而作家恰好相反,哪怕他居于偏远一隅,也要通过作品发出自己的声音。典型如托尔斯泰,他离开热闹的莫斯科,来到乡间,看似归隐,实则是选择了一片更容易发出“大声”的阵地。他的《复活》、《战争与和平》都完成在那里。去年我拜谒托尔斯泰的庄园,伫立在他的墓前,我想托尔斯泰确实是伟大的,因为他在晚年选择了一片寂静之地发声,所以他的声音是振聋发聩的。相反,像刚刚去世的艾特玛托夫,我非常喜欢他早期的作品,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他的离世,意味着那片土地上,最后一位文学神父离去了。在我心中,他是带着一抔故乡的泥土,去另一个世界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艾特玛托夫的晚年,过得太热闹了,所以他的文学之火,过早地熄灭了。当然,他仍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不过,比起托尔斯泰,他还是弱了。看来,适时地“隐”,对一个作家来说,是重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可能最令人厌烦的事情是信息被扭曲。你如何对待被曲解?
迟子建:碰到这种情况,我一般不会去解释。比如今年有人在天津的一家刊物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我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说其中的一个细节失真,他认为,一个死人怎么可能被装进冰柜呢?多年前,我曾看过一个报道,一个医疗事故的受害者亲属,因怀疑司法机关在尸检结果上做了手脚,为了保存证据,就把死者放进冰柜保存。而且,如今冰柜的容量,是完全可以蹲得下一个人的。但我不愿意回应这样的文章,因为回应一个不难理解的道理,是无趣的事情。只要是善意的曲解,我都能理解。如果明显恶意,你也没什么办法,一笑置之吧,因为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就是没事可做,听听音乐发发呆也好啊。
三联生活周刊:你写了很多中篇,相对说,为什么最让你适应的是中篇小说写作?
迟子建:在我眼里,长篇是大海,短篇是溪流,中篇是江河。对它们,我都爱。我觉得一部作品的长度,是由容量决定的。你让一条小溪,承载江河的流量,它就会崩溃;而没有足够的江河水的汇入,大海也不会有气象的。相对于长篇,中篇能让你少说废话;相对于短篇呢,中篇又能让你滋润地施展笔墨,所以我比较喜欢这种文体。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第一篇作品是如何被接受的,顺利吗?
迟子建:1981年,我高考不理想,进大兴安岭师范专科学校学习。学校面对山峦草滩,风景优美。由于课业不紧,我有充裕的时间看书,写作的野心,就这样渐渐滋生出来。写了几篇稿子后,我开始尝试投稿,引起了《北方文学》编辑的注意。我最早的作品,是毕业前夕写的《北极村童话》,写它时19岁,还处在浪漫年华中。不过这篇小说比我的处女作发表得要晚,因为两家刊物都退稿,说它不像小说。幸运的是,1985年我参加了黑龙江作协在呼兰举办的小说创作学习班,遇到了一位好编辑,我胆怯地把小说给了他,希望他提出修改意见,没想到只改了两个细节,就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就这样,我一路慢慢写了下来。
三联生活周刊:近年的创作是否碰到过瓶颈期?
迟子建:可以说,近年的写作越来越舒展了。如果遇到瓶颈期,也没什么不好。瓶颈是妖娆的障碍啊,能从它颈下爬出来,一定会脱胎换骨的。作家如果有勇气面对有难度的写作的话,就不要怕遭遇瓶颈。真是奇怪,提到“瓶颈”这个词,我甚至觉得挺美的,会联想起穿过石缝的鱼,越过云层的雄鹰。如果你的心是自由的,世上就不存在枷锁。■(文 / 苌苌) 迟子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