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矛盾的《崩溃》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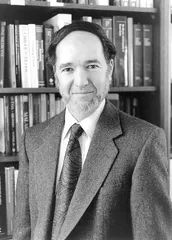 ( 贾雷德·戴蒙德 )
( 贾雷德·戴蒙德 )
文明如何崩溃?
1998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地理学和生理学教授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出版了专著《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 and Steel),为他赢得了无数荣誉。10年后,戴蒙德撰写的又一本描述人类历史兴衰的《崩溃》(Collapse)在中国出版。
《枪炮、病菌与钢铁》描述人类文明的兴起。戴蒙德把文明的胜败归功于枪炮、病菌与钢铁这三个因素,而这三个决定性因素的起因都指向一点: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戴蒙德用大量事例证明,农业和畜牧业之所以率先在某些地区得以发展,并不是因为那里的人民天生聪明或者本性勤劳,而是因为那片土地恰好生长有适合被驯化的野生动植物。
这个理论是如此简单而又完整,使得读者在阅读《枪炮、病菌与钢铁》时充满了“恍然大悟”式的快感。这种快感在《崩溃》中则几乎不存在,因为戴蒙德并没有像前者那样,为人类文明的崩溃找出一个清晰而又准确的解释。但这并不是戴蒙德的本意。他在撰写此书前,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终极理论”,那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可是,随着写作深入,戴蒙德发现,除了生态环境恶化、气候变化(不光是全球变暖,还包括冰河期、火山爆发等)、强邻在侧、友邦援助的减少,以及错误的对策都可以用来解释不同文明的崩溃。这5个罪魁祸首彼此间虽有联系,但内涵各不相同。
事实上,不少学者对文明的崩溃都有不同的解释。英国历史学家、《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一书的作者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认为,文明社会早期由少数“极富创意的精英”们领导,但到后来却由于世袭制而使一批庸才被推上领导岗位,最终导致了文明的崩溃。美国人类学家、《复杂社会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一书的作者约瑟夫·泰特(Joseph Tainter)则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社会结构肯定会趋向复杂。按照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理论,一个社会的组织结构越复杂,为了解决问题而付出的成本就越高。最后该成本一定会高到自然资源无法满足的程度,于是崩溃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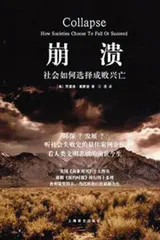 ( 贾雷德·戴蒙德的《崩溃》 )
( 贾雷德·戴蒙德的《崩溃》 )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瘟疫的流行也是许多古代文明崩溃的根本原因,甚至戴蒙德本人对此也有过详细的论述。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戴蒙德用详细数据说明,南美洲印第安文明的消亡并不是由于西班牙军队的枪炮,而是他们带去的天花病毒,这和南美洲的生态环境没有任何关系。
既然如此,戴蒙德的这本《崩溃》是否还有阅读的必要呢?答案是肯定的。虽然戴蒙德没有把生态环境当作文明崩溃的唯一原因,但他用大量鲜活的例子证明,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历史上很多文明之所以崩溃的主要原因。但是,社会可以选择更好的方式应对生态环境的恶化,戴蒙德选择“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作为这本书的副标题,试图用这本书引导广大读者向先人们学习,用科学的态度总结历史教训,避免重蹈业已崩溃的那些古代社会的覆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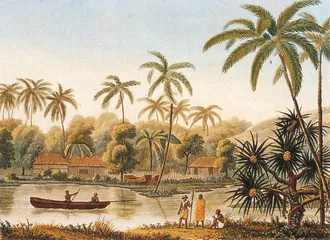 (
南太平洋塔希提马塔韦湾(插图画)
)
(
南太平洋塔希提马塔韦湾(插图画)
)
历史如何借鉴?
现代人对待传统的态度有两种极端。不少种族主义者认为,正是远古时期的“土著”们无节制的乱砍滥伐导致了很多原始森林的消失,而极端环保主义者则认为,古代人统统生活在伊甸园中,我们应该放弃现代生活方式,回到过去。
这两种态度显然都令戴蒙德非常不满,他在“前言”中就迫不及待地给了这两类人当头一棒。“现代社会的问题和过去社会存有诸多不同,我们不应该天真地认为只要以古为鉴就能找到通今的解决方法。”戴蒙德说,“古人没有文字,无法得益于从前社会崩溃的例子带来的警示,他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一种无法预见和始料未及的悲剧,因此在道义上既无法归咎于盲从,也不能归咎于有意识的自利行为。”
戴蒙德以冰岛和格陵兰岛为例,解释了两种极端做法的利弊。这两个岛都是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地方,移民冰岛的维京人在吃尽了苦头后,采取了极端保守的行为,拒绝一切新的尝试,并因此而存活至今。与此相反,移民格陵兰岛的维京人在岛上坚守欧洲生活方式,大量放牧,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教堂,导致原始森林完全消失,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最后这批维京人全部死亡。与此同时,从北美移民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却在该岛顽强地活了下来。
传统有好有坏,如果不加区分,一味坚持传统,结果很可能大相径庭。
提倡坚守传统的人往往对科学技术嗤之以鼻,但戴蒙德用大量实例证明,科学的力量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效果显著,用不好则无异于自杀。比如,氟利昂代替有毒的含氨制冷剂曾经被认为是科技进步的体现,没想到氟利昂却会破坏臭氧层,于是不得不紧急叫停,经济损失惨重。戴蒙德通过这个例子说明,新的科学技术也许能为人类带来好处,却很可能同时带来新的问题。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治理环境,不能指望将来发明出新的高科技办法来解决现在留下的环境问题,那样做效果不一定好,但成本肯定更高。
但是,环境保护也不能离开科学指导。比如,美国加州政府为了保护森林,严禁任何形式的砍伐,并动用飞机严防山火,结果却让小树得以疯狂生长,为山火提供了向上燃烧的“阶梯”,燃自地表的山火一旦烧到树冠,便会迅速蔓延开来,很难控制。这就是加州近年来山火不断的主要原因。加州政府的做法,看似环保,结果却适得其反。
高科技往往和跨国公司联系在一起,后者往往被环保人士视为死敌。同样,戴蒙德认为大公司也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因为大公司影响巨大,只有得到它们的帮助,环保事业才能真正取得实效。戴蒙德专门用一章描述了几内亚岛上的两个石油公司的情况,一个对环境破坏严重,另一个反而成了该岛诸多珍稀动物的乐园。戴蒙德坚信,如果民众对大公司进行严格而又有效的监督,大公司完全可以变成环保的榜样。
这本书最精华的部分是戴蒙德对几个岛的研究。岛的地理特性非常特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封闭的人类学实验室。戴蒙德研究了几十个太平洋小岛的状况,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那些特别大和特别小的岛往往能够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而中型的岛则最容易发生生态崩溃。戴蒙德认为,大岛容易产生独裁者,小岛则会变成彻底的民主乐园,无论是前者的“由上至下”,还是后者的“由下至上”,这两种管理模式都会产生比较好的效果。最坏的情况就是类似复活节岛这样的中型岛国,以及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上的玛雅文明,两者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出现统一的帝国,结果就是长年军阀混战,生态系统逐渐衰败,最后导致崩溃。
戴蒙德从这几个例子引申,得出了一个新颖的结论。他认为专制制度有时对环境保护反而是件好事,比如日本的德川幕府时代,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楚吉洛,都对本国的环境保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相比之下,后者更为发人深省,因为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共享同一座小岛,两者的自然环境相差无几,但海地的独裁者不重视环保,结果酿成了生态灾难。
上述几个案例形态各异,似乎找不出一剂“万能药”,但是,表面的“混乱”恰好验证了戴蒙德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对待环境问题,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一种包治百病的药方都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这就是《崩溃》这本书给读者最大的启示。
中国问题
戴蒙德专门用一章讲述了中国问题。戴蒙德对中国的态度可以说是“谨慎的乐观”,一方面他对中国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忧心忡忡,同时他又高度赞扬了中国政府实行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戴蒙德的看法代表了大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态度。他们担心,一旦中国的13亿人口都想达到西方的生活水平,那么地球将无法承受。事实上,人口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地球面临的最根本的环境问题。如果地球人口一味地膨胀,那么无论如何都将用光地球上所有的自然资源。■(文 / 袁越) 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