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艾特玛托夫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 )
(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 )
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深深影响中国文学青年的苏联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6月10日在德国逝世,享年79岁。就在几个星期前,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访华,在讲座上还被问到对艾特玛托夫的看法,他说:“他在土耳其也很受欢迎,我读过他的小说。但我更喜欢他早期的作品,那是人类生活的精华,纯真且简单……我觉得他应该得诺贝尔奖。”问者和答者都想不到,那时话题的主人公已时日无多。吉尔吉斯斯坦旋即宣布6月14日为国悼日,艾特玛托夫成为国宝级人物,是因为他把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只有300万人口的国家,带到了世界文学的前列。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的数据,他的小说被翻译成世界170多种语言,比如在我国,除了汉语,还有维吾尔语的译本。当然他的贡献不止于此。
现在的年轻人很少谈论艾特玛托夫,很难想象在80年代,他是如何以散发人性光辉的抒情文字,打动了我国文学青年的心。相对当时随处可见的英雄主义、伤痕文学,艾特玛托夫早期作品写的都是普通人的故事,爱与失去,对自由的向往,把硝烟弥漫的战场和英雄留在了远方,他擅长写景状物,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现在书店里还可以找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他的中篇小说集《草原和群山的故事》,书中收录了《查密莉雅》、《我的包红头巾的小白杨》、《骆驼眼》、《第一位老师》,前两篇分别发表于1958年和1961年,是他早期创作的代表作。当时艾特玛托夫年仅30岁,给苏联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气。《查密莉雅》发表后的第二年,法国作家阿拉贡就亲自把它译成法文,称其为“世界上最优美的爱情故事”。
有40多岁的读者说,《查密莉雅》太美,《我的包红头巾的小白杨》太悲,看完都不忍看第二遍。《查密莉雅》的情节并不复杂,一个少年倾慕年轻健美的有夫之妇,她是个不被传统观念所拘囿的人,最终爱上另外一个男人,并与之出走,追求自己的幸福。3年后写的《我的包红头巾的小白杨》则相对成熟些,男主人公在工作上逞强好胜的性格,使他一错再错,自暴自弃,最终导致爱情悲剧。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俄罗斯文学研究室主任石南征说:“艾特玛托夫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新潮环境成长起来的一代,他的作品写吉尔吉斯民族风情有很自然、浪漫的味道,又吸收了俄罗斯传统文学的气息。苏联的现实主义文学于我们有天然的亲近感,而且吉尔吉斯族和我国的柯尔克孜族是一个族系,他的小说带着很浓的诗情画意。”艾特玛托夫的创作有很强的画面感,所写的十余部中长篇小说无一例外地全都拍成了电影和电视剧,有的还改编成芭蕾舞剧。
客观说,艾特玛托夫的文学趣味还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现在看,无论是叙述技巧还是对人性的深度刻画都略逊一筹,后来就被越来越多涌入的欧美和拉丁美洲文学淹没了。艾特玛托夫的父亲在1938年被迫害致死,早年他的作品带着淡淡的厌战情绪,后来则直接挖掘导致国家和民族悲剧命运的根源,如已出版的《永别了,古利萨雷!》、《一日长于百年》。艾特玛托夫近年的作品以全人类未来命运为出发点,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读者尚未看到,不过帕慕克的评点也是意味深长的。
艾特玛托夫曾说过:“一个人失去民族和历史属性,失去个性的全部特征,他就变成了顺从的奴隶、驯服的机器人。”在中后期的作品中,他自己的角色变得越来越沉重,思考更多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之外的人类命运问题,像个警世的预言家一般。他后来从政,作为戈尔巴乔夫的好朋友,曾是驻卢森堡大使,去世前是吉尔吉斯斯坦驻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的大使。■
 ( 《草原和群山的故事》
)
( 《草原和群山的故事》
)
艾特玛托夫最后的绝唱
——专访艾特玛托夫著作中译者谷兴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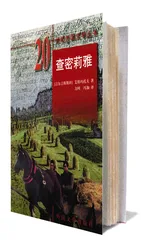 ( 《查密莉雅》 )
( 《查密莉雅》 )
1961年,他的成名作《查密莉雅》就被介绍到我国来了,立即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中苏边境工作,从朋友处借到内部出版供批判用的黄皮书——《白轮船》,主人公小男孩亲眼看到外祖父把母鹿打死了,对世界觉得不可理解,很绝望,想找他的父亲去,希望变成一条鱼,其实是跳到河里自杀了。书中对善与恶的深刻思考,让我记住了这位吉尔吉斯族作家的名字,并一直关注他的创作。“文革”结束后,他的作品陆续在我国出版,到80年代中期竟形成了众多出版社抢译新作的热潮。1986年他的《死刑台》在苏联的杂志上连续发表时,我国还未加入国际著作权公约,于是各出版机构竞相组织人抢译,到1991年已经有“漓江”、“湖南人民”、“外国文学”、“重庆”、“上海译文”、“中国文联”、“百花洲”7家出版社各自推出了自己的译本,书名有《断头台》、《死刑台》与《上帝前的殉难》等不同译法。我是当时在一本苏联的原文杂志上看到小说的第三部发表,于是写信给出版社主动联系翻译,书翻译好后,中国文联出版社拿去发了,效果还好。
他在《死刑台》中写到有组织的犯罪,和当时的体制结合起来,揭露社会之恶,那时就流露出对未来命运的悲观,似乎人类就要走上断头台了。这个作家给我的印象,是他的站位很独特:立足本民族,直面苏联现实,写作技巧上可以看到他接受了现代派影响,有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将过去、现在、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后来他长期生活在西欧,视野进一步开阔,看问题更尖锐。1995年,蓝英年先生带给我他的新书《卡珊德拉标志》。苏联解体后,艾特玛托夫选择了吉尔吉斯斯坦国籍,《卡珊德拉标志》先在德国出版,后于1994年发表在俄罗斯的文学刊物上,它折射出作者经历了沧桑巨变后的思考,站在全球的高度上,审视人类自古以来的善恶交锋。我和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但按期交稿以后,出版社却迟迟不见出版。因为艾特玛托夫在书中有个观点,他提出,一个主体做过的恶并不随他的肉体一同消失,而会遗传给下一代,恶积累起来,像定时炸弹,在适当的时候就会爆炸。他反思和挖掘斯大林问题的根源,他认为如果不搞极端主义,苏联还不至于解体,用意识形态解释一切行不通,人才是最重要的。当时我和艾特玛托夫联系上了,吉尔吉斯斯坦驻华大使馆告诉了我他在比利时的电话,我告诉他我正在翻译这本书,他很高兴。但后来书最终没有出版,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问怎么回事,全世界都出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他说他其实在书里主要批评的是美国。
这是一部有深刻含义的科幻小说,宇宙僧给教皇写信说他发现并破译了人类胚胎发出的信号,胚胎在母腹内形成的最初几周内有能力预知自己未来的生活,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果态度是否定的,便抗拒出生。抗拒出生的信号是孕妇额头上的一块色斑,他称之为“卡珊德拉标志”。他从太空对胎儿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胎儿选择不出生。这是人类面临灾难的预感。先觉者、启蒙者往往要承受孤独、寂寞、苦闷、悲哀与凄惨的命运,这几乎是一种规律。人类要进步,要发展,似乎必须首先献出自己最优秀的儿子。宇宙僧的忏悔,未来学家的报警,最后得到的回报却是围攻、扼杀。宇宙僧后来拒绝返回地球,自杀了,成了宇宙中的木乃伊。其实在《白轮船》的最后,他就曾写过:“你摒弃了你那孩子的心不能容忍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安慰。你短暂的一生,就像闪电,亮了一下,就熄灭了。但闪电是能照亮天空的,而天空是永恒的。这也是我的安慰。”
2006年末,我看到艾特玛托夫在俄罗斯的杂志上发表的新作,就与他联系,他给我寄来一本原著——《崩塌的山岳——永恒的新娘》,是他在布鲁塞尔当大使时写的。翻译时,我遇到以往没有过的困难,他使用了很多少数民族的新词,中央民族大学研究吉尔吉斯语的胡振华教授给了我很多帮助。当时,市场经济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占了统治地位,他的游牧民族出身的同胞很难适应经济一体化,出现了严重危机。书中主人公是个著名作家,情人是个著名歌唱家,但是歌剧没人看了,就被一个大款包养,作家想见她一面都难。后来作家被老家的电话召唤,回去给来打猎的阿拉伯石油大亨当翻译,雪豹是他们的珍稀动物,但最后只能拿它来换钱。当地人想绑架打猎的大亨,作家最后走投无路,对天开枪,结果四面八方都向他开枪,子弹不知是来自阿拉伯人还是同族的年轻人,最后他和雪豹相拥而死。要想掌握这个作家,就要认真思考他的少数民族特性,动物从始至终在他的小说中是个重要存在,你可以感觉到在他的笔下,人和动物是平等的。他曾经说过“人类太高估自己了”,在这部小说里,作家最后留下一篇小说,里面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杀人或者被杀,你怎么办?弱小的民族,没法抗拒世界经济全球化,怎么办?作为人类的精英,他不失自己的操守,任何情况下坚持自己的立场,自己个人的恩怨可以放到一边,生命可以放到一边。我是这么理解他的。这也是艾特玛托夫最后的绝唱。■(文 / 苌苌) 艾特玛托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