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之会”与《兰亭序》
作者:刘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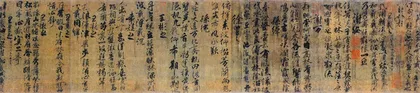
古人“集”的场面,汉代画像石、汉晋墓室壁画以及北宋以来的卷轴画上都能见到。汉末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的邺宫“西园之会”,是文人雅集的典范,聚会情景留在他们的诗歌里:“旨酒盈金罍”,“管弦发徽音”,“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
晋朝士人喜好自然,集会移向山林。著名的两次,前有西晋石崇的“金谷之会”,后有东晋王羲之的“兰亭之会”,照旧饮酒赋诗。“兰亭之会”的诗作,有四言有五言,这些诗篇,我们可以在北京故宫收藏的《兰亭诗卷》里读到,据说是唐朝书家柳公权的手抄本。王羲之为“兰亭之会”写过一篇《兰亭序》,前半部分记叙风流之盛,后半部分伤时感怀,悲叹人生不永。《兰亭序》有墨迹本传世,后来成了书法史上显赫的经典之作。书法名作诞生于文人雅集,“兰亭之会”开了先例。
兰亭是集会之地,位于绍兴西南20多里的兰渚山下,这里是丘陵山区与平原水网地带相接之处,相传春秋越王勾践在此地种植兰花,东汉时建有驿亭,故名“兰亭”。王羲之说,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那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与会人数比石崇“金谷之会”多,凡42人,有隐居当地的名士,有士族官员,明星人物是谢安、许询、支遁、孙绰,51岁的王羲之还带着自己的儿子赴会。众人临水而坐,虽无“丝竹管弦之盛”,却有自然之助,“一觞一咏,畅述幽怀”。集会那天是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初三,古代的“修禊”之日。“修禊”源于先秦时期春秋两季在水滨设祭的“除恶”风俗,《后汉书·礼仪志》所谓“去宿垢疢为大洁”,意思是除旧疾,求健康。曹魏时代,民间的“修禊”活动才固定在三月初三。
王羲之的《兰亭序》最早名为《兰亭集序》或《临河叙》。成为书法名作之后,异名别称甚多,宋朝时,欧阳修名其为《修禊序》,蔡襄称《曲水序》,苏轼称《兰亭文》,黄庭坚称《禊饮序》,宋高宗题曰《禊帖》。
但是,《兰亭序》最初有名,在文章而非书法。《世说新语·企羡篇》说:“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已敌石崇,甚有欣色。”石崇的《金谷诗序》还有部分文字保留下来,结尾一段:“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俱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公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世说新语》注文引录的《临河叙》,最后一段文字与《金谷诗序》相近:“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临河叙》这段赋诗、罚酒人数的文字,在唐朝以来传世的《兰亭序》里见不到,而且《临河叙》的篇幅比《兰亭序》短。这个现象,引起了清朝学者、书家李文田的注意,他说:《临河叙》多出的42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既然“文尚难信,何有于字?”对此,启功先生在《〈兰亭帖〉考》里做了一番解释:“诗文草创,常非一次而成,草稿每有第一稿、第二稿以至若干次稿的分别。古人文集中所载,与草稿不相应和墨迹或刻石不相应的极多。且注家有对于引文删节的,也有节取他文或自加按语补充说明的。以当时的右军文集言,序后附录诸诗,诗前有说明的话四十二字,抑或有之,刘注多这四十二字,原不奇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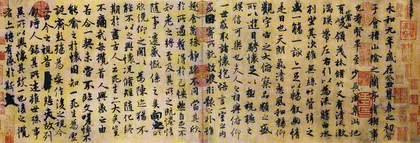
《兰亭序》出名是在唐朝初年,据说太宗“尤为宝重”。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出现了两篇有关《兰亭序》的文章:一篇是刘《隋唐嘉话》中百余字的笔记文,一篇是何延之两千余言的《兰亭记》。
刘、何所记《兰亭》故事详略不一,也有出入。《兰亭》的流传线索,刘溯至梁朝,提到的经手人物多,何延之只追溯到隋朝智永。李世民得到《兰亭》的时间,刘说在太宗做秦王的武德四年(621),何说在即位后的贞观年间(627~649)。太宗得到《兰亭》的方式,刘只是说太宗“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师处,使萧翊就越州求之”。何延之笔下,“萧翊”写作“萧翼”,用了上千字篇幅记叙太宗获得《兰亭》的曲折故事:得知《兰亭》藏在辩才和尚手中,将他从越州请到长安,礼遇有加,前后三次索要,辩才不愿交出,谎称“坠失不知所在”,只好放他回家。然后派萧翼扮成书生,下越州,骗得辩才的信任,乘机盗走。为皇上偷窃不为盗,后人名曰“萧翼赚《兰亭》”。太宗曾经令人摹拓《兰亭》,刘说到具体时间和摹拓数量,“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何延之则说:“帝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只将四位“供奉拓书人”一一列出。《兰亭》最终殉葬昭陵,这件事,刘说是褚遂良的意见:“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何延之说是太宗本人的要求,那个场面描述得绘声绘色:“(太宗)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又涕,引耳而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兰亭》,可与我将去。’及弓剑不遗,同轨毕至,随仙驾入玄宫矣。”
刘是唐朝史学家刘知几之子,供职史馆,他写《兰亭》故事用史家手法,取大要,略细节。何延之做过均州刺史,他的《兰亭记》写得生动曲折,接近小说家的“传奇”。宋朝桑世昌编撰的《兰亭博议》,收罗各种有关《兰亭序》的文篇。其中录有晁补之的一段文字,对何延之讲述的唐太宗派人赚《兰亭》半信半疑,他说:《兰亭》有这么宝贵吗,竟让万乘之主失信于匹夫?以太宗之贤,近古所无,怎么会溺于小小嗜好而轻忽君王的大节!王铚写的一则文字,表示根本不信,他认为:太宗始定天下,威震万国,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僧岂敢吝惜一纸!太宗想得到《兰亭》,也不至于“狭陋若此”,出此下策。
何延之《兰亭记》中有许多经不起推敲的故事“细节”,说王羲之用“蚕茧纸,鼠须笔”写《兰亭序》就是一例。唐太宗时,见过《兰亭序》原迹的人很少,不外魏征、虞世南、褚遂良这些近臣,宫廷摹拓《兰亭序》的那些拓书人也可能见过,但是亲见者也只能知道纸质如何,岂能见到王羲之写《兰亭序》是用“鼠须笔”?未见过《兰亭序》真迹的何延之就更不用说了。
为了强调《兰亭》的“唯一性”,何延之称王羲之“挥毫制序,兴乐而书”,酒醒之后又写过“数十百本”,都不如雅集那天所写。何延之生活在盛唐时代,那时李白《草书歌行》、李颀《赠张旭》、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说到张旭的草书,都将杯中之物的“酒”与“书法”联系起来。大概何延之以今人度古人,联想到兰亭雅集那天的王羲之也是酒后作书,也是当场挥毫,便用“酒”来解释《兰亭》书法绝妙的由来。虽然“酒”与“书法”的关联不是何延之的“发明”,但他追溯到王羲之“酒后”写《兰亭》,比他说王羲之用“鼠须笔”写《兰亭》来得合情合理。
何延之很细心,注意到《兰亭》中20个“之”字写得各不一样,并以“变转悉异”赞扬《兰亭》书法的丰富性,比他“遒媚劲健,绝代更无”的评语更有见地。传世的唐摹《兰亭》神龙本确实存在这个现象,估计他见过这类摹本。一篇行书文稿,重出的字三两个写得不同不足为奇,20个“之”字无一雷同就令人惊诧了。何延之把这种书法现象称为“重者皆构别体”,这个论点,后来成了书家品评《兰亭》书法的“口头禅”,而且是行草书法的一条“金科玉律”。 中国古代史唐朝书法兰亭集序兰亭序王羲之文化王羲之书法之会金谷诗序兰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