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机密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文桐(郑州) 图/陈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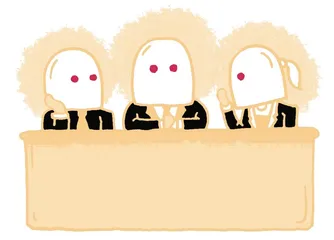
上个月,接到某电影杂志的电话,要我去上海进行面试。因为路途遥远,来回颇费周折,于是在电话里问及一个最关心的问题:工资待遇。而电话那边告诉我,这是商业机密,我说这是一个关乎生存保障的事情,我认为应该知道。那边简短地回答:我们是不会告诉你的,你自己看着办吧。然后非常不客气地撂了电话。
什么时候工资待遇成了商业机密?而我想要知道这份工作是否能够保障我在异地的生存,怎么也变成刺探别人商业机密的间谍行径了?挂了电话,我觉得似乎自己是犯了错误的人,可是怎么想,都觉得自己没什么错儿。
对于薪水的问题,以前我有过一次经历。当时刚刚从报社出来,一个企业内刊的总编邀请我去他们杂志做编辑,清楚告诉我每个月4500元的薪水。可是突然这个总编被调到其他项目,杂志也进行人员调整,于是他介绍我去另外一家杂志,说是那个老总昨天还到他这里要人。我问了待遇,他说:“那家杂志应该和我们的差不多,至少月薪3000元以上。”我顺利进入那家杂志社,在杂志社里根本没再问薪水多少。但是到发工资那天,我彻底傻了眼,1200元,而且所有编辑告诉我,全体都是这么多。吃过这样一次亏,所以我认为应该在去工作前把待遇弄清楚,这是最现实也是最安全的问题。
还是买了往返机票,心想面试时见了老板,再提这个问题,应该一定会有答复吧。
8点30分到11点30分,完成了笔试,14点30分到15点30分看了一个超级晦涩的黑白短篇并完成一篇观后感,被告知等待面试。这一等,就一直等到了18点30分,我们一共4个人,就坐在一间小屋子里,从期待变成了无奈。其中一个北京来的女孩子的返程车票是19点,18点她必须是要赶往车站的,可是老板迟迟未归,她不得不让那张车票作废。我们心里非常疑惑,提前那么多天通知我们来面试,为什么却安排得这样无序?
终于在接近19点的时候,见到了面试我们的老板。在那间斯皮尔伯格曾经光顾过的宽大书房中,进行了集体面试。老板问了第一个问题:“你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于是,一场电影杂志社的新闻发布会开始了。按照从左向右的顺序,第一个人提出的问题是杂志的前景是什么,第二个人提出杂志的广告很少,为什么不扩大宣传,第三个人问的是现今市场上也有几本电影杂志,竞争是否激烈,老板都一一做出回答。我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这是杂志方对我们进行的面试,怎么突然感觉像是记者在采访杂志社呢?终于轮到了我,终于我问出了一直想问的事情:“我比较关心的是杂志编辑的薪水是多少?在来之前,我已经在电话里问及这个问题了,而你们的人员告诉我这是商业机密。”老板说:“现在我也不可能回答你这个问题。”我紧追:“上海是个生活成本很高的城市,所以我必须要知道我的生存是否能够得到保障,是否在解决温饱之后也能比较舒适地生活。在我的城市中1个月3000元的工资基本能够保证生活需求,但是在上海,租住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就要2400元左右,如果在这里也是3000元的薪水,我将入不敷出,形同乞丐。我觉得我想知道待遇这个要求并不过分。”老板回答:“我可以告诉你试期工资是1500元1个月,但是3个月试用期过后的薪水是没有一个标准的。”我说:“那么您能告诉我一个大概的平均数字吗?”他继续玩捉迷藏的游戏:“你不过来工作,谁知道给你开多少工资,只有你来工作了,才能够知道给你多少钱。”
那个老板还在云天雾地不着边际地扯着,大谈着什么远景,抨击着其他杂志,痛斥着曾经在这里工作现已离开的职员,我已经懒得再听他说这些与我们毫无关系的东西,我只关心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本杂志并不是刚刚起步正在创业,它已经是发行10多年的一本成熟杂志,在待遇方面还在这样兜圈子,只谈前景,让我觉得非常可笑也不可理喻。
我明白那些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学生,怀抱着一腔对电影的热爱,是多么迫切地希望能踏入这家杂志的门槛,没有见识过世界的残酷和生存的艰辛,因而理想主义地不计回报。而我不同,我喜欢电影,但是还不至于伟大到因为对电影的热爱而去献身,我也并不需要在这家杂志工作的资历来为以后求职提供方便,我想要的只是一份面包与自身价值并行共得的工作。
于是,在面试的一半,我截住那位老板的话头说:“您还有什么事情吗?如果没有,我先走了。”然后在那位老板错愕的神情里,起身离开。
我以我自己的方式告诉他,别忽悠我了,我不是孩子。 商业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