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跨海大桥”和它的骨牌效应
作者:贾冬婷 ( 杭州湾跨海大桥效果图 )
( 杭州湾跨海大桥效果图 )
杭州湾的想象与现实
每次离开慈溪时,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副总工程师王仁贵总是选择飞机的A座,回来他会选择F座。王仁贵是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总设计师,天气好的时候,他可以从一侧的舷窗看到大桥的样子:“波光穿透了桥面,优美的S形曲线由南向北蜿蜒,一段段桥面逐渐显现,如海中游龙。”
这座6车道的大桥将使宁波和上海的距离缩短100多公里,而此前这片广阔的海域,尚无桥梁建筑师涉足。王仁贵记得1999年3月第一次到杭州湾南岸踏勘时的情景,“茫茫大海,没有系统的水文、地质资料,一片空白”。
他勘测发现,杭州湾流速快,潮差大,一天最大的潮差近8米。这里是世界上形成“涌潮”奇观的3个海湾之一,与南美的亚马孙河河口、南亚的恒河河口齐名,原因在于它典型的“喇叭口”地形:湾顶宽约20公里,湾口宽约100多公里,纵长约100多公里。来自不同方向的4股水在此交织,上游的钱塘江、曹娥江,下游的东海,还有裹挟着泥沙的长江,将这片海水染成混浊的红色,水流紊乱。遇东风或东南风时,喇叭口将形成“窄管”效应——风力翻倍,风推着浪,浪形成波,都在桥区集聚。
所有这一切——潮水、急流、强风、海洋环境,都是混凝土和钢铁的敌人,这也让战胜了它们的杭州湾大桥成为独一无二的样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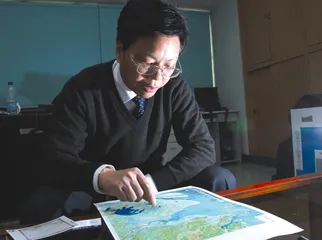 ( 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总设计师王仁贵 )
( 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总设计师王仁贵 )
王仁贵在这里遇到与杭州湾打了10多年交道的傅涌廷。傅涌廷自90年代初就参与了杭州湾大桥项目的研究。他对宁波到上海距离的直接认识开始于50年代,那时候他还是浙江省供销社的采购员,慈溪产棉花,嘉兴产蚕丝,他经常往返两地。南北两岸隔海相望,直线距离不过50公里,但他开着机动三轮车,一大早从慈溪出发,到嘉兴通常已过了吃晚饭的时间。1984年,傅涌廷调到慈溪经委,这时候的慈溪是改革开放的明星,全民、集体、乡镇、个人“四个轮子一起转”的经验形成了“慈溪模式”。但这些产业都是比较低级的加工业,傅涌廷意识到,要发展外向型经济,当时高速公路还没修,交通成了最主要障碍。傅涌廷对记者说,有一次来了几名意大利的客商,一见面就对他抱怨:“我从罗马飞到上海12个小时,没想到,从上海到慈溪竟也花了12个小时。”而周边的萧山、绍兴给了慈溪又一重压力,因为靠近交通主干线,它们的发展速度更快。时任市计委主任的傅涌廷接到新任务:缩短与上海的距离。慈溪有10多公里滩涂,潮来淹没,潮落显露,常规的定期航班肯定不行,他想到了气垫船,可以水陆两用。1990年气垫船开通,从慈溪的庵东到达嘉兴乍浦只要45分钟,但要遇到大风大雾,船就开不了。
长久之计还是要建交通通道。1992年6月26日至29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发展规划会议,首次提出要重点建设沪甬通道,宁波市随即发动研究,傅涌廷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其实通道就是两种选择:架桥或铺隧道。2001年来到杭州湾大桥工程指挥部的副总工程师方明山对记者说,看上去隧道能全天候通车,不受大风、暴雨、大雪、大雾和严重冰冻等恶劣气候环境的影响,但建水下隧道有两种方法:沉管法和盾构法,杭州湾强涌潮、多风浪、海水挟沙量大等恶劣海床水文条件,使沉管法难以实施;用盾构法建如此长的隧道,建设工期很长,资金需求量很大。据估计,隧道造价大约是大桥的2倍,无论是技术上还是造价比上,建造跨海大桥都有明显的优势。
 ( 施工中的大桥主塔 )
( 施工中的大桥主塔 )
王仁贵第一次来这里勘测时南岸还在“九塘”,两年过去已经到了“十塘”,2000多年前北岸的“零塘”海岸线所在地王盘山已经是海中央的一个孤岛。南岸的10公里滩涂区不断淤积,北岸不断冲刷,海岸线不断向北退。沿着两岸不稳定的海岸线勘测,桥梁专家王仁贵要应对的第一个问题是:桥建在哪里?这看上去是个几何问题,只要选择距离最近的两点连成直线就行了,但现实问题更复杂,除规模之外,还要考虑它与既有路网的对接,这条线应该与我国国道主干线“五纵七横”最东边的沿海大通道“同三线”连接顺畅。另外,桥相对两岸岸线要稳定。
杭州湾最窄处恰在起潮点上游。90年代末,水势还无法从技术上很好地控制,在潮流和径流的共同作用下,河床摆幅达3到4公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建在起潮点上游,尽管桥总长只有10多公里,但主桥长度要超过3公里,以覆盖最大摆幅。王仁贵说,建1平方米引桥平均只要6000元左右,而1平方米主桥则需2万多元,桥短并不等于经济。所以,无论从安全角度,还是成本角度考虑,设计师们都选择了避开涌潮点,选在起潮点下游。南端选在宁波的慈溪,如再向“喇叭口”更大开口处走,线路更长,水下地形也不稳定;北段选在嘉兴的海盐,乍浦港上游,避开乍浦港的出海航道。
跨海建桥样本
在第一次研究大桥项目的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担忧:“跨海大桥会不会影响钱塘潮?”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前后,数十万游客争睹钱塘潮,“天排云阵千雷震,地卷山河万马腾”,它的速度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2到3米,是世界上最大、最壮观的涌潮。这一千古奇观会因大桥的建设变小或消失吗?
王仁贵说,这要看钱塘潮的形成原理:一是喇叭口的平面形态;二是水深的逐渐减小,也就是尖山沙坎的存在。建桥并未改变这两者。这也被模型试验所验证。研究人员按照杭州湾海床实际模拟了一个巨大模型,模型的上边界是上海市金山卫,下边界是萧山的老盐仓,与实际不同的是,模型中已建起了长长的杭州湾大桥。科研人员可直观地看到大桥对潮水的影响,在高阳山一带起潮,在八堡、新仓一带成为壮观的“交叉潮”,在盐官形成整齐的“一线潮”,在老盐仓出现“回头潮”……结论是钱江潮起潮点离大桥上游尚有30多公里,基本不受大桥影响,建桥后潮头高度的降低不会超过2厘米。
从北端进入,大桥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片浅紫色,颠覆了人们对于桥梁混凝土形象的想象。紫色护栏向前延伸一段,变成了蓝,再变成青……呈现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渐变。在大桥指挥部内部也曾有激烈争论:会不会太花了?王仁贵说,因为桥太长,司机长时间注视黑色路面,易产生视觉疲劳,颜色改变有助于舒缓压力。
S形造型也是同样的原理。建高速公路有科学的要求,直段不能太长,否则也易产生视觉疲劳;另外,桥梁各段的桥轴线应尽量与涨潮和落潮的主流垂直,以减少建桥对水流的影响,杭州湾的不均匀流向形成曲线桥身。考虑到通航需要,在南北航道的通航孔桥处各呈一拱形,北航道可通过3.5万吨级海轮,南航道可通过3000吨级海轮,大桥同时具有了起伏跌宕的立面形状。王仁贵说,设计师们在设计中借鉴了“长龙卧波”的意象,同时吸取苏堤的元素符号,将苏堤纵向的曲线美在平、纵线型上放大了。
桥的中央是高耸入云的A字形桥塔。带记者参观的中交公路规划院的刘涛说,这其实是一个钢缆支撑系统,南航道桥由一座202米高的A字型桥塔支撑,北航道桥由两座187米高的钻石形桥塔支撑。钢缆可以支撑巨大的跨距,而三角形构造,则增加了桥梁在狂风中的稳定性。杭州湾上的小气候多变。比如雾,设计人员专门在桥的每处路灯下安装了雾灯。而更令人担心的是台风,2005年的台风“卡努”从这里登陆后,70米箱梁预制厂的房屋都被卷走。刘涛指给记者看护栏上的多层风障,还有钢缆上的麻点和螺旋线,这些细节都是为了增大对风的阻力。
2003年大桥在筹划10年之后终于开工,但一开始就遇到一个桥梁工程师未曾遭遇过的难题:在离南岸约9公里的地方,海底40到60米深处有不规则分布的沼气,初勘时曾从海底冲出海面二三十米,并发生燃烧场景。如果这时贸然打下钢管桩,无法控制的天然气井喷会损坏桥梁的基础,并引发灾难性的爆炸。工程师们专程到美国找专家咨询。方明山说,对方说可以帮忙,但提出一个无法接受的条件,要把工程承包权拿下来。他们又找到国内的石油专家,专家们提出“有控制地放气法”:选择天然气的几个积聚点钻孔,把天然气释放出来。另外是增加泥浆的比重,这样在灌桩时可以平衡气压。
让世界最长的大桥跨越海峡,要打下5747根钢管桩做根基。“插在茫茫大海里,就像细小的筷子”,方明山形容,但这些“筷子”其实是每根直径1.5米、长约90米、重70吨的巨大钢管。杭州湾风大雾大,也使得大桥的施工颇具难度,据估计,一年有效施工时间只有120~150天,最多不超过180天。为缩短海上作业时间,他们专门在镇海建立了工厂,就地制造钢桩。每根钢桩必须被打进海床以下80米的深处,除了承受重量以外,还要能够抵御长年累月的海水侵蚀。方明山说,他们采用GPS全球定位系统供打桩的驳船参照,海湾两岸的全球定位基站与轨道卫星进行联系,确立一个三角坐标系,误差在几厘米之内。活塞以每平方米250吨的冲击力打桩,把一根90米高的巨型桥桩打下海床要两个多小时,每艘船每天可以打入七八根。
每9到12根桩上架设一个承台,它是现浇的,为在钢管桩和桥墩之间承上启下。为抵抗海洋环境的侵蚀,王仁贵说,他们在混凝土桥墩中加入了粉煤灰和磨细矿渣,主要性能是填补粗骨料的间隙,提高混凝土的密实度和防腐蚀能力。仍然延续了“大型化、预制化、标准化”的思路,重达300吨到440吨的桥墩在工厂预制完成,再用大型浮吊安装到位。相比这些基础,桥梁必须要承载更多,确保像桌面一样支撑每天几万辆车驶过。在北岸的海盐县边上建立了70米箱梁预制厂,每根箱梁长70米,宽15.8米,重达2200吨,要花费150名工人整整一天才能浇注一片梁。这些箱梁虽然重,但对 "天一号"来说并非难事。“天一”不愧为“天下第一”的名字,它长93米,排水量1.1万吨,负载能力可以达到3000吨,起重高度为53米。
但在杭州湾的另一侧是一片潮水形成的滩涂,在海岸上绵延70公里,并延伸到海中10公里,大型施工器械无法涉足。怎样才能把跨度50米、单片重达1430吨的大型箱梁架起来?总工程师吕忠达操刀攻关:把箱梁从陆上预制场运到提梁站是一道难关,把它提上桥面又是一道难关,最后从桥面一端运到架设点更是一道难关。国际上已有的可借鉴方法是“梁上运梁”,但最重纪录是900吨,吕忠达想,900吨只用2片梁,如果增加到4片梁,不就可以运送1430吨了吗?负责施工的中铁二局专门研制了TE1600运梁机,有76米长,并配置了多达640个车轮,像一只巨大的千足虫,王仁贵说,这么多车轮可以保证4片箱梁运输载荷的受力均衡,经测算每平方厘米受力仅10公斤。电脑利用这种信息,调整每组160个轮子的速度和角度,确保4辆车行动一致。TE1600在满负荷时的最高时速为4公里,每天可以安装两三根箱梁,像蚂蚁搬家一样在巨大的泥滩上建起这座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第一桥”的价值
尽管还未正式通车,桥南端已经悄然开进了旅游车,大桥正迅速成为杭州湾令人兴奋的新景观。桥的景观价值最集中体现在中央的海中平台上——车辆行至途中,出现了一条弧线分叉,这条路下去就是海中平台,形似一个浮游岛。
最早这里只是一个施工平台。王仁贵说,大桥绵延36公里,附近没有岛屿,这也意味着施工工人一早出去,一天都要浪费在途中,而且海中也缺乏堆放建材和信息服务、交通救援的地方。后来他们想到把施工平台、救援平台延展到观景平台,为跨海大桥增加一个新视点,从这里可以一览大桥绵延的优美线形。在这片椭圆形平台上,未来将会出现一个7层楼高的五星级酒店,还有一个145米高的观光塔。在设计师的设想中,这一海中平台应该是主题性的,比如海洋文化、服装展示等,否则等到附近第二、第三座跨海大桥建起,它标志性景观的吸引力就会降低。
杭州湾跨海大桥更大的收益在于过路费。跨海大桥暂定的收费标准为每辆车80元。王仁贵说,如果比较桥两点间不同路线,走桥和绕行高速路收费一样,但大桥将距离缩短了120公里,省油省时间。这一标准原定为55元,收费提升的背景是总投资从118亿元增加到140亿元。
根据2002年大桥工程指挥部提供的交通流量调查预测,大桥建成第一年,每日通过标准车量约为4.5万辆,2015年增至8万辆,到2027年将增加到9.6万辆。按照当初每辆车收费55元的标准计算,投资回报期为14.2年。
方明山说,大桥筹建时,国家投资向中西部倾斜,宁波提出自己融资,采用BOT模式,吸纳民营资本进入,这为杭州湾跨海大桥又增加了一圈光环。在杭州湾大桥工程正式立项后,出现了“民资争着参股、银行抢着贷款”的热闹景象,到2001年7月成立杭州湾大桥发展有限公司之初,总投资118亿元的杭州湾大桥,项目资本金占35%,银行贷款占65%,其中企业投资的35%中,民间资本就占了50.26%。宋城集团董事长黄巧灵认为当初的投资心态有些“躁动”,“有了海中平台与世界第一跨海大桥两大亮点,就有了投资的冲动”。
但现实中的收益并非简单的线性模型,最大的影响因素发生在杭州湾第二、第三座跨海大桥的筹建——绍兴通道和萧山通道。民营资本一度掀起撤资风波,他们认为,这两张接连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会对“第一桥”构成分流威胁。
(实习记者蒲实对本文亦有贡献)
跨海大桥牌局
杭州湾跨海大桥并不是王仁贵参与的第一个跨海大桥项目。他说,我国最早筹划的跨海大桥是珠海到香港的伶仃洋大桥,早在1998年就立项,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拖延,目前线路已南移,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他是这一尚在规划阶段项目的副负责人。2005年,东海大桥建成,这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跨海大桥。现在,王仁贵正在参与海湾大桥、象山港大桥、杭州湾第二大桥——绍兴通道等的前期设计。事实上,目前我国已建或将建的跨海大桥有十几座,东海大桥和杭州湾跨海大桥只是个序幕。
跨海大桥不再是新物种。王仁贵说,在我国规划的高速公路网“7918网”中,由7条首都放射线、9条南北纵向线和18条东西横向线组成,而跨海大桥是其中连接海上通道的重要渠道。从空间上看,杭州湾周边有杭州湾一桥、杭州湾二桥、东海大桥、东海二桥、崇海通道等待建,无疑是跨海大桥分布的最密集区。
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建军对记者说,跨海大桥建设是与GDP发展成正比的。“长三角”是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土地面积占全国2%、人口占全国10%的地方,创造了GDP和财政收入均超过全国20%以上的巨大经济能量。在这里,4小时内可达的交通圈基本形成,这一网络主要靠高速公路搭建,因为高速公路是地方建设,地方获益。但之前这一网络存在缺陷,主要由于受长江、杭州湾两面天堑的阻隔,以上海为起点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铁路、公路主要干道,都被扭曲成了“Z”字形。
陈建军认为,杭州湾跨海大桥可视作长三角区域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看到长三角区域发展的三股动力——自上而下、上海因素和城市间竞争。
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由宁波主导,传导至中心城市上海,陈建军认为,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力,是长三角发展的第一股动力,具体表现为上级城市的发展速度不如下级城市,如上海不如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南京五大城市,这五大城市又不如再下级的城市。
在此之前,一段160公里长“盲肠式”的支线,使港口城市宁波长期处于长三角的末端城市地位,一直被视为杭州的延长线城市。杭州湾大桥建成,宁波终于摆脱了这种尴尬,与杭州、上海间互相2小时可达,重构了三角关系。按照经济专家说法,3小时不能到达的地点,就会被认为距离太远,难以管理及经常到访,“3小时效应”决定了该地区能否直接获得中心城市的辐射和拉动。
陈建军所认为的第二股发展动力是上海因素,它是整个区域对外开放、信息集聚的中心。杭州湾3座跨海大桥的起点分别是宁波慈溪、绍兴上虞、杭州萧山,同处杭甬高速公路沿线,相隔距离均只有几十公里,而桥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连接上海,这是杭、绍、甬三城开展的一场接轨上海的交通竞争。
傅涌廷提供的一种说法是,在宁波筹建杭州湾大桥之初的1995年,他们到省里开会征询意见,周边的绍兴也听到风声,“你们搞跨海大桥,我们也要搞”。省里论证认为,从交通发展总量上看,都可以搞,但要有先后顺序,所以现在的杭州湾二桥要晚于一桥几年再上马,否则大家都“吃不饱”。势均力敌城市间的这种竞争关系是陈建军所认为的第三股动力。陈建军说,短期看,一条线距离缩短,将资源抢夺过去,但这等于推倒了多米诺骨牌,迫使其他线也缩短,所以从长远看会使区域内资源更集聚,是一种竞合关系。 第一陈建军骨牌效应跨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