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速成
作者:薛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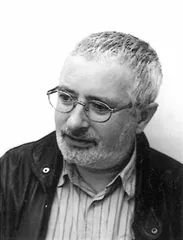 ( 特里·伊格尔顿 )
( 特里·伊格尔顿 )
学理论为何令人生厌
2月6日,这位59岁的作家在接受《澳大利亚人报》采访时说:“文学理论在人们的头脑中扎了根。而这种令外行读者反感的语言非常沉闷。”他还说,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去采访他的人,尤其是非常学院化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记者,都会问他:“你的身体理论是怎样的?”他被这样问过十来次。“在此之前,他们会说,让我们来谈谈男性的目光,你就知道你们开始进入高级胡说八道的领域了。接着突然间又没人问你男性的目光了,没人问你的身体理论了,因为又开始流行别的理论了。这就是这些理论的危险之处,它们只有5年的保质期。”
文学理论确实是走马灯似的轮番登场。日本作家筒井康隆写有一部传奇性的小说名为《文学部唯野教授》,该书以唯野教授的恋爱为主线,以他给学生上西方文学理论课为副线,他号称此书让你只需用读专业书籍百分之一的时间,就可以掌握那些晦涩难懂的文学理论。全书共9章,每一章的标题都是一种文学理论:印象批评、新批评、俄罗斯形式主义、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麦克尤恩讨厌文学理论的原因还不只是因为其语言沉闷、晦涩,还因为它们想把自己伪装成一门科学。“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文学理论让我觉得那是浪费时间,他们希望往他们的学说中引入一些未经验证的理论和几个科学术语,借此赋予其理论一些客观的可信度。”学者们指出,文学理论科学化的一个害处是会破除文学作品的神圣性,如筒井康隆所说,“把结构主义弄通之后,再去读谷崎润一郎,你就不可能坠入痴爱的情欲世界了,届时在你眼中小说就像新闻报道、法律文书等其他的语言一样”。伊格尔顿说,文学作品被看做一个结构,其机制能像其他科学研究的对象一样,加以归类和分析。浪漫主义则认为,诗歌像人一样,有一种生命本质和灵魂,而摆弄一个灵魂是无礼的。
在麦克尤恩看来,文学理论走科学化之路没有错,错在它们还不够科学。法国的心理分析理论家拉康创制了一套复杂的“镜子阶段”理论,讲的是儿童第一次在镜子中认出他们自己的镜像这一时刻对他们心理发展的重要性。“拉康的‘镜子阶段’理论一点证据也没有。在我看来,既然你要使用心理学的术语,你就应该从检验我们的概念入手。你要讨论儿童心理发展的阶段,你最好从观察大量儿童入手,考察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儿童有什么共同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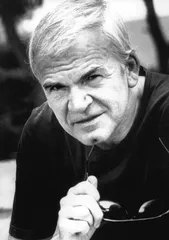 ( 米兰·昆德拉
)
( 米兰·昆德拉
)
麦克尤恩是认知心理学方面书籍的热心读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读了大量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方面的著作。他说他上大学的时候本应该选择分子生物学专业。“二十来岁的时候我埋头研读弗洛伊德的著述。我愿意相信,有一天我们也许能够得出一套植根于事实和观察的心灵理论。”他的读物中一直包括很多科学方面的专著,这段时间他在看德国小说家丹尼尔·克尔曼写的《测量世界》、“诺贝尔奖”生物学奖得主詹姆斯·沃森的自传《避免打扰别人》和理查德·弗拉纳根(Richard Flanagan)的《古尔德的鱼之书》。他24岁的儿子威廉是一位研究艾滋病的遗传学工作者,“我有时有些嫉妒他在从事这样一项正在迅猛发展的科学,年纪轻轻就拥有了一定的知识和专业技能”。
麦克尤恩讨厌文学理论,因为它们只是貌似科学,并没有事实依据,文学理论依赖的是印象,而科学依赖的是观察和量化。显然他对主观性的东西存有偏见,他嫉妒他儿子的专业,认为他年纪轻轻就拥有了很多知识和专业技能很了不起,赞赏沃森自传中的热情和好奇心,因此他“非常喜欢沃森这部关于人性的著作”。刻画嫉妒、热情、好奇、热爱这些情感,这些都是麦克尤恩在谈论科学家时的过人之处。他用这种方式谈论科学,却指责文学理论没有实现其客观性目标,这显得有些奇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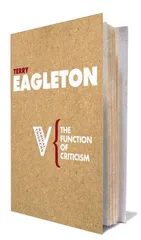 ( 特里·伊格尔顿的作品《批评的功能》 )
( 特里·伊格尔顿的作品《批评的功能》 )
文学理论的正当性
在《文学部唯野教授》一书中,唯野曾经在课堂上这样对学生说:“评论家这种人,本来就是依赖于作家的存在而生存的,这个职业在它出现时就已经败在了作家手下,可是他们却一直想打倒作家,但是最终还是斗不过作家。评论家最害怕人家说他们有本事自己也写本小说看看。”
 ( 日本作家筒井康隆的小说《文学部唯野教授》 )
( 日本作家筒井康隆的小说《文学部唯野教授》 )
他还说,正是作家和评论家们的互相较劲导致文学理论越来越高深,为了不被作家小瞧,“评论家们努力从文学以外找到一种很艰深的理论,一个作家反驳不了的、有权威的批评方式,比如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这么艰深的理论,这下你们作家没辙了吧?作家当然反驳不了,一个作家如果开始学语言学,他的文章还不得变得别扭死了?作家本来就不应该学习和观察理论。不过因为不学那些理论就反驳不了,所以偶尔也有一些作家没事找事学来进行反驳。这一来评论家急了,就再找出更高深的理论来对付,所以文学批评现在搞得越来越深奥。深奥得作家看了如坠五里云雾,完全不知所云。评论家真可怜,搞了容易理解的印象批评被人骂那是暧昧的批评;用理论武装了来搞批评又被人说看不懂。也许作家和评论家相互之间语言不通的这种状态,才正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也未可知。双方不用吵架相安无事地各干各的事”。
但显然作家鄙夷甚至敌视评论家的现象会永远持续下去。日前台湾地区作家张大春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说,他故意不和评论家往来,“我对那些自己不创作的评论家完全不信任,大部分评论家都是作者身上的寄生虫”。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说:“对有些理论家来说,一件艺术作品只是他们进行某种方法论(心理分析、符号学、社会学等等)练习的借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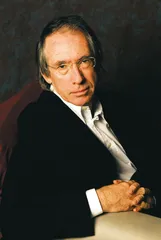 ( 伊恩·麦克尤恩
)
( 伊恩·麦克尤恩
)
作家们不仅鄙视文学理论,还巴不得它早点死掉。麦克尤恩说,文学理论每5年就会更新换代一次,“这种对待文学的风格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现在。但现在我认为,我也希望,它正在消逝”。无独有偶,伊格尔顿也认为文学理论已经式微。他在1983年出版了历史上最畅销的文学理论书籍《文学理论导论》,唯野教授坦承,他在形成自己的理论时受伊格尔顿的启发最大。而伊格尔顿在2003年出版的《理论之后》中说:“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成了过去。”他说,在恐怖主义的时代,文化理论已经跟时代脱节,理论家们都没有回应道德、形而上学、爱、宗教、死亡、苦难等问题。今天的研究生和教授们陷入了相对主义中,写关于性和身体的文章,而不是关注重大问题。
不过伊格尔顿仍为文学理论辩护说:“批评理论的人也会发现,理论比他们要去解释的文艺作品还令人兴奋。弗洛伊德比爱兰尔桂冠诗人塞西尔·戴-路易斯更迷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比查尔斯·金斯利的小说更吸引人、更有创造性。”
另外,文学批评比文学创作更加自省、自我审视,作家容易无意识地、不加反思地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的俘虏,他们也不是自己作品最合适的阐释者。昆德拉说:“小说家绝非任何人的代言人,他甚至不是他自己的想法的代言人。当托尔斯泰写下《安娜·卡列尼娜》初稿的时候,安娜是一个非常不可爱的女人,她悲剧性的结局是应得的下场。而小说的定稿则大不相同,我觉得在写作过程中,托尔斯泰聆听了一种与他个人的道德观念不同的声音,聆听了小说的智慧。真正的小说家都聆听这一高于个人的智慧,因此伟大的小说总是比它们的作者聪明一些。那些比他们的作品更聪明的小说家应该改行。”改行去做评论家吧!昆德拉此前还说作家的传记作者不能阐明一部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可读者需要知道《安娜·卡列尼娜》初稿和定稿的不同,这应该正是文学评论的功能和功劳。 速成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