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是一颗要剥皮的洋葱
作者:苌苌 ( 《 剥洋葱》 )
( 《 剥洋葱》 )
在2007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君特·格拉斯形容“回忆就像洋葱”,是因为洋葱的一些特性很符合他对12?32岁——他生命中最关键的20年的认识。第一,洋葱你要一层层剥开,每剥掉一层,都会露出一些早已忘却的事情;第二,层层剥落间,经常令人不由自主地泪湿沾襟;而最后他发现,在生活的洋葱一层层剥开后,最终并没有藏着蕴含意义的内核。
《剥洋葱》的中文版仅比德文版发行晚半年左右,对外电报道有印象的人还记得,这本书出版后,立即引发震惊世界文化界的“格拉斯党卫军事件”。这是因为他打破长达60年的沉默,道出参加过纳粹组织的真情——曾经被称为“希特勒青年”的格拉斯在17岁时加入纳粹,不是被迫,而是完全出于自愿,是他主动要求上前线的。而且文中他没有一味地批评环境,为自己脱责,以至于从现在的历史环境看来,显得有些为党卫军辩护的劲头,从而引起轩然大波,令他面对直接的批评和冷嘲热讽。也有赞扬:至少格拉斯让我们看到了,不被既定历史和公众舆论所左右,对自己的行为和信仰负责的勇气。
格拉斯生于1927年,与他的12岁相对应的历史时间是1939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格拉斯说这对他意味着童年的结束,而此前的童年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的。格拉斯出生于但泽,身为小店主的父母省吃俭用让他上高级中学,周围男同学纷纷向往的是去“遥远的北国”战场为党国效力。党卫军那仿佛预示着艰难前景的入伍宣誓——“哪怕人人背叛,我们依然忠诚”,不可能不影响到热血沸腾的青少年。当然很多年后,这所谓的荣耀被历史彻底地否定了。
格拉斯深厚的文学功底在他的回忆录中当然有所体现,平实而冗长的叙述中,忽然会出现一些让读者猛然体会到人性的美和力量的闪光处,几位人物如同闪耀的星星散布其间。你可以看到真正的荣誉属于海因里希斯和那个绰号叫“这事咱不干”的小伙子。海因里希斯是格拉斯在但泽高级中学的同学,当所有男同学在海滩上晒着太阳,言谈间向往去“遥远的北国”,希望身上洒满荣誉的光斑时,他就对他们的愚昧无知冷嘲热讽。这是因为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他父亲在上世纪30年代就是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曾经被关进集中营,侥幸生存下来,战后被任命为苏占区的州议会议长,却死于党派内部争斗。海因里希斯长大后学术成就卓著,但在柏林墙倒塌后,西德人所做的新 “评估”中,他又什么都不是了——这种事情在统一后常见。而他的身影在格拉斯的记忆中挥之不去,是因为同样十几岁的他当年固执地不愿意相信有悖于自己价值取向的事情,即便那更接近于正道。“这事咱不干”是他在新兵营中遇到的小伙子,始终拒绝摸枪,对抛过来的枪,回答以“这事咱不干”,即便他的行为导致全队的人跟着他一块受罚,仍然难以撼动他的信念。他的坚定令格拉斯等士兵从憎恨到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在他神秘失踪后,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但又渐渐弥合。最终信仰无法弥补的沟壑出现在他在前线的那个时期,反战情绪不是出于某种忽然起来的正义感,而是出于人类天性中对死亡的恐惧:刚刚还谈笑风生的和他一样年轻的小伙子,霎时粉身碎骨,他的救星一等兵成了无腿的残疾人,而他完全是出于奇特的好运,躲过了炮弹的袭击。那天是元首生日,以至于1954年他的结婚日就定在了那一天,尽管他本人声称那时早已放弃“希特勒青年”的信仰,但他的岳父一家则以自己是瑞士人为借口,肯定了这个时间上的“巧合”。格拉斯在战俘营待了3年,跟着一个号称贵族家的厨子学会了做菜,授课过程在食物严重匮乏的战俘营是纸上谈兵,但却让他看到了语言和想象所具有的强大力量。美国军官给他们看毒气室和堆积如山的尸体照片,有一阵他还认为是美国为了反德伪造的,当然最终他接受了信仰的大厦坍塌的现实,并在很长时间内在心里对往事守口如瓶。
但如果在回忆录中彻底否定年轻时的自己,说自己当时“太傻太天真”,只一味抱怨环境——“没有一个坚定的父亲引导”、“假如我当时不是被……”反倒会被世人耻笑,一老年人,何必呢?“诸如此类的抱怨是廉价的。”格拉斯写道。也没必要把格拉斯的反省看得过于伟大,经历过事业的最高荣耀,在步入人生尾声的时候,让心灵得到些许解脱,夫复何求?在采访中,谈到自己是否有过负罪感时,他说参军当时其实并没有。“后来,这种负罪感成了耻辱压迫着我。对我来说,它始终和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你当时能够认识到你会遇上的事情吗?”与此相比,更多人选择遗忘,或者做沉默的大多数,最差劲的是见风使舵的识时务者。格拉斯曾经在长篇小说《铁皮鼓》中塑造过一位前青年团的首领,在战后顺风摇身一变,成了从不直面冲突的明哲保身的参议教师。还有那种所谓的“事后自封者”,年轻时出于冷血和懦弱的原因、不曾为英雄主义宣传所撼动的人,战后突然把自己说成一个天生的自觉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把磕在自家煤油炉上的伤疤说成是迫害所致,这样的人在任何国家都比比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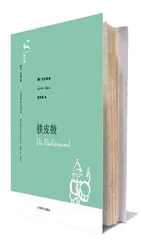 ( 《铁皮鼓》 )
( 《铁皮鼓》 )
令读者印象深刻的还有,在青少年时代的20年中,格拉斯一直处在强大的饥饿感中。先是对食物,后来对女人,战后则是对艺术。小时候他从烟盒中的画片上完成自己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时代的美术教育。退伍后,尽管处境艰难,他还是考进了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学雕塑,鲍伊斯是他的同学,所以格拉斯的简历上还说他是个雕塑家。后来在文学中找到自我,之前以诗歌在国内的文学小圈子中有点名气的他,到了1956年夏天,花了很长时间,在巴黎简陋的寓所找到他成名作的第一个句子:“我承认,我是一所疯人院的住客……”书中的主人公奥斯卡3岁时目睹成年人世界的丑恶,决心拒绝长大。此后,格拉斯便一章接一章地轻松地写了下去,他回忆录中提到的一些经历成了小说素材。小孩模样的侏儒身份使主人公得到实际的好处——放纵、自私、胡作非为、任意满足欲望,而公众对他的一切行为都接受下来,奥斯卡的经历是一个暴君的成长史,也象征社会的逐步自我“矮化”。1959年《铁皮鼓》第一版发行,格拉斯一夜成为灿烂的文学新星,之后的经历世人皆知。在《剥洋葱》的最后,他写道:“从此以后,我就这样生活在一页又一页纸之间,生活在一本又一本书之间。我内心仍然有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但是要讲述这些,却缺少洋葱和兴趣。”
格拉斯出生的城市但泽,也有自己凄楚的记忆。这座德国和波兰的边境城市,在格拉斯出生到1939年那段时间是个自由市,纳粹时期属于德国,1946年以后又归属波兰。在纳粹时期,但泽的卡舒贝人被列为三等公民,而格拉斯的母亲就来自那个血统。后来这座城市在战争中被苏联人炸毁,格拉斯的亲人流离失所,母亲为保护妹妹几次被苏联士兵强奸,后死于癌症。而妹妹也受到一定刺激(尽管书中没有详细说),长期对生活感到迷茫,战后执意要去做修女。这些事情在战后的历史中,都被纳粹对犹太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遮蔽了,这是格拉斯看似平静的叙述中,要向世人讲述的。
 ( 君特·格拉斯夫妇 ) 剥皮洋葱一颗回忆
( 君特·格拉斯夫妇 ) 剥皮洋葱一颗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