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禁锢与想象?
作者:娜斯 ( 《潜水钟和蝴蝶》剧照 )
( 《潜水钟和蝴蝶》剧照 )
奥斯卡后,一个电影网站的小编辑与我在MSN上聊天,让我猜提名的5部影片哪部在他那个网站上点击观看的次数最多?我说这个比让我猜哪个能得奖难多了。他告诉我,是《赎罪》,其次是《迈克尔·克莱顿》,并且表示不解,因为《赎罪》是部文艺片。我说在提名的这5部电影里,当然《赎罪》对观众来说还是最好看的,有明星,有悲情。《迈克尔·克莱顿》估计是乔治·克鲁尼号召力的缘故吧,如今有旧式好莱坞明星风范的男星也就属他了。其他几部,《朱诺》的幽默离中国太远,《血色将至》真的是部闷片,而《老无所依》的那种叙事风格,也需要某种欣赏习惯才行,何况字幕翻译得实在太差(常常一点边都不沾,比如医院一场里,伍迪·哈里森演的职业杀手问退伍老兵出身的主人公:“你也曾参加过‘越战’?”对方答:“是,我也在越南。”而翻译是:“你冷酷无情吗?”诸如此类,这对以对话写得特别好而且能传递很多不可忽略信息的科恩兄弟的电影真是致命打击)!
不管怎样,叫座的、广受欢迎的电影还是需要传统叙事模式的底子。如果题材沉闷,起码还有明星号召力作为帮助。《老无所依》毕竟是对西部追杀片的一个逆反式处理,并且有幽默感;还是一个剧情片,并不是太离谱;明星不是特大,也还是有,所以还是可以进入商业影院的。今年奥斯卡提名最佳导演的《潜水钟与蝴蝶》,才真的是一部根本与主流市场无缘的片子:基本由不为美国观众所知的法国演员组成;很多场景是通过一个模糊的摄影机镜头拍摄的;关于一个全身瘫痪、只有一只眼睛能眨的男人的最后的日子;由一位只会说一点法语、主业不是导演的美国导演拍成的法语电影!
据报道,即使是影片的法方投资商都曾希望它用英文来拍,“这本来已经是一个难拍的题材,一个不容易找到观众的题材,然后你再用法语来拍让其更困难?”
要说电影的起因,本来还真的是想做得更主流一点。好莱坞老牌制片人凯瑟琳·肯尼迪、环球公司和影星约翰尼·德普三方想合作,把《潜水钟和蝴蝶》搬上银幕,这样原本就是一个好莱坞片商制作的、针对更广泛人群的电影,而约翰尼·德普希望由朱利安·施纳贝尔来做导演——施纳贝尔之前的影片《夜幕降临前》就是由德普主演的。对好莱坞大片商来说,有约翰尼·德普的话,还可以想象拍成一部像丹尼尔·戴·刘易斯第一次获奥斯卡奖的《我的左脚》那样的电影。
但是约翰尼·德普因《加勒比海盗》档期的原因退出了这个计划。没有了德普,也就等于自动退出主流市场,倒可以由着导演的性子来了。朱利安·施纳贝尔与《通天塔》制片乔恩·基里克(Jon Kilik)是长期合作伙伴,加上凯瑟琳·肯尼迪,三人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做一部专门针对电影节和艺术影院的电影。事实上,在电影节也的确颇有斩获,施纳贝尔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在奥斯卡获最佳导演提名(在电影节的圈子里有人开玩笑地为该片起一外号——“我的左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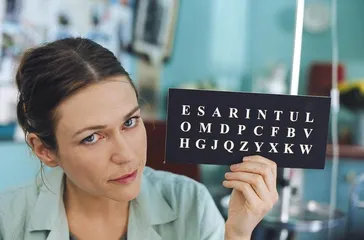 ( 《潜水钟和蝴蝶》剧照 )
( 《潜水钟和蝴蝶》剧照 )
以画家身份拍电影的施纳贝尔,对安东尼奥尼有一份偏爱——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安东尼奥尼本身也是绘画出身,并且其影片以视觉形式的独特性而著名。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虽然主题常常抑郁,但是色彩非常鲜明,这也是《潜水钟和蝴蝶》的特色,也正符合它要表达的东西:在最彻底的身体的禁锢中,想象力是唯一的自由,而且也可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加上主人公原本是为一商业女性杂志工作,所以整部影片色彩和画面的调子都很明亮鲜艳,有时候几乎接近了商业广告摄影——诸如那个女人长发在敞篷车后座上飞舞的镜头。因此,虽然题材听起来有点吓人,但是影片基调却并没有那么阴暗,画面带着法国式的优雅与明丽,带着视觉创意的无拘无束。
施纳贝尔也没有采取通常该类题材惯有的以情动人、毅力战胜残疾等的励志片叙述方式,而是更多地以画家的感觉,去反映当一个人只剩下意识能够活动的时候想象力的释放。一个关于身体禁锢和直面死亡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对心灵和想象力的丰富性和自由度的庆祝。由于题材本身的难度,和施纳贝尔讲述这个故事的成功,很多人都认为奥斯卡获最佳导演的应该是他,毕竟科恩兄弟的《老无所依》对他们自己来说突破并不大。
《潜水钟和蝴蝶》的故事应该已经为人熟知了,43岁的法国《Elle》杂志主编吉恩·多米尼克·鲍比因中风患上了极其罕见的闭锁症候群,最后只剩一只左眼的眼皮能眨动。就是靠这只眼的眨动,医疗专业人士以拼字母的方式与他沟通,最后竟以此方式写成一本书,在他去世前两天出版,风行法国以至世界。
促成施纳贝尔接手这个题材的最主要原因,是2003年他父亲患癌症面临死亡,其最后的日子是在施纳贝尔家度过的。也正是这时候,《潜水钟和蝴蝶》的改编剧本由编剧送到他手上。对施纳贝尔来说,这个剧本忽然与他个人的生活有了相关性。“我想帮助我的父亲去不畏惧死亡,我自己也不想畏惧死亡。我想以拍摄这部电影来克服那种恐惧。”这也是为什么在这部电影中,围绕男主角的是一群女人:他的护理师、前妻和现任女友,但是最强烈的情感关系却是与父亲交流的场面。而以伯格曼《野草莓》(同为考量死亡主题的电影)中出演老教授角色而享誉国际影坛的马克斯·冯·赛多(Max von Sydow)出演父亲角色,更为这个线索加重了分量。疾病常常促进释放人的情感,死亡也使得灵魂真正无拘无束,在影片中有一个场面是男护士抱着鲍比的身体在泳池中,那个造型不难看出是来自圣母玛丽亚抱着十字架下濒死的耶稣基督的古典绘画造型,也是电影对于死亡主题最接近宗教情绪的一个画面。
《赎罪》的小说作者曾说电影最难表现的就是人的意识和潜意识——商业片更多的是靠情节、动作、对话,而《潜水钟和蝴蝶》吸引挑战者的正是它的主角除了一只眼睛,根本没有其他动作,也不能张口说话。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也许没有人比朱利安·施纳贝尔更适合来拍这个题材了。首先他是知名画家,本来就是以视觉想象而非语言和故事来表达他的艺术感觉。另外,他之前拍的两部电影,都是艺术家题材。初执导筒的影片《轻狂岁月》讲述的是纽约街头画家吉恩-米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的故事,巴斯奎特的绘画风格就是极度随意、自由、反体制和天真烂漫的。如果说该部影片让施纳贝尔在电影界颇受好评,那么他的第二部电影《夜幕降临前》就彻底奠定了他的导演地位,以至于以前他的名号是“拍电影的画家”,之后有人开始称他为“画画的导演”了。《夜幕降临前》讲的是古巴作家雷纳多·阿里纳斯(Reinaldo Arenas)的故事,他是同性恋,在古巴受到迫害。两部影片的主人公都是艺术家,都是体制外人物,都是在想象中获得自由。本届因《老无所依》获奥斯卡男配角奖的巴尔登,就因出演《夜幕降临前》的同性恋作家一角而获奥斯卡提名,并且进入好莱坞。而偏好以化妆、奇装异服形象出现的约翰尼·德普,也在该片中出演一个易装癖同性恋角色而引人注目。
这么说来,《潜水钟和蝴蝶》简直是为他度身定做,3部影片可称为他的艺术家“三部曲”,都是讲磨难与艺术家的故事。虽然《潜水钟和蝴蝶》的主人公本来算不上艺术家,但是身体的意外瘫痪,反而让他写成了他做商业杂志主编时一直希望而没有写成的书,用文字来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一个安置所。这正切合施纳贝尔3部影片一贯的主题:能够将人拯救于禁锢和磨难的,唯有精神、心灵、想象力。对于《潜水钟和蝴蝶》的主人公而言,这更加彻底,身体的完全禁锢,反而给了他思想的时间,给了他想象力的自由。
有些时候,某一方面的限制其实可以带来另一方面更大的自由,也就是说,限制的正面就是纪律,而纪律是需要的。举个例子,通常人们把电影看得比电视的艺术层次高,就是因为影院限制了观众某些方面的自由:在电视机和录像机前,人们有太多的自由,走动、接电话、聊天,想快进就快进,想跳看就跳看,注意力无法完全集中。而在电影院里,相对来说,人们应该准时进场,不该随便走动,灯光是暗的,两只眼睛的注意力只在银幕上,并且释放自己的想象力。而《潜水钟和蝴蝶》的主角,因为疾病把这种观看推向极致:他像摄影机一样,用一只眼睛看;他观看,他想象,别无其他。
而艺术电影所受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其自由的通道。没有明星,没有大预算,没有高票房的期待,没有传统故事的要求,制作者反而可以更自由地表达个体的感觉与想象。个体的自由表达是艺术的最基本要求,也是与商业电影的最大区别。
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提到的是,艺术电影在西方永远有人投资和制作,一方面是其经济体系和文化体系从来有这个传统,有钱有闲来鼓励与包容艺术个性与创意;另一方面也跟它的艺术影院系统分不开。艺术影院的观众比较固定,很多有会员制,有固定影讯,其观众的阅读水平高,自己会主动看报章杂志的影评或信息,喜欢与好莱坞商业电影不同的路数和想象力,所以,在艺术影院发行和推广电影,比一般电影的市场花费要低。商业电影要砸钱做广告,而艺术电影会有影评人主动来评。
总之,艺术影院和艺术电影的体系跟主流电影是不同的游戏规则,如果完全用商业电影的操作方式去进行,反而会适得其反。
在中国,商业电影的体系都很混乱,更不要说艺术电影了。可以说,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电影商业大制作和创意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就永远不会得到解决,也不会像好莱坞那样,可以兼收并蓄,边缘不断颠覆主流,主流又不断从边缘吸收新血。■ 或者好莱坞老无所依想象自由潜水禁锢夜幕降临前传记电影剧情片美国电影电影节赎罪商业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