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敌》和诗朗诵
作者:苗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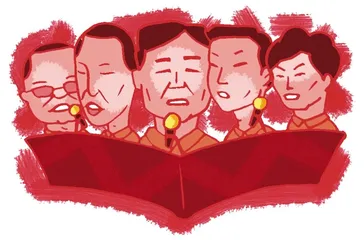
2003年,“非典”结束之后,我忽然非常想看话剧《人民公敌》,这个戏的故事很应景,说一位勇敢的医生,发现自己居住的城市里,温泉受到了污染。这个城市是个温泉疗养地,城里的人大多靠旅游为生。医生想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报告,报纸受到了政府的压力,不能发;印刷厂老板也不给他印传单;医生想去演讲,结果发现自己成了“人民公敌”。
我当时上班的地方就挨着人艺剧场,每天都能看到那里的话剧海报,就是没有《人民公敌》。于是我翻出剧本来,自己当导演,心想,这个医生角色应该让濮存昕或者何冰来演,我给我熟悉的人艺演员都安排了个角色,即便是林兆华大导演都不可能调动那么多演员。我幻想中的排练很成功,比如我让朱旭老先生说出这句台词:“人民不需要什么新的真理,人民有了老的真理,就能过日子。”然后我就听见观众如雷的掌声。可惜,朱老先生档期安排不过来,他们真排了一个话剧,叫《北街南院》,用时髦的话说,讲述了抗击“非典”取得的伟大胜利。
看话剧,我是个老派人,最不喜欢别人瞎改,但好多人都愿意与时俱进。比如南京大学3年前来北京演出过《人民公敌》,就采用了戏中戏结构,说的是一群生长在淮河边的大学生暑假回到家乡,要给老乡们演易卜生的戏剧《人民公敌》,希望借此唤起当地的环保意识。演出介绍给了个悬念:“100年前的斯多克芒医生坚守自己的理想,现在的大学生们能坚守自己的理想吗?”这个悬念对我不起作用,我管你是不是坚守自己的理想呢,我就是想看一出话剧。再说了,温泉被污染,医生是先知,淮河被污染,瞎子都看见了,这个戏跟环保没什么关系呀。
但去年3月的一次演出,把《人民公敌》和环保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那时是世界银行开会,发布中国的环境污染报告,会议结束后就在保利剧场演《人民公敌》,演出由国家环保总局、世界银行、挪威大使馆联合主办,冯宪珍、韩童生担纲主演。可惜我得到消息太晚,后来在许多讨论“绿色中国”的文章中才知道有这么个演出。于是我杞人忧天,真害怕人们把《人民公敌》当成一部环保戏剧来看。
当然,我非常明确地知道,文艺作品可以拿来做各种目的使用。但并不是每一个机构都有实力搞一出话剧当堂会,如果你没本事排练《人民公敌》,又特别想宣传环保,我推荐一个节目,那就是朗诵新美南吉的《去年的树》。这篇童话只有1000多字,说一只小鸟给一棵树唱歌,第二年,小鸟再来,发现树被砍掉了,小鸟找到工厂,树木已经被加工成火柴了,小鸟找到一个村庄,火柴已经用光了,但它点燃的火焰还在,小鸟就对着那火焰唱了首歌,然后就飞走了。要我看,这个童话可以说是一个爱情故事,小鸟要完成一个对爱人的约定,但把它当成一个宣传环保的故事也没什么错。
朗诵一首诗,总比搞一个话剧要简单一些。今年春节晚会,加入赈灾环节,某位导演说了,我们本来是想搞一个雪灾背景的小品,但时间太紧迫,只好搞一个诗朗诵。以我对中国话剧史的了解,几天之内搞一个活报剧,向人民宣扬一个道理,这一点都不难,没料想现在话剧果然凋零了。但中央台的主持人,诗朗诵的水平一直很高,他们从2005年开始有一个保留节目叫“新春诗会”。春节前我在家看电视,看到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新春诗会,董浩老师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烟斗,朗诵李瑛的《蟋蟀》,他的朗诵太棒了,“激起我心头满海的涛涌”。
这个新春诗会是在去年12月31日首播的,那时雪灾还没有闹起来,所以还可以看到朱军在朗诵鲁迅先生的《雪》——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他朗诵得声情并茂,但春节晚会上的诗朗诵,就否定了朱军的朗诵。上来是李瑞英,“雪在下,雪在下,雪在下,从‘三九’过后一直下到腊月二十八”。然后是康辉的,“从北向南,不分昼夜,垂直倾洒,冰凌黄河,雨雪长江,冻颤三湘大地,直扑珠三角,不见了花城那含苞欲放的迎春花”。
央视主持人一个个朗诵没话说,但几个影视演员,到这儿就能显出台词功底来,在我看,陈道明、张国立都中规中矩,只一位头上戴着个发套的青年偶像演员,显然是打了磕巴,我所喜爱的蕾蕾,那声音也不适合朗诵。
即便我喜欢话剧,也没能力为雪灾赶写出一个小品或剧本,但为了歌颂抗击雪灾而取得的伟大胜利,我挑了首艾青的诗练习诗朗诵——“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中国的路,是如此的崎岖,是如此的泥泞呀……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公敌诗朗诵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