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和桃花渡
作者:王星
( 吴敬梓故居 )
第一次去秦淮河是在7年前。乌衣巷比想象中热闹,也没想到李香君故居门前还有霓虹灯。东拐西绕,看着雨花石、紫砂壶摊变成门口站着小伙子拍手吆喝的服装店,又见服装店变成门面更狭促的杂货摊,然后是一大片花鸟市场。走出市场、回到大街上天色已晚,街边的小饭馆亮了灯,映出些“小龙虾”、“鸭血粉丝汤”之类的字样。顺着臭豆腐的味道往前走,不知不觉上了座桥,桥头就有臭豆腐摊,摊子后立着块石碑,上面刻着:“吴敬梓纪念馆。”毕竟是第一次去南京,匆匆走过,吴敬梓纪念馆在印象中只剩下一个掺杂了臭豆腐与河水阴潮味道的影子。
7年后再去秦淮河,已经有闲心一路溜达着琢磨街边店铺的兴衰变迁。贡院门前新立起一串铜像。铜像四周有栅栏,但底座并不高,再加上都是真人大小,成排立在人行道中间乍看有点“加莱义民”的味道,只是神情上相去甚远。江南贡院是当年科举考试的“南方考点”,有幸成为铜像立在这里的不一定是当年的“状元”,但都是后来的名人。每个铜像脚边是它们各自原型的名讳生平,有唐寅,有吴承恩,有林则徐。等看到吴敬梓时,终于又想起7年前一眼晃过的那块石碑。
这时已经知道那座桥叫淮清桥。它的本名应是“淮青桥”,因位于南京两条古水道秦淮河与青溪河交汇处而得名。从贡院一路找过去并不难,大街两边的景物没什么改变,只是白天与傍晚看起来略有不同。桥上没看到臭豆腐摊,倒见四五个人提着鸟笼倚在桥栏上闲聊。桥下河岸西侧有座仿古楼阁,正与刻着“吴敬梓纪念馆”的石碑相对,楼上却只挂了块茶楼的招牌。石碑边有条弧形小巷,进了巷子看出楼阁后还有院子,院门上挂着牌匾:“吴敬梓故居”,下面另有告示牌,说是门票两元、进茶楼喝茶门票可免。
进了门反而看不出有什么茶楼。经一个小男孩指引、敲了阵窗户才找到卖门票的人。院子不算很大,但也有水池、假山、石径、回廊,倘若不是刻意散放在石径两侧无人修整的盆景更衬映出建筑本身的朽颓,大概也能称得上玲珑。北面有从桥上能看到的楼阁,还有一座醒目的古代文人石像,想来只该是吴敬梓。石像不远是一小汪看不见底的水池,那个男孩趴在池边、拿根系了线的竹竿正试图从水池里钓什么。东南面风景更开阔些,而且有石径与回廊似乎通向河边,于是首先选择向东南。草木半掩的南侧粉墙下另有组石像,似乎是位长者在监督一个男孩写字。
选择去水边只为空荡而不是因为对河景有什么特别爱好,毕竟还记得在夫子庙门口见过的那些花花绿绿的画舫和岸边的龙形灯饰。下了石阶,沿河是条石栏护着的空落走廊。石栏比贡院门前桥上的簇新,对面的河景却比夫子庙桥边的老旧。尽管沿岸河房挂了几串红灯,至少屋檐与墙壁还衬出些水色,加上几扇半敞的老窗子,倒也曲曲弯弯地把这一段秦淮河钩出了几折,多少接近点老照片上的味道。
 ( 20 世纪初,南京秦淮河景象
)
( 20 世纪初,南京秦淮河景象
)
走廊不长,向南走不远就被一扇小门挡住,门后另有石阶通向高处,似乎是另一户人家的院子。眼前不见人迹,回头看淮清桥,桥上应该还是车水马龙,但声音已远,几个鸟笼占着前景,拎笼的人也只剩了可有可无的半个背影。闲看了一阵,桥拱下遥遥地见有木船自北面过来,虽仍是游船,好歹是摇着橹的;但又听到机轮声,原来南面河道上也有画舫过来,两船行至一栋红灯高挂的河房附近忽然停下,河房里骤然响起阵笛声。秦淮河旅游介绍中说有“停艇听笛”一景,看来就是如此。“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眼看两条船中相继有相机举起、且有朝向走廊方向的,我识趣让开。
走廊向北蜿蜒至淮清桥。临近桥下,路面渐宽,最终成了片与高处庭院呼应的小花园,园中立着块假石石碑,上书:“桃叶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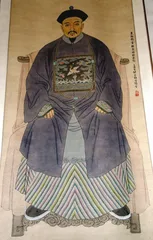 ( 吴敬梓官服像 )
( 吴敬梓官服像 )
以前也听说过桃叶渡,但没想到它与吴敬梓故居竟在一处。这倒验证了有关吴敬梓故居的那种说法:吴敬梓在南京的寓所虽有“秦淮水亭”之称,但并不位于淮清桥边;因原址已建高楼难以恢复,故在古桃叶渡附近另建故居纪念馆。《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据信是吴敬梓的化身,依照小说中叙述,杜少卿迁居秦淮河,寻房时“走过淮清桥??一路看了几处河房,多不中意,一直看到东水关”。这大概也算个旁证。
古桃叶渡确在此处应该是不假的。关于如此狭窄的河道何以成为渡口已经有过很多人论证,都说是当年此处河道极宽、水深湍急,而河道变窄是清顺治初年利涉桥修建之故。《儒林外史》假托为明时旧事,但书中多处显露出清朝成文的痕迹,章回名中出现“沈琼枝利涉桥卖文”便是一例。修建利涉桥本是方便渡涉的善举,却也被经常慨叹为泯没了百年古迹。利涉桥只是座木桥,早已坍塌不复存在,秦淮河河道也未因此再度变宽。
 ( 桃叶 )
( 桃叶 )
见了标志“桃叶渡”的石碑,更觉得刚才没凑到镜头中“弄景”明智。王献之在此处迎娶爱妾桃叶,这已成后世诸多文人骚客吟赋的典故。豪放如辛弃疾尚且有“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姜夔自然少不了“想桃叶,当时唤渡。又将愁眼与春风,待去”;吴敬梓多少占地利之便,一组《金陵景物图诗》中当然有写给桃叶渡的“花霏白板桥,昔人送归妾”;郑板桥的“一缕江丝偏系左,闺阁几多埋灭”固然有“千红一悲”的味道,总不及那句“名以王郎久,花又古渡新”更情真意切。“花又古渡新”语出清初金陵才女纪映淮,据说此诗作于她离乡远嫁之时。清初王士祯《池北偶谈》载:“女名映淮,字阿男??及笄,嫁莒州杜氏,早寡,年五十余,以节终。”
当然,桃叶渡的主角总归是桃叶和王献之。关于桃叶的传说,最常见的版本是:王献之出游乌衣巷,偶遇金陵女子桃叶,继而于渡口迎娶为妾。《今古乐录》言:“《桃叶歌》者,晋王子敬(献之字)之所作也。桃叶,子敬妾名,缘于笃爱,所以歌之。”《桃叶歌》其一“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传唱千古;其二“桃叶复桃叶,桃叶连桃根。相连两乐事,独使我殷勤”却已使后人琢磨“桃根”所指为何人。桃叶的身世在传说中也经过多次变化,有说桃叶是金陵卖砚女,还有说桃叶渡其实是桃叶因婚娶无望投河才得名。
 ( 夫子庙贡院门前的青铜像 )
( 夫子庙贡院门前的青铜像 )
假如《世说新语》相对野史裨语更可靠些,王献之在情史上更值得慨叹的其实是他与自己原配间的离合。《世说新语·德行篇》载:“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晋书·王献之传》记载王献之“以选尚新安公主”,一句蔽过王献之休去原配郗道茂另娶东晋简文帝女儿新安公主的过程。因王献之与郗道茂原为姑表姐弟,因而两人始终互称“姊弟”。王献之唯一传世的书帖《奉对帖》中曾有:“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类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足,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姊耶?俯仰悲咽,实无已无已,唯当绝气耳。”迎娶桃叶是王献之另娶新安公主之后的事,桃叶最后的去向不见史册。王献之享年43岁,据说至死都为抗拒休妻再婚时自残一足的残疾所苦。
史载王献之“神韵超群,天资特秀,流便简易,志在惊奇”,又赞其书法“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王献之的书法也许在书法界另有定论,毕竟有人说他无法望其父项背,也有人说他的“一笔书”开怀素草书之先。王献之的风流倜傥倒被另一奇女子验证过。魏晋名相谢安侄女谢道韫曾以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留名至今。因当时王谢两家素来联姻,谢道韫嫁给王献之兄长王凝之,留下句感慨:“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王献之与诸人舌战不敌,挺身而出、垂帘助战的正是谢道韫。
无论是否身居此处,吴敬梓将笔下卖身后又逃婚的沈琼枝安置在利涉桥也许并不是出于偶然。沈琼枝卖文利涉桥,逃婚事发后与官府的种种交涉依吴敬梓写来洒脱不逊须眉,也只后人附会强加的文字里才把她变成个设下计谋生儿抢夺家业的人物。利涉桥旧址与现在的吴敬梓故居纪念馆相去不远,吴敬梓倘若有灵也该满意。
上了石阶,回到算是吴敬梓故居的庭院。原先粉墙下见到过的父子雕像此时也知道该是王羲之父子。略过各种雕像、穿过回廊,见凸向河边的亭子里多了架了鸟来喝茶的人。上楼,楼上是正经纪念吴敬梓的陈列馆,昏暗的展室里有展板介绍“秦淮水亭”的变革和《儒林外史》的兴衰荣辱。日已近暮,却听楼下传来丝弦曲声。
楼下原本也是展室,此时却多了屋票友。即便不通吴侬软语,也能听出唱的是越剧。先还是矜持伫立门外,无奈被人发现请入室内,摒了声息进去找个位置坐下,看了看居然是“十八相送”。
也许梁祝相送其实不在这里,填过“十日九风雨”的“祝英台令”或许也只是个曲牌,但这是我难得完整听过的一折戏。
出门天色已暗,隐隐又有臭豆腐味道。沿小巷一路走下去,两侧多是居民楼,楼房底层有几家店铺,有古董店,也有修理铺,还有一家卖花的。此时巷子里不过偶尔有自行车经过,几盆君子兰几乎将枝叶舒展到路中间。再往前走,也许会找到《儒林外史》中说的“状元境”,季恬逸曾为蹭一顿饭自状元境跑到水西门再回状元境再去三山街,我想我还不必如此。■ 秦淮河桃花儒林外史王献之吴敬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