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苹如之死
作者:孟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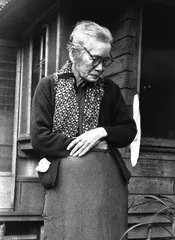
( 郑苹如的母亲木村花子(郑华君) )
2007年9月13日下午,阳光温暖而不灼热,上海莘庄的一幢小楼,退休教师郑国基抱着小狗tonny安详又有点肌肉紧张地对着我们的镜头摆姿势。他说:“我小姑昨天在美国开了记者招待会,她主要是受不了《色·戒》里1/5的情欲戏。以前我们不便说什么,张爱玲也没说写的是我二姑,但现在媒体都说我二姑就是原型,她怎么可能爱上汉奸呢?”
他的二姑郑苹如,被绝大多数人认定是《色·戒》的原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业余特工。上海档案馆的陈正卿说:她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国民党的《上海抗战蒙难同志名单》中,上海档案馆也没有任何关于她的档案资料。陈正卿对记者说:“你别告诉郑家人,他们会伤心的。”
是的,他们会伤心,他们珍视郑苹如的身后声誉。日本人以出任汪伪司法部长作为交换条件,让郑苹如的父亲郑铖在救女儿和节操间择其一,他选了后者。郑苹如殉职后,她的姐姐于1942年心脏病发作去世,父亲患上了胃癌,1943年也去世了。一年后,她的弟弟和未婚夫——两位飞行员在重庆空战中牺牲。抗战胜利后,上海举办地下工作者展览会,全家人去看,进门第一幅大照片是郑苹如。1948年,台湾办了类似展览,郑苹如的嫂子又去看了。“她在台北忠烈祠是有名字的”。郑国基说,他是郑苹如在大陆的唯一亲人。
如果没有李安,《色·戒》只是张爱玲小说中被忽略的一小篇,郑苹如也仅存于高阳的《粉墨春秋》中那合理想象后物是人非的1万多字。实际上,所有关于郑苹如的纪录、记忆都称不上准确,入职、动机、行刺、被捕、囚禁、处决,每段细节每个人的叙述都是不同的。在央视十套“重访”栏目找到的,距她殉职不过几年的一份报纸上,不但写错她未婚夫的名字,更把她行刺的人物弄成李士群。她的死亡时间都已成谜,妹妹郑天如(又名静芝)在美国的记者招待会上称,郑苹如为了不连累家人,吃过1939年的圣诞团圆饭后,翌日赴死,家中一年后才得知她的死讯。而上海史志专家许洪新见过“76号”的老人,他得到的细节是,郑家1940年2月接到郑苹如上司的电话,得知她在前几天被害。1946年一位化名张振华、很有可能在“76号”服务过的人给《大同报》写信,又是另一种说法:郑苹如在1939年12月被软禁,第四大队长林之江看管期间意图污辱她未成,一个月后,她被林之江带到徐家汇火车站荒野处决,“死时林之江之卫士不忍下手,命中要害后,由林之江亲自射击三发,一中胸部,二中头部,方始毙命”。这封信被作为证供收录在南京档案馆编辑的《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中。
这些叙述者都是有凭有据的,为何仍有如此遥远的偏差?而在野史的鳞光片羽中,郑苹如的故事更无法像她在《良友》画报封面上青春丰美的容颜那样清晰可辨,短短的26年生命里,她拍了无数照片,如今存留下的只是解放前夕的夜里,家人匆匆坐船离开上海时带走的一小部分,其他都在“破四旧”中毁掉了。一个高级特工是不会有这么多留影的,像丁默邨和李士群只能找到一张合影。这个酷爱照相、喜欢社交,有那么多时髦衣服的摩登女郎,并不是一位职业特务。郑国基说,中统局从来没给她发过工资。她凭着热情、冲动,以自身为饵诱“76号”的一号头目丁默邨进入死亡的包围圈,尽管那个人此时已经被二号人物李士群排挤得“进不了76号的门”(陈正卿语),她还是义无反顾地一试再试,直到自己反被猎物吞掉。
 (
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与儿子近卫文隆 )
(
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与儿子近卫文隆 )
她连审讯笔录都没有,她本来不必死的。陈正卿告诉记者,日本人曾给“76号”下达的三条原则中的一条是:不许搞和日本有关系的中国人,郑苹如的母亲是日本人,她符合这点。她的死亡完全是由于汉奸阵营内派系争斗的绞杀,处决理由很荒诞:“据翻译说,郑小姐有几个日本朋友是共产党,这样被捕的(丁默邨1946年11月审判笔录)。”而更真实的原因陈正卿点破了:“‘76号’杀人有很大的随意性。”
郑苹如把丁默邨引进了西伯利亚皮衣店,张爱玲却把皮衣换成了钻戒,这笔看似与郑苹如撇清关系的改编却也是有来由的。在张振华的信里,提到郑苹如临刑前佩戴金链及鸡心金质照片,被林之江掳去。而上海史志专家许洪新的材料里提到:胡兰成说,同时被劫走的还有一枚钻戒。
 ( 郑苹如的侄子郑国基 )
( 郑苹如的侄子郑国基 )
这便是《色·戒》的由来。
郑苹如是中日混血,她的母亲木村花子(郑华君)有许多亲戚在天皇的政府中任要职,通过这层关系,她在日伪高层社交圈长袖善舞、如鱼得水。木村花子向来崇拜中国文化,她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国家要侵略丈夫的国家,郑苹如的大弟郑海澄在名古屋飞行学校学习,小弟郑南阳也在日本学医,“七七事变”爆发后,俩人被日本方面扣押,用偷渡的办法才回到中国。因此,郑苹如并不像日本当局想象的那样,有天然的亲日情绪。郑国基听叔叔郑南阳(郑苹如的小弟)讲过:她和两个弟弟用零花钱买了宣传品到浦东宣传抗日。摸清了她的思想后,陈宝骅邀请她加入组织,他说:“你这样没组织抗日不行。”
 ( 郑苹如和大姐的女儿 )
( 郑苹如和大姐的女儿 )
郑苹如的直接领导叫嵇希宗,是她上海法政学院的同学,这个人物正和小说中的邝裕民相对,事实上,后来的刺杀他都有参与。父母不知道二女儿在做些什么,她一直很活跃、爱交际,身边总围绕着一大群追求者,郑国基说:祖父是后来才慢慢察觉女儿的特殊身份,国民党机关全部撤离上海,只留下了法院系统,也给负责人郑铖留下了一部地下电台,郑苹如正是用这架电台向重庆方面汇报工作。
许洪新在《郑苹如和她的家人们》一文中提到:她在日伪高级社交场合发表“中日共存、东亚合作”、“日本应对美作战”一类言论,她于是结识了反战派、首相近卫文的弟弟近卫忠以及近卫的谈判代表早水亲重,还有日本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人。她得到最有价值的一份情报是1938年汪精卫投敌前,她已经两次知会重庆方面汪有异动,可是国民政府未加重视。直到汪精卫发表“艳电”,重庆方才意识到这个业余特工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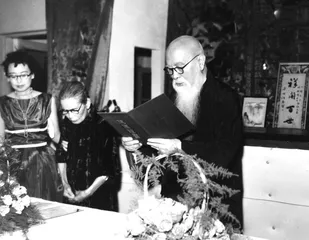 ( 郑苹如的父亲、妹妹都当过于右任(右)的秘书 )
( 郑苹如的父亲、妹妹都当过于右任(右)的秘书 )
郑苹如获得褒奖后干劲大增,她策划了一个大行动——绑架首相的儿子,许洪新估计这一事件仅是郑的个人行动,最多是嵇希宗他们几人的密谋。近卫的儿子近卫文隆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上学,从普林斯顿大学转到这里的他寂寞难耐,每天翻墙出去逛。郑苹如借机带他玩遍夜总会,郑国基也说:近卫迷上二姑,和她谈恋爱。政治上幼稚的郑苹如以为扣押了他,可以逼迫近卫文停战。她把近卫文隆骗到一个“中统”的朋友家,用玩乐和柔情困了他一天一夜。重庆方面也阻止了她的行动,近卫文隆在浑然不觉情况下又被送回。这次行动的代价是郑苹如暴露,重庆方面将她抽调,从日方改攻汉奸丁默邨一线。
郑南阳见证过郑苹如、嵇希宗安排的第一次行动。丁默邨送郑苹如回家,郑提出请他进去坐坐,丁默邨推辞说“下次再来”,计划流产了。第二次是丁默邨约郑苹如一起参加日本特务头子影佐和周佛海举办的宴会,郑苹如借打扮拖延时间通知了上级。她向丁默邨抱怨自己的蓝呢大衣过时了,想去静安寺的西伯利亚皮货店里买一件,丁认为这个地点没有事先约定,还算安全。1939年12月21日下午15点,郑苹如挑大衣时,丁默邨突然扔下200美元说:“你自己挑吧。”从另一个门奔出,箭一般窜进汽车。埋伏好的陈彬等人猝不及防,只在防弹车上留下几个弹痕。事后胡兰成说,丁发现有人向店内观望,即使他贴着郑苹如出门,杀手也可以顶着他脑门开枪。杀手并不认识丁默邨,只是知道是和一位穿大衣的女子在一起的男人,当一个男人单独出来时,他们迟疑中失去了良机。在1946年12月丁默邨的笔录中,他的供述是只听见枪声,中统的人为了报功才称打中车子。

之后的记录众说纷纭:许洪新的文章中讲丁照样参加宴会,并勒令郑苹如自首,否则杀她全家,郑约丁共度圣诞夜,怀揣一把勃朗宁手枪踏上不归路。《上海旧事》中是她自告奋勇,继续试探丁的态度,二人在电话中虚情假意了一番后,郑苹如以要钱投石问路,并叫上沪西日本宪兵分队长横山作为护身符,同去“76号”,刚进大门,日本宪兵涩谷支走横山,将郑押送至定盘路(今江苏路)第一行动大队。第三种是《抗战时期的上海静安》一文的描述,郑约丁在沪西舞厅见面,李士群下属窃听了电话内容,抓走了郑苹如。郑国基在美国看到了中统局的档案材料,其中记载的是第二种说法,他认为郑苹如不甘失败,再次赴险的说法最可靠。他说,那时汪伪并不敢到郑苹如居住的万宜坊来抓人,她所处的法租界新式住宅里有邹韬奋等名人,便衣不能为所欲为。
郑苹如被捕后的遭遇已不可考,陈正卿见到的“76号”的老人,在他签下绝不说出其姓名的保证书后,透露了一些内情。郑苹如起初并未关进“76号”,而是在汉奸潘三省的家中。李士群抓她的目的是“臭臭老丁”,在内部宣扬她是一个颠倒众生的女人。据说出于好奇和嫉妒,一些汉奸眷属如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及丁的老婆赵慧敏都曾去看郑。在抗战胜利后,木村花子给法庭的信中提及这几位老婆一致主张处死郑,她们当然是矢口否认,甚至谎称没听说过此事。可以确定的是,郑苹如从未交待她的真实身份,一口咬定是情感纠纷。
几方的供述中都认可丁默邨并不想杀郑苹如,他到底是因为不忍还是觉得不必,没人知晓。在1946年的笔录中,丁默邨根本不承认有郑这个学生,他先是说:“学生很多,不知道。”法官问:“那与你有特殊的关系怎会不知呢?”丁改口说:“知是知道的。”而后一步步承认见过郑许多次。
为什么不写全名?沈醉的回忆录里,提到嵇希宗说郑苹如只是中统的“运用人员”——即连中统外围组织名册也上不了的,只是利用来完成任务的小人物。并如此评价自己的这名以身殉职的“运用人员”:“郑苹如虎穴锄奸,最重要原因是出于好奇心,她这个人生性喜欢冒风险。”结合马国亮的叙述,成为《良友》封面女郎时,郑苹如可能已经具有了微妙的身份。 郑苹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