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我像戴安娜?我可不是傻大姐
作者:李孟苏
( 蒂娜·布朗 )
布朗VS戴安娜
6月18日晚,伦敦海德公园里的蛇纹岩画廊,汇集了布莱尔、保守党主席大卫·卡梅隆、麦当娜等名人。他们来给蒂娜·布朗(Tina Brown)捧场,庆祝她的处女作《戴安娜纪事》(The Diana Chronicles)在英国上市。
热热闹闹做大排场,蒂娜·布朗最擅长此道。想当年,她在伦敦做杂志的公关活动,需要60把椅子,都要从纽约空运过去。这回派对的地点,她就选择得很用心。1994年,查尔斯王子接受电视访问,首次公开了他和卡米拉的婚外情,搞得天下轰动。当晚戴安娜高调前往蛇纹岩画廊出席派对,穿了件设计师克里斯蒂娜·斯坦博利安(Christina Stambolian)的后腰缀着飘带的露肩小黑裙,不时停下来配合记者们的拍照,借此暗示她比那个第三者时髦、漂亮、行为端正。而对于布朗,此次高调亮相,也很有深意。自2002年卸去《清谈》(Talk)杂志主编一职后,她快被社交圈忘了。要知道,她曾经在英国和纽约的传媒业叱咤风云近30年,有“炒作蜂后”的美称,有关她的人事变动(1998年离开《纽约客》去做《清谈》的主编)能上《纽约时报》头版。
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回大家是冲着书来的,至于这位先后担任过《闲谈》(Tatler)、《名利场》、《纽约客》杂志执行主编的“蜂后”是否能借此机会再冲回传媒圈,事业是否还有起色,谁在乎呢?
说起来,布朗和戴安娜颇有相似之处。她们都是金发美女,都很讲究仪表和风度;都出身于英格兰上流阶层,都嫁入了王室——布朗的丈夫哈罗德·伊文斯爵士是兰登书屋的总裁,他们家一度是纽约传媒业的王室;都是权谋家,极其善于编织人际关系网,都在20世纪90年代抵达人生的全盛时期;她们的故事都是各自城中的奇谈,坊间对她们的评论也都呈两个极端。布朗却认为这种类比“有几分莫名其妙”,“我从来不认为我和一个嫁给了王子的伯爵家的傻大姐闺女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 在布朗新书上市的庆祝会上,汇集了大卫·卡梅隆、麦当娜等名人 )
( 在布朗新书上市的庆祝会上,汇集了大卫·卡梅隆、麦当娜等名人 )
布朗很自信她的智商高于戴安娜。她出生于1953年,父母均为英国娱乐业名流,父亲是电影制片人,母亲是劳伦斯·奥利弗的公关代理,杂志的八卦专栏作家。她后来擅长在派对中解决所用问题,是得到了家学真传的。她父母常常在家里开派对,她从小坐在肖恩·康纳利、琼·柯林斯等明星的膝盖上玩耍,很早就熟悉了名人阶层,知道如何与他们周旋。
布朗上的是私立寄宿学校,先后3次被开除,其中一次是因为她讽刺女校长的胸是UFO。被学校开除没对她的成长带来负面影响,反倒让她自信心爆棚。后来,她上了牛津。她很聪明,到了牛津就算不上聪明了。于是,她组织自己的派对,经营得让同学们以得到邀请为荣。她的同期学友布莱尔,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一荣幸。从此,派对就成为她战无不胜的利器。
 ( 在布朗新书上市的庆祝会上,汇集了大卫·卡梅隆、麦当娜等名人 )
( 在布朗新书上市的庆祝会上,汇集了大卫·卡梅隆、麦当娜等名人 )
传媒业的“蜂后”
20岁,布朗开始出名。1974年,她创作的独幕剧本荣获《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最佳剧本奖。她的志向不在于做个写字的人,而是要掌管一份出版物的命运。她进了《星期日泰晤士报》任记者,在此期间,她先后和一连串有名的男人谈恋爱,有后来的著名作家马丁·艾米斯和奥伯龙·沃,也有同事哈罗德·伊文思。伊文思是英国著名报人,当时任《星期日泰晤士报》编辑,比她年长26岁,为她离了婚。
 ( 1994年,戴安娜穿着小黑裙在蛇纹岩画廊亮相 )
( 1994年,戴安娜穿着小黑裙在蛇纹岩画廊亮相 )
25岁,布朗出任270岁、奄奄一息的老杂志《闲谈》的执行主编。她用4年时间使杂志焕然一新,发行量增加了3倍,撮合康德·纳斯特集团收购了《闲谈》,自己也得到集团老板纽豪斯的欣赏,被指派去拯救垂死的《名利场》杂志。《名利场》创刊于1913年,当初的定位是给有钱人看的奢侈杂志,因此内容多是讲名士明星的趣闻轶事。30年代经济大萧条,杂志被迫停刊。80年代初杂志复刊后,市场和评论的反应都极差,到布朗接手时,每期广告只有14页。1984年元旦上任后,布朗使出了她在《闲谈》的两大法宝:名流明星(意味着有大排场),炒作。
首先,布朗确定《名利场》的内容构成:光鲜夺目的时尚业,无所事事、空虚无聊的名人阶层,大量的海外报道。布朗称这一混合物为“高级废物”。第二,她把自己的形象和杂志合二为一,频频接受专访,举办各种推广、公关活动。一年半以后,杂志开始盈利,她真正成了“蜂后”,一群“工蜂”围着她嗡嗡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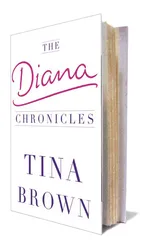 ( 《戴安娜纪事》 )
( 《戴安娜纪事》 )
1992年,布朗担任《纽约客》执行主编。很快,与《纽约客》长期合作的作者们就嗅出新主编实际上是个俗物,她把这本精英的清流刊物变成了《人物》和新闻杂志的混合体。她要求作者把文章写短,首次让照片登上刊物,还约来大批稿子,却又以编辑人手和版面不够毙掉大多数稿件。为杂志写了20年稿子的小说家牙买加·金凯德说她是“暴君,穿着高跟鞋的斯大林”。她不怕被人议论,怕的是不被人议论。
她起用了一批“会从名人文化的槽中找食吃”的一流作者,提供的稿件倒是让《纽约客》容易读了,也在评论和商业上获取了成功。她说:“封面上那些下流的标题会吸引读者去看一篇严肃的、很有挑战性的万字长文吗?如果可以,那谢天谢地。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这是市场营销。如果一本刊物没有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最令人兴奋,最喜吸引眼球,我是不会满意的。任何时候,我都完全服从于读者的需求。我认为这是一场战争。”
布朗是工作狂,改稿子的传真有时竟是从健身房或妇科诊所发来的。在看到康德·纳斯特靠出售《纽约客》上的20多篇文章的电影改编权便获益颇丰,布朗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找到老板,希望能介入这一业务,被拒绝后愤然辞职,去了电影制片公司米拉麦克斯。米拉麦克斯成立了一家多媒体公司,旗下有一本《清谈》杂志,布朗任执行主编。1999年春天,《清谈》发布会在自由女神像附近举行,暗示这本杂志的主人是城中最有权力的人物。
布朗办刊的两板斧在《清谈》完全耍不开。杂志中关于明星的内容,被读者批评是给电影公司当托儿,不买这本新杂志的账。布朗的盛大排场也让杂志招架不住。“9·11”后,杂志业遭重创,广告商纷纷撤广告。在总共赔进去5000万美元后,2002年初《清谈》宣告倒闭,她毫无征兆地被撵走。
精明过人的布朗竟未能及时看穿老板的心,于她乃终生难忘的耻辱。布朗是个雄心勃勃、认准目标便会披荆斩棘大踏步前进的人。她渴望做媒体巨头,偏偏天不遂人愿,于是野心就害了她。老板们并不喜欢她突出、拔高个人形象,她做杂志只是取得了表面的成功,发行量和广告的增多,没有带来实质的盈利,因为她的编辑成本实在太高昂了。1998年《财富》上有一篇文章披露,纽豪斯收购《纽约客》以来总计亏损了1.75亿美元,其中一半是布朗玩完的。《财富》评论说,这位主编编辑了一本美国媒体史上最昂贵的杂志。
挖掘到“解释性独家 新闻”的戴安娜新传
初到纽约时,布朗说:“你不用交朋友,你只用发展关系网。”她的关系网果真发达,迅速帮她找好了出路,在一家有线电视台做了脱口秀主持人,同时任《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在这两块阵地上,她尽其所能还击了幸灾乐祸嘲笑她是败家子的人。倒霉的时候,厄运总是接踵而至,她的脱口秀节目因收视率低被停,又因在专栏上泄私愤受到报社监察人员的调查。
不甘寂寞的布朗只好重新拿起笔,她认为自己应该去写书了。她对其文学经纪人爱德·维克多说,想出版她的日记,里面记载了她在传媒圈30年所看到的秘闻。维克多老于世故,建议她写戴安娜,可以安排在戴安娜去世1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上市。维克多记得,早在1985年,她曾授意《名利场》发表一篇评论,指出戴安娜的婚姻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事实上,“戴安娜”在出版业的市场正在缩小。读者真的还需要讲戴安娜的书吗?戴安娜36岁的人生已经被反复咀嚼,很难再爆出爆炸性的内容,很难再写出新意。作者换成布朗则另当别论。布朗丈夫的兰登书屋出版了这本书,预付金高达100万英镑,发行量为20万册。
布朗拉来两个得力干将合作,一个是舰队街著名记者菲利帕·肯尼迪,一个是《每日快报》的前王室记者阿什莉·沃尔顿。她发挥自己超强的公关能力,说服一些关键人物——密友、保镖等人,开口谈论戴安娜。他们自戴安娜死后一直咬紧牙关。她甚至采访到布莱尔。新书面世后,她更是充分调动了一切人脉资源进行宣传。《纽约时报》收到她的新书两天后便发了书评,接着又对她进行专访,纽约媒体也开始炒她辉煌业绩的冷饭。出版社的宣传通稿说她是戴安娜的闺密,她却否认,说自己只能算是戴安娜的熟人,彼此认识很长时间。她一本正经对英国的记者说:“难道英国的媒体这么说吗?我会纠正的。”遭到记者不留情面的反问,这是不是晚了点?
尽管看不大上伯爵家的傻大姐,布朗还是性急地在书的第二页就告诉读者,戴安娜死前不久,还与她和美国版《时尚》主编安娜·温特在曼哈顿的四季饭店共进了午餐。她说她把戴安娜、一个与媒体发生了又爱又恨的共生关系的人,当做现代英国的一个文化类型来研究。布朗没有在书中披露出戴安娜至今不为人所知的秘密,而是挖掘了“解释性的独家新闻”。比如,很多书中都说戴安娜死前正筹划着移居美国,而布朗公布的“解释性的独家看法”是:美国是个全明星崇拜的国家,人们不在乎戴安娜的中学会考成绩有多么糟糕,她只需要展示自己,证明自己是个名人就行了。她的资料来源更多的还是小报和已经出版的戴妃传记。所以,这本书有时看起来像论文,有时又带来小说的阅读快感,不乏娱乐性的奇闻轶事。比如,戴安娜的密友对布朗披露,戴安娜出席高级宴会之前,总要像抓一根救命稻草般给他打电话,要他讲一些好玩的事,这样与达官显贵们聊天时能妙语连珠。
布朗不承认自己工于心计,可是书中随处可见设置精妙的心机。3年前,戴安娜的管家伯勒尔出版了一本戴安娜传记。她曾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上冷嘲热讽伯勒尔等人是“一帮走投无路的跳梁小丑”,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昧着良心赚死人的钱。同一群人,在她的书里换了一副长相,她用奉承的文字大大赞扬了这些贤臣良相。脸变得这么快,只因为伯勒尔等人同意帮助她。
书后附有7页不可能翻过不看的感谢名单。她感谢了274个人,感谢了高跟鞋设计师马洛诺·布拉尼克、鲍威尔将军、影星约翰·屈伏塔、俄罗斯芭蕾明星米凯亚·巴瑞辛尼科夫、英国文化大臣特莎·乔维尔、亨利·基辛格……这份名单显示,她和很多老朋友恢复了往来,叙了旧。名单里甚至变相穿插了广告,有为她采访提供了住宿的伦敦豪华旅馆,有功能齐全的便携式电子记事簿。
布朗还感谢了戴安娜。在“感谢”一章节中,她说是丈夫陪伴她度过了2年的写作生活。他们住到了位于长岛的别墅,白天各自在相邻的两间书房里工作,中午骑车出去吃饭,晚上看一个电影录像带。她写道:“如果可怜的戴安娜在家里能拥有这般浓浓的爱意该多好。” 戴安娜傻大姐